劉義慶和《世說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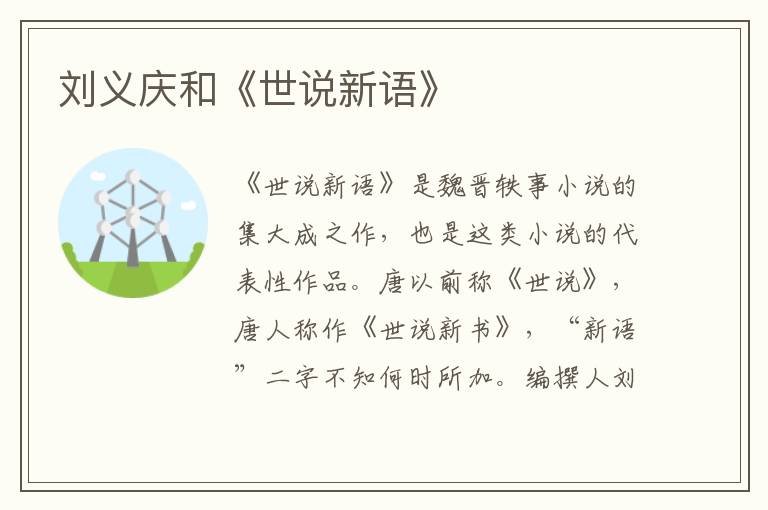
《世說新語》是魏晉軼事小說的集大成之作,也是這類小說的代表性作品。唐以前稱《世說》,唐人稱作《世說新書》,“新語”二字不知何時所加。編撰人劉義慶(403-444),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是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封臨川王,官至尚書左仆射、中書令。他喜好文史,門下聚集了不少才學之士。《世說新語》可能就是他和手下的文人合編的。本書在梁代已有劉孝標的注本。劉注引用古書四百余種,其中多數今已失傳。在補充、豐富、辨正《世說新語》的內容和保存古書佚文方面,劉注都有很大功績,極為珍貴。解放后有王利器的校訂本。本書不少故事取自己散佚的東晉裴啟的《語林》和郭澄之的《郭子》,文字也間或相同。書中所記僅有五則是東漢以前的事,其余均為漢末至東晉士族階層人物的遺聞軼事,尤詳于東晉。全書按內容分類錄事,計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每門多者數十條,少者幾條。編撰者劉義慶站在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立場,標榜儒家名教,崇尚老莊自然,往往用同情和贊賞的態度去描寫許多應該嚴格加以批判的東西,宣揚了不少封建的沒落意識,這就給本書的思想帶來很大的局限性。但從內容的客觀意義來說,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認識價值,可以作為研究當時社會歷史的參考資料。
本書以大量的篇幅記載了名士們種種奇特的舉動和玄虛的清談,向人們展示了所謂“魏晉風度”、“名士風流”究竟是一種什么貨色,從而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側面加深對兩晉士族階級腐朽本質的認識。如《任誕》篇所記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劉伶從婦求酒,縱酒放達,脫衣裸形在屋中;畢卓說:“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雅量》篇所載顧雍在下圍棋時得到兒子死訊,雖五內如焚,表面依然神氣不變;太尉記室參軍褚裒雖被吳興縣令趕到牛棚下,然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言語》篇所記身擔要職的謝安登冶城,悠然遠想,有超脫世俗之志。《賞譽》篇所記許掾與簡文的清談、《文學》篇所記王丞相與殷中軍的清談,都終日不散,通霄達旦,等等。總之,縱酒放達,醉生夢死,適意而行,任誕不羈,故作鎮靜,喜怒不形于色,高談玄理,追求虛靜超然,既或身擔要職也不務世事,羨慕隱逸,以“朝隱”為高,能賞風景,好游山水等,便是所謂的名士風度。這些風流自賞的情態,劉義慶都是津津樂道,極力肯定的。《世說新語》中的有些作品客觀上暴露了豪門貴族的腐化侈奢生活和殘忍兇惡的本性。如《汰侈》篇所記石崇與王愷斗富;石崇宴客斬美人;王武子用人乳喂豬。《儉嗇》篇所記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和他的慳吝;郗鑒“大聚斂,有錢數十萬”。《客止》篇所記曹操“捉刀立床頭”,追殺匈奴使節。《尤悔》篇所記曹丕毒死曹彰,又欲害曹植等。《世說新語》中有些故事也表彰了一些具有某種善良品質的優秀人物,和一些人物的較好的行為。如《德行》篇所記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蔑視金錢與權貴。荀巨伯“寧以我身,代友人命”,具有重義輕生的品格。殷仲堪雖“得登枝”,依然不忘“貧者士之常”。《言語》篇所記王導,不忘“戮力王室,克復神州”,具有愛國熱忱。《政事》篇所記陶侃“性檢厲,勤于事”。《方正》篇所記何充富于正義感,敢于當面駁斥權勢者王敦。《識鑒》篇所載郗超“不以愛憎匿善”。《自新》篇記周處改過自新。《簡傲》篇記嵇康對司馬昭的黨羽鐘會公然表示冷淡并直言相譏。王羲之“坦腹臥”,以“如不聞”的態度對待郗太傅選婿,不慕權門,不持虛假,等。上面這些記述在全書中雖不多,但在今天卻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世說新語》在藝術上具有較高的成就。它能用人物的只言片語或幾個小動作就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傳神地刻劃出來。《言語》篇“新亭對泣”一則,通過王導的一句話,就表現了他難得的愛國思想。《德行》篇“管、華絕交”一則,精當地選取了兩個富有特征性的細節,就分明展現了管、華兩人在對待金錢權貴方面的不同態度。《世說新語》還能把記言和記事巧妙地結合起來。《德行》篇“阮光祿焚車”,將阮光祿聽到有人不敢開口借車后的感嘆之言同他斷然焚車之事緊相結合,顯示了主人公樂于助人的品格。《世說新語》刻劃人物形象,善于采取多種表現手法。如對比的手法。《簡傲》篇“東床坦腹”一則,通過王家“諸郎”“咸自矜持”和王羲之“在床上坦腹臥,如不聞”兩種行為表現的對比,表現了王羲之的特殊風度和高潔秉性。又如漫畫式的夸張手法。《忿狷》篇“王藍田性急”一則作者緊扣“性急”這一主要性格特征,漫化式地充分夸張地描寫王藍田吃蛋時的一系列動作,寫得幽默風趣又發人深省。再如陪襯的手法。《汰侈篇》“石、王爭豪”一節,用王愷之豪富來陪襯石崇的更豪富,具有戲劇性。《世說新語》語言高度凝練、清麗、雋永、含蓄、傳神。每則故事百字左右,少的十五、六字,多的也不過三、四百字,卻能表達出比較繁復真摯的情感,突出地表現出描寫對象的特征。如《儉嗇》篇寫王戎的貪婪僅用了“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鉆其核”這十六個字。《世說新語》對后世的影響很大。它是佚事筆記小說的先驅,也是后來小品文的典范。唐代以來以至近代摹仿它的著作不斷出現。它為后世戲曲小說提供了不少素材。有些故事被作為典故在詩詞中引用。后來的不少成語,也都出于此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