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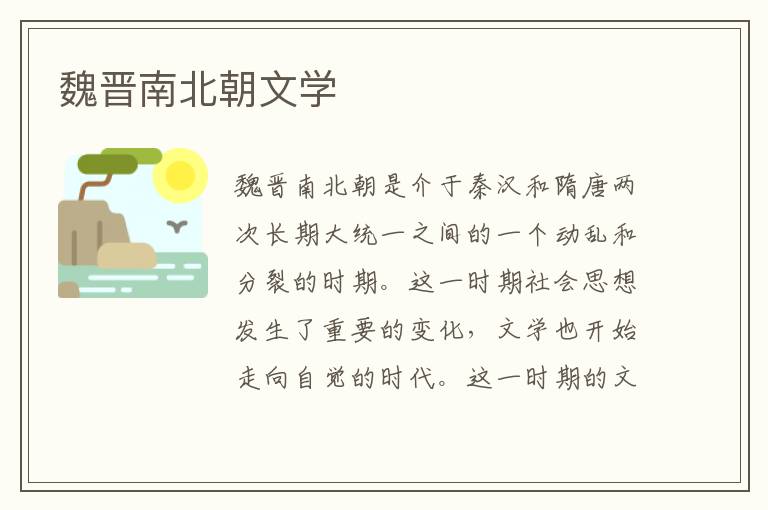
魏晉南北朝是介于秦漢和隋唐兩次長期大統一之間的一個動亂和分裂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文學也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這一時期的文學反映了這個特定歷史階段復雜的社會狀況,雖然曾有玄言詩、宮體詩這股文學逆流大肆泛濫,但總的說來,詩歌創作取得了突出重要的成就,小說、散文也有很大的發展,文學批評空前的繁榮。完全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承先啟后的十分重要的階段。
建安文學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代表作家有當時文壇的領袖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蔡琰等。他們或多或少都親身經歷了漢末黃巾起義以來軍閥割據、混戰的動亂現實,政治上有一定的抱負,對人民在戰亂中遭受的災難和痛苦也有深刻的同情,思想解放,不受儒家經典的束縛,勇于向樂府民歌學習。這就使他們能打破兩漢時期辭賦籠罩文壇的局面,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兩漢五言詩已經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寫出內容充實,感情真切,具有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優秀詩歌作品,從而形成了對后代詩歌有著深遠影響的“建安風骨”這一優良傳統。曹魏王朝后期,代表豪門地主勢力的司馬氏同日趨腐敗的曹魏統治者展開了激烈的奪權斗爭,政治異常黑暗恐怖。清談玄理之風興起,道家思想風行。正始文學就產生于這樣的現實條件之下,其代表作家為阮籍和嵇康。他們大力提倡老莊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對抗司馬氏鼓吹的虛偽的“名教”,在他們的詩歌、散文創作中,或曲折或直接地對黑暗現實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和反抗,流露了憂慮人生禍福和向往超現實的自然境界的情緒。他們的詩歌雖然還具有建安時代的慷慨之氣,走著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但詩風已與建安詩歌迥異了。
兩晉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權。曹魏以來施行的九品中正制,至西晉時,已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勢。由于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文學創作遠離社會生活,內容貧乏,片面追求辭藻和對偶,從西晉初就逐漸由現實主義走上了形式主義道路。到了號稱“勃爾復興”的太康時代,形式主義詩風更加盛行。陸機是這一文風的代表。這時只有杰出的詩人左思,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的傳統,在他的詩篇中,表示出對士族統治的憤慨,抒發了高尚的志趣和情操,寫出了具有較高現實意義,風格剛健明朗的詩篇。西晉末年,清談玄理的風氣盛行,玄言詩興起。這種“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幾乎統治了東晉詩壇。玄言詩具有宗教文學的性質,是東晉王朝門閥士族地主意識形態的代表。在玄風熾盛之時,東晉初期的郭璞在《游仙》詩中,抒發了對不合理的現實的抵觸情緒,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晉末宋初的陶淵明是這一時期成就最高的詩人,也是我國文學史上杰出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一反玄言風氣,獨樹一幟,具有樸素自然的風格,思想的主導方面是積極的。其田園詩,開創了我國詩史上的田園詩派。雖然他的詩在當時并不受人重視,但對后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南朝宋、齊、梁、陳四代,南方經濟有了非常顯著的發展。中國的文化重心遷移到了南方,文學的重要性也為地主階級進一步認識,這就為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南朝初期的劉宋時代,文人詩歌創作有了新的發展。從劉宋初年開始,山水詩代替了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的玄言詩。謝靈運是完成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詩人。他的詩雖還殘留著玄言的渣子,但“如芙蓉出水”,獨具特色,在詩史上影響很大。稍晚于謝靈運的鮑照,是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杰出詩人。他的詩使左思以來久已消沉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大放光輝,有力控訴了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具有比較廣闊深刻的社會內容。他的七言和雜言樂府詩,開創了七言詩體的新局面,為七言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齊、梁、陳時代的文學,由于上層統治者的倡導,一般說來,大力發展了晉代文學創作的形式主義傾向,達到了形式主義的高峰。梁陳時代出現的宮體詩,以輕艷的筆調著意描繪女性的色情,是貴族統治者荒淫無恥的宮庭生活的反映,標志著貴族文學的十分墮落。齊、梁時代產生了“永明體”詩歌。它一方面助長了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另一方面也為唐代近體律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謝朓是永明體作家中成就較高的詩人。他的詩繼謝靈運之后,在山水景物描寫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后梁代何遜、梁陳之間陰鏗等人的詩中,也有不少山水佳句。他們的山水詩雖然思想意義不大,但在藝術上還有其可取之處,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另外江淹、吳均等詩人的創作也是略有成就的。
南朝的散文創作趨向駢麗化,辭賦化。在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下,作家們對文學藝術的形式美片面極力地追求,造成了駢文突出畸形發展的局面。駢文、駢賦雖也出現了少數內容上有價值并具有獨創風格的作品,如鮑照、孔稚圭、江淹等人的一些作品,但就其主導方面來說,卻是形式主義的東西。這時期說理文、小品文、抒情小賦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魏晉南北朝時期,小說創作開始繁盛,出現了很多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前者以干寶的《搜神記》為代表,后者以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為代表。它們都粗具小說規模,標志著我國小說創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階段。文學理論批評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魏晉時代,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更把文學理論批評推向了新的更高階段,獲得了空前的具有深遠影響的成就。隨著文學批評的發展,選本和總集也相應地出現。如蕭統的《文選》、徐陵的《玉臺新詠》,都對后來有很大的影響。
在南朝文學中,以《吳歌》、《西曲》為代表的樂府民歌,特別值得我們珍視。它們幾乎都是情歌,同漢樂府民歌相比,具有顯著不同的特色。
北朝文學成就最大的是民歌。它們具有豐富深刻的現實內容,風格樸質豪放剛勁,可與南朝民歌比肩而美。《木蘭詩》是代表作。北朝文人創作總的說是消沉的。北方十六國時期,文壇幾乎一片荒蕪。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統一北方后,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特別是魏孝文帝以法令形式推行漢化,尊崇儒學,重用知識分子,使北魏后期的文學漸有起色,出現了溫子升、邢邵、魏收等作家。但他們的創作受南方文學影響較大,自己的特色不足。庾信由南入北后,他的遭遇和經歷使他這個宮體詩人的創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的創作大量抒寫了自己懷念故國和鄉土的情思,屈節仕敵的慚愧和感仿,以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風格剛健悲涼,表現了南北文風融合的趨勢。庾信不僅是北朝文人的泰斗,在整個南北朝作家中也是卓有成就的。在駢文統治南朝文壇的時候,北朝卻出現了《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幾部散文著作。它們以風格樸素著稱,同時也兼受到南朝駢麗文風的影響。《顏氏家訓》中的獨到的文學觀點也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北朝的社會生活、社會風尚與南朝不同,北朝文風同南朝文風相比,也有其特異之點。《北史·文苑傳》認為,北朝文學“詞義貞剛,重乎氣質”,“理勝其辭”,“便于實用”。這見解是頗值得我們參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