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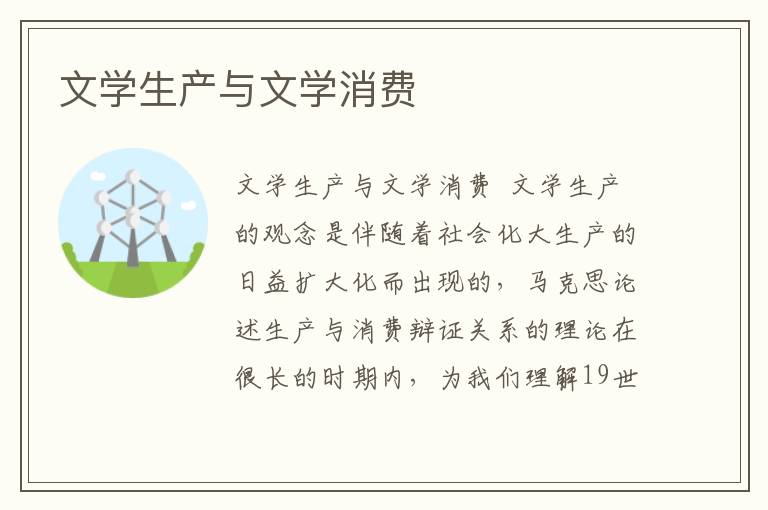
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
文學生產的觀念是伴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日益擴大化而出現的,馬克思論述生產與消費辯證關系的理論在很長的時期內,為我們理解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的文學變化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思路。
馬克思認為在理想的社會生產活動中,生產與消費是一對直接互相作用的因素,它們不僅直接就是對方,而且也經由各種中間環節互相決定、互相生產著。然而當商品社會出現后,生產與消費之間增加了流通環節,生產和消費的物品因此也不能再作為特殊的、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而存在了,相應地,它們以一種抽象物的狀態存在,即商品。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擴張,流通和分配環節日益演變成一個起決定作用的環節,成為生產和消費的主導者。正如馬克思所覺察到的,作家不再為自己和讀者寫作,他們更多地為書商寫作;他們不再關注自己作品的特殊含義,取而代之的是對其金錢價值,即抽象的普遍價值的追求。
文學成為一種“藝術生產”的形式是文學在自己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次意義最為深刻的變化,是文學的現代性轉型。
文學成為一種“藝術生產”形式的確切內涵是指,以現代圖書出版業的出現為標志,文學的創作者——作家由原來的純粹意義上的精神成果的創造者演變為現代意義上的作家,即從事“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的“生產勞動者”;而文學的成果——作品則成為一種滿足廣大讀者多元的精神需求的、在圖書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這樣,文學便兼具了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雙重性質,成為融文化科學技術、工業、商業等為一體的“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文學成為一種“藝術生產”形式是以現代圖書出版業的出現為標志和前提的,而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圖書出版業,即以活字印刷為基本手段,在短時間內大量復制和迅速發行傳遞書籍,產生廣泛而巨大的社會影響,這樣一種性質的社會生產部類或行當的產生卻為時甚晚。據美國出版史研究的權威德索爾的考證,在西歐,它的正式創始應當是在18世紀啟蒙運動的大百科全書編著時代,而成熟則是在19世紀以后,在中國,現代圖書出版業的出現和趨于繁榮更晚一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
文學成為一種“藝術生產”形式,即文學生產,給文學的接受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首先,是文學的空前大普及,使文學成為人們的閑暇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文學的社會功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得到廣泛、深入的發揮。
其次,是文學接受由傳統的審美中心、審美至上向精神需求的多元化、多層次的轉變,文學越來越成為一本大書,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適合于自己的那一頁。
再次,則是文學接受的需求的變化,使得文學的觀念泛化,出現了文學與歷史、文獻、科學、新聞、教育等相融會的現象,通俗文學、文獻小說、新新聞小說、全景文學等新的文學樣式、品種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而文學觀念的這些變化和實踐,反過來又強化和深化了文學接受的需求的變化,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提升的機制,成為推動文學發展變化的深刻而強大的內部動力,這已越來越成為我們觀察文學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視角。
但是,文學成為藝術生產的同時也受控于資本的操作之下,造成人的深度異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就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批判,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其中,阿多諾以對文化工業的批判揭示了資本對傳統文學的危害,他認為當代的文學生產已經轉變為社會化大生產式的,私人企業與國家行政結合起來,給人們營造了文化繁榮、社會化生產與個體微觀需求之間和諧發展的假象,將他們本不需要的文化產品經過產業的包裝販賣給他們,同時也削弱了人們的反思能力和意識。馬爾庫塞和弗洛姆都從現代精神分析中獲得了批判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靈感,不同的是,馬爾庫塞是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指出大眾文化和商業文化的同質化是資本主義壓抑人的新方式,它帶來的是社會與人的單向度。馬爾庫塞倡導通過詩歌激發人內心深處的、保持生命更大統一的愛欲沖動,來抵抗死亡與攻擊性的死欲沖動,前者通過經典的文學作品表達出來,而后者則表現為社會的生產性原則。弗洛姆則更多地從個體與心理學層面出發,強調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異化。
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入發展,生產過剩的矛盾日益加劇,到了20世紀中期,一些主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納“福特主義”,通過支付工人更多的工資以及給予他們更多的閑暇時間來改善勞資矛盾,但其最終后果是導致了大規模的消費活動。消費社會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將工人從勞動力轉化為消費力,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家制度,也導致了生產、流通、消費以及再分配等領域的同質化、有序化的結果,避免了經濟活動中各領域無序狀態帶來的沖突惡果。與此同時,為了完成這一同質化的序列,物品必須被進行社會性的“編碼”,因此在消費社會中,物或商品不再僅僅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的雙重性,而且還被附加上了符號價值。通過將傳統的、當下的文化符號化,符號價值連通了現實的社會等級結構與大規模的商品生產活動。
消費社會的這種符號價值特征深刻影響了文學的接受,人們購買文學作品的目的不再單純是為了閱讀,也可能是通過購買而炫耀自己的社會地位,而無須閱讀。閱讀的目的也不再單一地限制在審美上,社交、娛樂、時尚、獵奇,甚至打發時間,都可以成為閱讀的理由。另一方面,文學也以一種從未有過的廣度在大眾之中普及開來,閱讀成了人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也從以前那種消極的生產產品,變成了生產甚至社會的引導者,作品中虛構出的甚至是設計出來的場景、觀念、人際關系、風尚等,成為人們競相模仿的對象,虛構與現實通過符號價值系統融合在一起。法國學者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批判是深刻而悲觀的,他運用符號學理論改造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指出消費社會對文化的根本來源,即人的感性生活的架空的危險。在《消費社會》一書的結尾他談到,當國家權力、生產、市場與社會文化徹底同質化之后,人們其實只能訴諸一種無緣由的暴力。在他看來,這種同質化是通過取消商品的使用價值,將商品價值符號化,以及符號化之后的價值社會等級化一系列過程來完成的。按照這一邏輯,符號系統生產或指派出來的需求,取代了人們“真正的”自然需求,國家化甚至全球化的資本綁架了個體的自由意志。可以說,鮑德里亞的這種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都是站在啟蒙立場上對文化消費現象的審視。
我們看到,誠如啟蒙批判者們所言,文化消費產生于資本的同質化運程;但另一方面,通過消費,文化也給人們帶來了新的生活體驗,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這種體驗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交往性、非封閉性、主動性的特點,文學的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寫作中去,寫作的篇幅越來越短小、越來越需要他人的關注,等等。這意味著我們開始從啟蒙主體那種封閉、偏執、憂郁的自我中走出來,拋棄了一部小說即一個世界的自閉帶來的深度;同時每個人既有堅持自我的自由,也并非僅僅從自我出發、以自我標準來衡量周圍以至世界,文學更多地成了交往的媒介,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啟蒙主體。
[原典選讀]
從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上說,生產勞動是雇傭勞動,它同資本的可變部分(花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相交換,不僅把這部分資本(也就是自己勞動能力的價值)再生產出來,而且,除此以外,還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僅僅由于這一點,商品或貨幣才轉化為資本,才作為資本生產出來。只有生產資本的雇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這就是說,雇傭勞動把花在它身上的價值額以增大了的數額再生產出來,換句話說,它歸還的勞動大于它以工資形式取得的勞動。因而,只有創造的價值大于本身價值的勞動能力才是生產的)
——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6.
這里,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給生產勞動下了定義,亞當·斯密在這里觸及了問題的本質,抓住了要領。他的巨大科學功績之一(如馬爾薩斯正確指出的,斯密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批判中所做的區分,仍然是全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礎)就在于,他下了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這樣一個定義,也就是說,他根據這樣一種交換來給生產勞動下定義,只有通過這種交換,勞動的生產條件和一般價值即貨幣或商品,才轉化為資本(而勞動則轉化為科學意義上的雇傭勞動)。
什么是非生產勞動,因此也絕對地確定下來了。那就是不同資本交換,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資或利潤交換的勞動(當然也包括同參與分享資本家利潤者的各個項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換的勞動)。凡是在勞動一部分還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農民的農業勞動),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換(例如亞洲城市中的制造業勞動)的地方,不存在資產階級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和雇傭勞動。因此,這些定義不是從勞動和物質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產品的性質,不是從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的規定性)得出來的,而是從一定的社會形式,從這個勞動借以實現的社會生產關系得出來的。例如一個演員,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資本家(劇院老板)雇用,他償還給資本家的勞動,多于他以工資形式從資本家那里取得的勞動,那么,他就是生產勞動者;而一個縫補工,他來到資本家家里,給資本家縫補褲子,只為資本家創造使用價值,他就是非生產勞動者。前者的勞動同資本交換,后者的勞動同收入交換。前一種勞動創造剩余價值;在后一種勞動中收入被消費了。
——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1-142.
生產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對他本人來說是商品。非生產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也是這樣。但是,生產勞動者為他的勞動能力的買者生產商品。而非生產勞動者為買者生產的只是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使用價值,而決不是商品。非生產勞動者的特點是,他不為自己的買者生產商品,卻從買者那里獲得商品。
——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5.
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
成為希臘人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藝術)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系的觀點,能夠同走錠精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并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針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對自然的神話態度,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夠同火藥和鉛彈并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并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并不矛盾。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并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0.
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可是同時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中介運動。生產中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中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
(1)因為產品只是在消費中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其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于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后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在于它是物化的活動,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
(2)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與此相應,就生產方面來說:
(1)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在這方面生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
(2)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象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中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在客體方面,而且在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
(3)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狀態和直接狀態——如果消費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野狀態的結果——那么消費本身作為動力就靠對象來作中介。消費對于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于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0.
舊社會的一切關系脫去了神圣的外衣,因為它們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同樣,一切所謂最高尚的勞動——腦力勞動、藝術勞動等——都變成了交易的對象,并因此失去了從前的榮譽。全體牧師、醫生、律師等,從而宗教、法學等,都只是根據他們的商業價值來估價了,這是多么巨大的進步啊。
——馬克思.工資[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59-660.
于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志,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但是,資本的不變趨勢一方面是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如果它在第一個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這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余勞動。
這個矛盾越發展,下述情況就越明顯: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余勞動。當他們已經這樣做的時候——這樣一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一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那時,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勞動時間作為財富的尺度,這表明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同剩余勞動時間相對立并且是由于這種對立而存在的,或者說,個人的全部時間都成為勞動時間,從而使個人降到僅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們屬于勞動。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下冊[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1-222.
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作用于勞動生產力。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節約勞動時間可以看作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下冊[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
正是由于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并加以進一步發展。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0.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即體力的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
利益群體總喜歡從技術的角度來解釋文化工業。據說,正因為千百萬人參與了這一再生產過程,所以這種再生產不僅是必需的,而且無論何地都需要用統一的需求來滿足統一的產品。人們經常從技術的角度出發,認為少數的生產中心與大量分散的消費者之間的對立,需要用管理所決定的組織和計劃來解決。而且,各種生產標準也首先是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基礎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順順當當地接受這些標準。結果,在這種統一的體系中,制造與上述能夠產生反作用的需求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循環,而且越演越烈。然而,卻沒有人提出,技術用來獲得支配社會的權力的基礎,正是那些支配社會的最強大的經濟權力。技術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會異化于自身的強制本性。汽車、炸彈和電影將所有事物都聯成了一個整體,直到它們所包含的夷平因素演變成一種邪惡的力量。文化工業的技術,通過祛除掉社會勞動和社會系統這兩種邏輯之間的區別,實現了標準化和大眾生產。這一切,并不是技術運動規律所產的結果,而是由今天經濟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需求不再受中央控制了,相反,它為個人意識的控制作用所約束。電話和廣播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作用,這簡直可以說是一種飛躍。電話還依然可以使每個人成為一個主體,使每個主體成為自由的主體。而廣播則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參與者都變成了聽眾,使所有聽眾都被迫去收聽幾乎完全雷同的節目。人們還沒有設計出解答器,私人不可以隨便設立電臺。因此,所有人都被納入到了真偽難辨的“業余愛好者”的范圍之中,而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組織形式。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109.
一個人只要有了閑暇時間,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給他的產品。康德的形式主義還依然期待個人的作用,在他看來,個人完全可以在各種各樣的感性經驗與基本概念之間建立一定的聯系;然而,工業卻掠奪了個人的這種作用。一旦它首先為消費者提供了服務,就會將消費者圖式化。康德認為,心靈中有一種秘密機制,能夠對直接的意圖作出籌劃,并借此方式使其切合于純粹理性的體系。然而在今天,這種秘密已經被揭穿了。如果說這種機制所針對的是所有表象,那么這些表象卻是由那些可以用來支持經驗數據的機制,或者說是文化工業計劃好了的,事實上,社會權力對文化工業產生了強制作用,盡管我們始終在使這種權力理性化,但它依然是非理性的;不僅如此,商業機構也擁有著這種我們無法擺脫的力量,因而使人們對這種控制作用產生了一種人為的印象。這樣,再也沒有什么可供消費者分類的東西了。為大眾的藝術已經粉碎了人們的夢想。……對大眾意識來說,一切也都是從制造商們的意識中來的。不但顛來倒去的流行歌曲、電影明星和肥皂劇具有僵化不變的模式,而且娛樂本身的特定內容也是從這里產生出來的,它的變化也不過是表面上的變化……
在文化工業中,這種模仿最終變成了絕對的模仿。一切業已消失,僅僅剩下了風格,于是,文化工業戳穿了風格的秘密:即對社會等級秩序的遵從。……文化已經變成了一種很普通的說法,已經被帶進了行政領域,具有了圖式化、索引和分類的涵義。很明顯,這也是一種工業化,結果,依據這種文化觀念,文化已經變成了歸類活動。所有知識生產領域也采取了同樣的方式,服務于同樣的目的,從晚上下班到次日早晨上班,所有這些都占據著人們的感受,與此同時,人們在一整天的勞動過程中,也留下了這樣的印記。正是這種歸類活動,以嘲諷的方式滿足了同一文化的概念,而這一概念恰恰是人格哲學家們用來對抗大眾文化的武器。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1-118.
小說更加接近這種審美的超越性。無論以什么樣的特定“情節”和環境作為小說的主題,它那松散的文體,都能夠將現存的世界打破。卡夫卡也許是最突出的例子。在他那里,一開始,與現存現實的聯系,就被直呼事物的名字(這最終變得用詞不當)所打斷。那個名字所述說的東西,與實際存在的東西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不可調和的了。是否可以說,使人恐怖的東西正是兩者之間的實質上的同一,即兩者之間的同步?在任何情況下,這種語言都把那些虛假的面目撕破,也就是說,這種語言揭示出幻象是在現實本身之中,而不在藝術作品中。卡夫卡這類作品,就其結構本身而言是反抗性的,在它描述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可以接受的和解。
藝術這種第二層次的異化,在今日減小(如果不曾取消的話)藝術與現實之間距離的全面努力中,正在消失。這種努力注定要失敗。的確,在游擊式的戲劇舞臺上,在“隨意榨取”的詩歌中,在搖滾樂中,都存在著反抗。但是,它們的反抗依然是沒有藝術的否定力量的藝術。就其使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現實生活的一部分看,這種反抗喪失了使藝術與現存秩序對立的超越性,這種反抗仍然內在于現存秩序中……
藝術異化之器官的退化,是由物質過程造成的。社會的極權組織所造成的暴行和攻擊性已侵入那個仍能體驗到和誠心接受藝術的極端審美性質的內外空間。它們與現實恐怖的對立非常明顯;這個對立似乎想逃離在其中無路可逃的現實。藝術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擺脫直接經驗,擺脫實際上已成為不可能的虛假的“隱私”的體驗。這也就是非行為的、非操作性的藝術:它并不“主動作用于”任何東西,而是反省和記憶,也即是夢幻般的承諾。然而,夢幻必須成為變革的力量,而不只是去夢想人類的環境條件;夢幻必須成為政治力量,假如藝術在歷史的余暉中夢寐以求解放,那么,通過革命去實現夢想就一定是可能的——超現實主義的綱領,就仍然有存在的理由。文化革命是否證明了這種可能?
——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M].李小兵,譯.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60-162.
在勞動生產率這樣增長和商品不斷越來越充裕的基礎上,開始了一種對人們的意識和下意識的操縱和擺布,這已經成為近代資本主義最必不可缺少的控制結構之一。新的需要被一次又一次地渲染起來,煽動人們去購買最新的商品,使他們相信自己確實需要它們,而這種需要可以從這些商品中得到滿足。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人們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
——馬爾庫塞,等.革命還是改良[M].帥鵬,譯.北京:外文出版局,1979:54.
人民在他們的商品中識別出自身;他們在他們的汽車、高保真音響設備、錯層式房屋、廚房設備中找到自己的靈魂。那種使個人依附于他的社會的根本機制已經變化了,社會控制錨定在它已產生的新需求上。
——馬爾庫塞.單間度的人[M].張峰,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9.
高生產和高消費處處都成了最終目的。消費的數字成為進步的標準。結果,在工業化的國家里,人本身越來越成為一個貪婪的、被動的消費者。物品不是用來為人服務,相反,人卻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個生產者和消費者。
——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M].張燕,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74.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把人貶斥到成為機器的附件,被它的節奏與需求所統治。它把人變成消費機器,變成徹底的消費者,它唯一的目標就是擁有更多的東西,使用更多的東西。這一個社會制造了許多無用的東西,也同樣制造了許多無用的人。人,由于成了生產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上的齒,他已經變成了一件東西,而不再是人。他把他的時間花費在做他所不感興趣的事情上,伴著他所不感興趣的人,制造他不感興趣的東西。而當他閑著的時候,他就去消費,他是一個張著大嘴的永恒吸乳兒,不用花多大力氣,把工業所強迫他接受的東西——香煙、酒、電影、電視、體育運動、文章,一古腦兒地“裝進來”。
——黃頌杰.弗洛姆著作精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77-478.
倘若社會的經濟和政治領域要服從于人的發展的話,那么,新社會的模式必須是由擺脫了異化的、具有存在傾向的個人的需求所決定。就是說,人既不能生活在非人的貧困中——這依然是大多數人民的重要問題——也不能被迫成為像富裕的工業社會那樣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所制約的消費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要求不斷地發展生產,因而要求不斷地擴大消費。如果人類要獲得自由,不再通過病態的消費來維持工業的發展的話,那就必須在經濟體系方面進行一場根本的改革;我們必須結束目前的這種狀況,即僅僅以不健康的人為代價才換取了一種健全的經濟。我們的任務是要為健康的人民確立一種健全的經濟。
——弗洛姆.生命之愛[M].羅原,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9-10.
消費的過程應該是一種有意義的、有人性的、有創造性的體驗。但是在我們的文化中,這一點是太少了。消費在本質上僅僅是對人為的刺激所激起的怪誕的滿足,僅僅是一種和我們具體的、真正的自我相異化的離奇想象的把戲。
——弗洛姆.孤獨的人:現代社會中的異化[J].哲學譯叢,1981(4):71.
國家的職能是為健康的消費確定種種規范,以反對病態的、低質量的消費……
……我們有必要確定哪些需求根源于我們的有機體;哪些需求則是文化發展的產物;哪些又是個人成長的體現;哪些需求是人為的,是由工業社會強加給個人的;哪些需求“使人積極進取”;哪些需求“使人消極頹廢”;哪些是由病理決定的,哪些則根源于精神的健康。
政府可以通過給予令人滿意的商品的生產和服務設施以補貼的辦法來大大推進這一教育過程,同時要開展一場大規模的宣傳健康消費的教育運動來配合這些努力。可以預料,只要各方共同努力,激起人們健康消費的欲望,消費模式是可以改變的。
——黃頌杰.弗洛姆著作精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47-648.
文學可以是一件人工產品,一種社會意識的產物,一種世界觀;但同時也是一種制造業。書籍不止是有意義的結構,也是出版商為利潤銷售市場的商品。戲劇不止是文學腳本的集成;它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商業,雇傭一些人(作家、導演、演員、舞臺設計人員)產生為觀眾所消費的、能賺錢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個人思想結構的調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傭的工人,去生產能賣錢的商品。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說,“作家所以是生產勞動者,并不是因為他生產出觀眾,而是因為他使出版商發財,也就是說,他為薪金而生產勞動。”
……藝術可以如恩格斯所說,是與經濟基礎關系最為“間接”的社會生產,但是從另一意義上也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它像別的東西一樣,是一種經濟方面的實踐,一類商品的生產……我在這一章將提到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都理解這一事實,即藝術是一種社會生產的形式,就是說,他們并不將它看成一個表面的事實,交由文學社會學家去處理,而是認為它對決定藝術本身的性質有著緊密的關系。這些批評家——我主要指瓦爾特·本雅明和布萊希特——認為藝術首先是一種社會實踐,而不是供學院式解剖的對象。我們可以視文學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活動,一種與其它形式并存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生產的形式。
——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文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65-66.
如何說明藝術中的“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即作為生產的藝術與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之間的關系,依我看來,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當前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文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81.
增長的矛盾之一是,它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激發了需求。不過,兩者形成的節奏并不一致——創造財富的節奏與工業經濟的生產力有關,而激發需求的節奏則隨社會區分邏輯的變化而變化。但是,由增長所“解放”出來的需求(即由工業體系依據自身受限制的內在邏輯所產生的)的自下而上的、不可逆轉的機動性,具有其自身的活力。它與所謂為滿足它的物質與文化財富而產生的活力不盡相同……
作為社會存在(也就是說,能產生感覺,在價值上相對于其他人),人的“需求”是沒有限制的。物的量的吸收是有限的,消化系統是有限的,但物的文化系統則是不確定的。相對來說,它還是個無關緊要的系統。廣告的竅門和戰略性價值就在于此:通過他人來激起每個人對物化社會的神話產生欲望。它從不與單個人說話,而是在區分性的關系中瞄準他,好似要捕獲其“深層的”動機。它的行為方式總是富有戲劇性的,也就是說,它總是在閱讀和解釋過程中,在創建過程中,把親近的人、團體以及整個等級社會召喚到一起。
……由于這種競爭性的需求和生產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壓力,由于這種匱乏的壓力,由于這種“心理貧困化”,生產秩序安排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適應它的需求產生并得到“滿足”罷了。在物質增長的范圍里,依據這種邏輯,沒有也不可能有獨立的需求,只有增長的需求。在體系的內部,隔絕的目的是沒有位置的,只有體系的目的才有位置。加爾布雷思、貝爾郎特·德·朱納韋爾等所指出的各種功能失調是合乎邏輯的。機車和高速公路是體系的一種需求,這一點幾乎是毫無疑問的,大學的“民主化”與汽車生產實際是一回事。因為體系只為自己的需求而生產,所以,它就更系統地以個人需求作為擋箭牌。
——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51-54.
在種姓社會、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即在殘忍的社會,符號數量有限,傳播范圍也有限,每個符號都有自己的完整禁忌價值,每個符號都是種姓、氏族或個人之間的相互義務:因此它們不是任意的。符號的任意性開始于能指不再用不可逾越的相互性連接兩個人,而是指向一個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的時候,這個所指是真實世界的公分母,對它而言,任何人都不再有義務。
這是強制符號的終結,是獲得解放的符號的統治,所有階級都可以沒有區別地玩弄符號。競爭的民主接替了法定秩序特有的符號內婚制。這樣人們就同階級之間名望價值/符號的變遷一起,必然地進入仿造。因為,人們從符號受到限制的秩序(一種禁忌在打擊符號的“自由”生產),過渡到了符號的按需增生。但這種增生的符號與那種有限傳播的強制符號不再有任何關系:前者是后者的仿造,但這種仿造不是通過“原型”的變性,而是通過材料的延伸,以前這種材料的全部清晰性都來自于那種打擊它的限制。現代符號是不加區分的(它從此只是競爭的),它擺脫了一切束縛,可以普遍使用,但它仍然在模擬必然性,裝出與世界有聯系的樣子。現代符號在夢想從前的符號,可能非常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的真實參照和一種義務:它僅僅找到了一個理由,它的生存所依賴的這個參照理由,這種真實,這種“自然”。不過這種指示性聯系從此只是象征義務的仿象:它從此只能生產中性價值,即客觀世界中相互交換的價值。符號在這里的命運和勞動相同。“自由”勞動者的自由僅僅是生產等價關系的自由——“獲得解放而自由”的符號的自由僅僅是生產等價所指的自由。
——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M].車槿山,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6:68-69.
符號/價值是被某種特定社會勞動所生產出來的。但是差異的生產,以及差異性等級體系的生產,都不能與對剩余價值的剝削相混淆,同時這些生產也不是以它為原因。在差異的生產與剩余價值的生產之間,還存在著另一種類型的勞動,正是它將經濟價值與剩余價值轉換為符號/價值:這一過程依據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交換,它是一種奢侈(somptuaire)的運作,是一種消耗(consumation),或者是一種超越了經濟的價值。然而,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它也產生剩余價值:統治(domination),這種統治不能與經濟的特權或利益混淆起來。后者只是政治運作最初的物質跳板,這種政治運作包括了通過符號所實現的權力轉換。統治由此與經濟權力相連,但它不是自發地或者神秘地從其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在對經濟價值的修正中產生出來。……正是由于忽略了符號生產的社會勞動,才使得意識形態產生了它的超越性,符號和文化似乎都隱藏于“拜物教”之中,神秘地與商品的拜物教等同起來,并相伴而生。
符號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理論家鳳毛麟角。他們被馬克思主義(或者新馬克思主義)中暴力革命者的分析所驅逐、掩蓋。凡勃倫與戈布羅(Goblot)是兩位對階級進行文化分析的先驅,他們都超越了生產力的“唯物辯證法”,轉而去考察一種奢侈價值的邏輯,通過它的編碼而賦予了統治階級以霸權并將其永久化了。
——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5.
經濟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能指/所指
使用價值和所指并不分別與交換價值和能指有相等的分量。在我們看來,使用價值與所指擁有戰術上的價值(valeur tactique),而交換價值和能指則具有戰略上的價值(valeur stratégique)。體系就是由這功能性的兩極構造的,但這兩極之間存在著等級差別。其中交換價值和能指處于明顯的支配地位。使用價值和需要只是交換價值的一種實現。所指(以及指涉物)只是能指的一種實現(我們還會回到這一點)。兩者都不是交換價值或者能指在它們的符碼中可以表達或者闡明的一種擁有自主性的現實。最終,它們不過是被交換價值和能指的游戲所產生出來的擬真模型(modèles de simulation)。它們為后者提供了真實的、活生生的、具體的保障;然而,交換價值和能指同時以其為體系的存在,而用它們的整個邏輯來代替由使用價值和所指所保證的客觀的真實……
——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