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材料的運用《選材的要求》文學(xué)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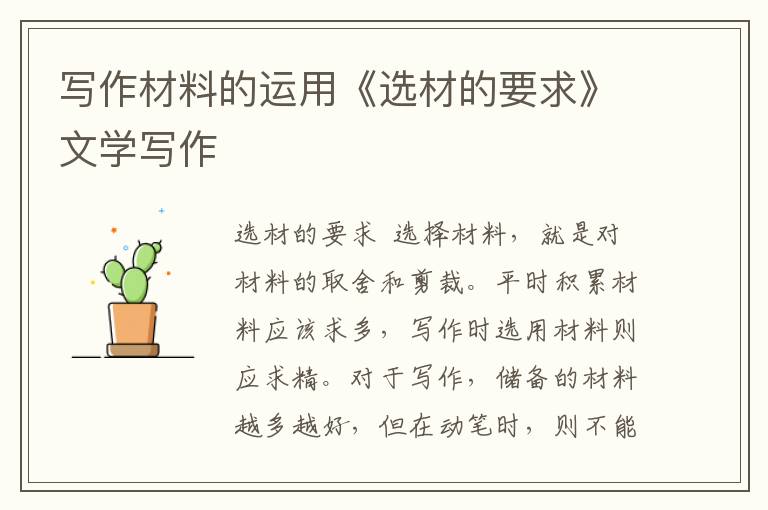
選材的要求
選擇材料,就是對材料的取舍和剪裁。平時積累材料應(yīng)該求多,寫作時選用材料則應(yīng)求精。對于寫作,儲備的材料越多越好,但在動筆時,則不能兼容并蓄,把所儲備的某類素材都寫進某篇作品中去,而應(yīng)對已有素材進行必要的取舍和剪裁。取舍和剪裁材料并非易事,袁枚認為“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難”,原因正在于儲備愈多便愈難以優(yōu)選。所謂“作色原姿妙選材,必須結(jié)構(gòu)匠心裁”,沒有匠心選材,不能巧妙選材,不具匠心剪裁,所用之材很難得當和得力。一篇作品只需要容納與主題有關(guān)的、必要的材料,關(guān)系不大的、可有可無的、多余的材料必須舍去。在作品中,主題和題材互為作用、和諧融合。主題從題材中提煉出來,又反過來統(tǒng)帥題材;題材受主題支配,同時又支撐和表現(xiàn)主題。因此,動筆時選用材料要嚴,剪裁要恰當,對準備的素材必須進行鑒別、取舍和加工,使所選的材料能成為作品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
選擇寫作材料,應(yīng)符合以下四點要求。
一、圍繞作品的主題選材
任何作品的內(nèi)容都是為了體現(xiàn)作者的意圖而被寫進作品,作為構(gòu)成作品內(nèi)容的題材自然肩負著作品立意的使命。圍繞主題選擇,是選材最根本的要求,也是取舍材料的主要依據(jù)。陳骙論詩選材時說:“文之作也,以載事為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為工。”他認為動筆作文的時候,選用材料是件困難的事;一旦被選用于文章的材料,就要能充分發(fā)揮“蓄意”(蘊含文章的立意)的功用。取舍加工素材,不能因為其來之不易,就不管作品的主題是否需要,是否有利于表現(xiàn)主題和增加作品的感染力,而將不必要的題材塞進作品。根據(jù)表現(xiàn)主題的需要,作者應(yīng)將最能蘊含、突出、烘托主題的題材用進作品中,將無關(guān)的、多余的刪去,即使這些題材是作者感興趣的、來之不易的,也要忍痛割愛。而這一點往往是作者不易做到的。白居易曾指出一般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通病:“凡人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裁,或失于繁多。”游離主題的題材多了,不僅使作品出現(xiàn)繁碎蕪雜的內(nèi)容,更重要的是會分散、削弱甚至破壞作品的立意,使作者的意圖難以表達。因此,選用題材時,不能“私于立是”,而應(yīng)圍繞主題的需要來考慮材料的取舍和安排。我們以美國著名的“極簡主義”小說家雷蒙德·卡佛的小說《大眾力學(xué)》為例來分析。
那天一大早就變天了,雪開始溶化成一攤攤臟水,一條條污痕從面對后院那扇及肩的小窗戶流下來。車子駛過外面街上的爛泥,外面的天色漸漸轉(zhuǎn)暗,里面也漸漸暗下來了。她走到臥室門邊時,他正在里面往箱子里塞衣服。我真高興你要走了!我真高興你要走了!她說。你聽到了嗎?他繼續(xù)把東西放到箱子里。狗娘養(yǎng)的!我真高興你要走了!她哭了起來。你連看都不看我一下嗎?然后她看見床上那張嬰兒的照片,便拿了起來。他看著她,她擦擦眼睛,瞪著他看,然后轉(zhuǎn)身走回客廳。拿回來,他說。收拾你的東西,然后滾蛋,她說。他沒有回答。他扣緊箱子,穿上大衣,關(guān)燈之前并環(huán)視臥室一周,然后走進客廳。他站在小廚房的門口,抱著嬰兒。我要孩子,他說。你瘋啦?沒有,可是我要孩子。我會找人來處理關(guān)于小孩的事情。你別想碰這個孩子,她說。小孩開始哭,她掀開蓋在他頭上的毯子。喔,喔,她說,你看他。他朝她走了過去。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說。她向后退了一步,躲進廚房。我要孩子。滾開!她轉(zhuǎn)身,試圖抱著小孩躲到爐子后面的角落。但是他走上來,手伸過爐子上方,緊緊抓住孩子。放開他,他說。你滾,你滾!她大叫。小孩的臉變得通紅,并且尖聲大哭。兩人搶來奪去時撞掉了爐子后面的花盆。他把她逼到墻邊,企圖掰開她緊握的雙臂,他抓住孩子,用盡力氣推撞。放開他,他說。別這樣,她說。你會傷到孩子,她說。我不會傷到孩子,他說。廚房的窗戶沒有任何光線,在幾近全然的黑暗中,他一手掰開她握得緊緊的手指,另一只手把哭叫的小孩緊緊挾在腋下。她覺得自己的手指被迫張開。她覺得孩子離她而去。不!她的手松開時尖叫一聲。她要擁有這個小孩。她抓住小孩的一只手臂,扣住他的手腕并將身體往后傾。但他不放手。他覺得小孩從他手中溜走,于是很用力地向后拉,這件事就用這種方式解決了。
(選自雷蒙德·卡弗《當我們談?wù)搻矍闀r我們談?wù)撌裁础罚g林出版社,2010年版)
卡佛簡約的寫作手法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逼迫讀者改變閱讀方式。那些不完整的情節(jié),似乎沒有結(jié)局的故事迫使讀者思考,更加關(guān)心那些沒有寫出來的東西,并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卡佛的簡化不是表面的修辭,而是一種世界觀,是一個表達對他自身和他所寫那個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在人的生命中,在真實的生活處境中,是存在著巨大的沉默的。一種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傷痛,只好放到沉默里。
二、選擇典型的題材
選擇題材,要盡可能選擇典型題材。所謂典型題材,就是在同類題材中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事物的特征和本質(zhì),使作品內(nèi)容最具表現(xiàn)力的題材。一般說來,事物的普遍性是通過個別性表現(xiàn)出來的,沒有個別性,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典型題材應(yīng)是“個別”的,具有“個性”的題材。同時,還要認識到:典型題材并非一定是影響時勢的風云人物和人們關(guān)注的大事,能夠啟迪人們善待人生的凡人小事也可作為典型題材。要求選擇典型題材,實際上是要求對題材的優(yōu)選,即從同類材料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題材。需要說明的是,強調(diào)典型材料,是指在同類題材中的優(yōu)化;提出反映生活本質(zhì),但這不能框式一切材料;要求個別表現(xiàn)一般,但并不是指所有個性都有共性;作者選材時,應(yīng)從具有典型的個性材料入手,盡可能生動地、形象地、新穎地、有表現(xiàn)力地體現(xiàn)自己的構(gòu)思和立意。
選材時應(yīng)該處理好題材的個性與共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典型性與一般性的關(guān)系。過去的教材中只強調(diào)典型性,使作者在選材時腦子里首先出現(xiàn)的是“這個題材有沒有代表性?”由于這一條的約束,使作者漏掉和放棄生動感人的個別特殊材料(這些個別特殊材料被看作是沒有代表性的)。我們認為,在選材時不僅要注重選擇那些有代表性的典型題材,也要留心那些有表現(xiàn)力的個別特殊的題材。對這類題材,我們先不要去考慮它是不是有典型意義,是不是有代表性,而是首先看它有沒有表現(xiàn)力,即能否最恰當生動地說明題旨。有時題材并不具有典型意義,但是它非常獨特,很有表現(xiàn)力。試看美國小說家布赫瓦爾德的小說《爸爸最值錢》。
一天,我從兒子房間門口經(jīng)過,聽見他正在打字。
“想寫點什么呢?”我問他。
“正在寫回憶錄,描述做你兒子的感受。”
聽了他的話,我的心里甜絲絲的,“寫吧,但愿在書中我的形象還不壞。”
“放心吧,錯不了!”他說,“嗨,爸,商量件事。你把我關(guān)進牛棚,用你的皮帶抽我,像這樣的事,我應(yīng)該在書中寫幾次啊?”
這使我愕然。“我從未把你關(guān)進牛棚,也沒有用皮帶抽你啊!再說,我們家壓根兒也沒有牛棚。”
“我的編輯說,要想使書有銷路,我應(yīng)該描述諸如此類的事:當我做錯事的時候,你狠狠地揍我,繼而又把我關(guān)進廁所。”
“可我從來沒有把你關(guān)起來啊!”“那是事實。但編輯指望我的故事能使讀者大開眼界,就像加里·克羅斯比和克里斯蒂娜·克勞索德寫的關(guān)于他們父母的故事那樣。他認為讀者想了解你的私生活——你的廬山真面目。現(xiàn)在兒輩們都在寫這方面的書,而且都是暢銷貨。假如我也把你描述成一個墮落的父親,你不會反對吧?”
“你一定要這樣做嗎?”
“是的,必須如此。我已經(jīng)預(yù)支了一萬美元,他們的條件是我必須揭露你的隱私。你可以讀一讀我寫的第二章。內(nèi)容嘛,是你在一次演講臺上鬧出了大笑話,會后你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中,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從床上轟了起來,逼著我們刷地板。”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從來沒有這么干過。”
“哎呀,我的爸爸!這只不過是一本書。我的編輯喜歡這樣的書,第三章他最中意了。那一章中,你對母親拳打腳踢,大耍威風。”
“什么?我揍了你母親?”
“我并不是說你真的傷害了母親。不過,我還寫了我們幾個小孩慣于藏在毛毯底下,這樣我們就聽不到母親挨打時那種聲嘶力竭的叫聲了。”
“天啊,我從未打過你的母親啊!”
“可我不能這么照搬事實。編輯說過,成年人是不會花十五六美元去買《桑尼布魯克農(nóng)場的麗貝卡》的。”
“好吧,就算我用皮帶抽了你,揍了你母親。除此我還做了些什么?”
“對了,我正在第四章中寫你拈花惹草的事呢。假如我寫你常在凌晨三點鐘把那些歌舞女郎領(lǐng)進家門,你說人們會不會相信?”
“我敢肯定,人們會相信的。但即使這是一本暢銷書,難道你不認為這太離譜了嗎?”。
“這是編輯的主意。平時,你沒有粗暴待人的惡名聲,這樣一寫,讀者才會真正感到驚奇、刺激。對我不會有什么損害的。”
“對你是沒什么損害,但對我可如同下地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沖他吼叫起來,“那我究竟做了點好事沒有?”
“有。其中有一章我特別寫到你為我買了第一輛自行車,但編輯讓我刪去了。因為我也寫了圣誕節(jié)的事。那次,我跟你頂嘴,氣得你把一碗土豆泥統(tǒng)統(tǒng)扣在我的腦門上。編輯說這樣的兩碼事寫在一起是會把讀者搞糊涂的。”
“那你為什么不寫僅僅因為你數(shù)學(xué)考試得了‘良好’,我就用冷水把你從頭淋到腳?”
“你說得好。那我就這樣寫,一次我得肺炎住院,你這位當爸爸的甚至連看都不看我。”
“看來你是想把你的父親以一萬美元出賣了?”
“不僅是為了錢。編輯說如果我把一切都捅出去,那就連巴巴拉·瓦爾德斯都會在他主持的電視節(jié)目里采訪我,那時我就再也不用依靠你來生活了。”
“好吧,如果這本書真會帶給你那么多的好處,你就干下去吧。要我?guī)兔幔俊?/p>
“太好了,就一件事。你能不能給我買一臺文字加工機?如果我能提高打字的速度,這本書就能在圣誕節(jié)前完稿。一旦我的代理人把這本書的版權(quán)交給電影制片商,我就立即把錢還給你。”
(選自《微型小說選家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這篇小說中的“兒子”為了獲得金錢,不惜昧著良心,違背天倫,在“回憶錄”中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實去污蔑損毀父親的形象。這樣的“兒子”極為少見,是不具代表性的,從所謂的“典型”理論來看,他不應(yīng)是“典型”。但事實上,生活中就實實在在有這樣的“兒子”及像他那樣的“所作所為”存在。即便是以個別的、特殊的現(xiàn)象存在,但這種現(xiàn)象依然包含著某些做兒子的人的本性和社會生活中一些發(fā)人深省的道理。在金錢社會中,親人關(guān)系及親情被腐蝕,被扭曲和踐踏的現(xiàn)象是不可避免的。《爸爸最值錢》中的“兒子”及其所作所為無疑是有很強的表現(xiàn)力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看待個別特殊的題材時,腦子里先不要有一個“是否典型”的框框,我們首先可以從感性上去判斷它的基本內(nèi)涵是否有認識作用,是否有審美價值,是否有表現(xiàn)力,過早地用“典型”“代表”的要求去框式材料,會一開始就喪失對生動的個別、特殊的材料的興趣,而放棄對這種材料的合理使用。
這里所論述的并不是降低題材的典型化要求,而是指應(yīng)怎樣看待典型材料。有代表性的、能說明一般的材料(比如人人都做得到或應(yīng)該去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該用的好題材,非一般性的、無代表性的材料(不提倡做,多數(shù)人做不到或不愿去做的事情)也可能是該用的好材料。有代表性的材料,可以包括在現(xiàn)在看來是個別的、偶然性、特殊性的材料。社會生活和一切客觀事物總是發(fā)展變化的,今天看起來沒有代表性的事物,明天也許就會有代表性。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作品中表現(xiàn)出作者獨到的認識和情感傾向。
我們強調(diào)材料的典型性,絕不是要求所寫題材都具有共性能夠統(tǒng)一個性的特點,而是指個性與共性的融合,而這種融合可以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所以我們在處理個性與一般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典型性與共性的關(guān)系時,應(yīng)把注意的重點放在對具有個性材料的采集上。同時,對共性、一般性、普遍性不要看得太死,看得太簡單(太單一),而是應(yīng)該認識到這三性本身就包含有豐富的多種內(nèi)涵,更不能要求每個材料都具有能夠表現(xiàn)社會本質(zhì)的功能。在這里,恩格斯所說的不要讓個性消融在原則中去的論述仍是有指導(dǎo)意義的。
三、選擇真實的題材
這個問題,并不是針對所有文學(xué)作品的選材講的。小說、詩歌、戲劇等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追求的真實主要是藝術(shù)的真實。藝術(shù)真實是以生活的真實為基礎(chǔ)并高于生活的真實。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作者可以在素材的基礎(chǔ)上進行合理的想象和虛構(gòu),進行多種手段的藝術(shù)加工,對各種生活現(xiàn)象進行重新組合排列和大膽創(chuàng)造,以揭示生活的規(guī)律和本質(zhì)。但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文學(xué)作品都只追求藝術(shù)的真實而不表現(xiàn)生活的真實。比如報告文學(xué)、散文等體裁的作品,就必須追求生活本來面目的真實。
報告文學(xué)是新聞與文學(xué)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人們早已把它歸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范疇。但它所體現(xiàn)的真實主要是生活的真實而非藝術(shù)的真實。報告文學(xué)的特征首先是“報告”,其次才是“文學(xué)”。報告文學(xué)的可信性和感染力主要來自它的真實“報告”的新聞性,讀者不能接受它對所寫的人和事進行虛構(gòu)。如果在真實的題材里塞進虛構(gòu)臆造的東西,那報告文學(xué)的性質(zhì)就會改變,它的價值就會大大削弱。我國20世紀80年代曾掀起過報告文學(xué)熱,文壇上曾涌現(xiàn)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xué)作品,如《人妖之間》《地質(zhì)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中國姑娘》等。這些作品之所以強烈震撼了廣大讀者的心靈,主要在于它們反映的人和事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感人的真人真事。而20世紀90年代至今,出現(xiàn)的報告文學(xué)并不少,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冷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許多報告文學(xué)的人和事失去了真實性。不少作者受名利驅(qū)使,為達官顯貴和愿意出錢的企業(yè)家樹碑立傳,所寫的報告文學(xué)摻和了不少虛假的內(nèi)容,讓讀者大失所望,甚至極為反感。報告文學(xué)的題材一旦失去了真實性,也就失去了廣大讀者。散文也是如此。散文寫的都是真人真事及真情實感,“寫實”是散文的藝術(shù)特征之一。古今中外的散文都具有“寫實”這一特點。散文與小說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就是前者需要“寫實”,后者允許虛構(gòu)。因此,寫報告文學(xué)和散文,在選擇題材上要遵循真實的要求,不能運用虛構(gòu)的方法去任意改變事實。當然,報告文學(xué)和散文要生動感人,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也離不開文學(xué)的藝術(shù)性。這種藝術(shù)性的獲得,不是靠虛構(gòu),而是靠對真實題材合理巧妙的組合安排,加以必要的想象,對記敘、描寫、抒情、議論等多種手段的靈活運用,以優(yōu)美生動或樸實有趣的語言表達來獲得的,如干天全的《羅幺爸的桃色事件》。
生產(chǎn)隊的各色工匠中,羅幺爸的手藝最吃香。他有一手砌灶的絕活,砌的灶好燒又省柴,工費也很少,主人家給一元或五毛,他都樂呵呵地接著。社員們擺起他都很是羨慕,說他經(jīng)常有肉吃,說不準床草里還藏有五十、一百呢。那年頭,灶臺與人的“食為天”相關(guān),也與豬的“食為天”相關(guān),社員灶臺上的一口大鐵鍋既煮人食又煮豬食。每戶人家砌新灶,都要想方設(shè)法買點肉熬鍋底,一是為敬灶神求得今后的日子能吃上肉,二是為了謝砌灶的師傅。羅幺爸經(jīng)常到四鄉(xiāng)八鄰去砌灶,自然少不了油葷。我和另一位知青剛?cè)胱⌒录遥吐犎苏f我們的灶是羅幺爸砌的。這灶臺雖然比社員家的小得多,但小巧精致,灶面光潔,邊沿倒了圓角,灶墻上抹的石灰平整白凈,還用墨畫了兩條裝飾線。可惜羅幺爸沒有在我們這里聞到肉味。
羅幺爸很少下田干農(nóng)活,我們下鄉(xiāng)幾個月都沒見過他。那天澆完麥苗路過鐘家大院,見一陌生的中年人坐在門檻上翻著衣角捉蚤子,同行的社員說這人是羅幺爸。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羅幺爸”,他猛抬頭怔怔地望著我。我自報姓名,并說是新來的知青,羅幺爸霍地起身笑容滿面地喊著:“歡迎歡迎!”這時我才看清他尊容。圓球似的腦袋,胖墩墩的身段,藍布衣褲已有些黑亮,上面補了不少長針短線的布疤。敞開的胸脯顏色灰暗,只有臉上白凈紅潤。一看這模樣,就知道他是長時間只洗臉不洗澡的男人。進他屋里一看,更讓人皺眉頭。靠屋右墻一張沒有蚊帳的單人床,床上黑乎乎的大小疙瘩分不清是衣物還是被褥。床頭的米柜兼作床柜,上方貼著發(fā)黃的毛主席像,床下好幾只凌亂放著的草鞋和膠鞋。屋的左邊橫著灶臺,石灰泥層剝落的地方齜牙咧嘴地露出青磚。真沒想到,有砌灶絕活的羅幺爸竟燒著這樣的破灶。他身居寒室卻還樂觀,言語中不少豪言壯語。他說:“生產(chǎn)隊沒有人像老子這樣快活,不說別的,單說喝酒吃肉,有哪個比我多?社員別提了,就連那些龜兒當官的也沒有我一年四季打的牙祭多!”這話讓我也羨慕起他來。政府每月配給每人半斤肉,還要憑票購買。一個月的半斤肉不夠一頓吃,還有八十九頓沒有油星。聽他講回鍋肉、涼拌白肉、紅燒肉的滋味,心里直想向他拜師求藝。不過,沒把這話說出來,自己畢竟是知青,還想著今后做比砌灶更大的事。臨走時問他為啥不討老婆,他說:“討來干啥,你們年輕不懂‘男活精,女活血’,討了老婆就不能像我的身板這樣篤實,你看那些‘窮骨頭發(fā)干燒’的人,拿給婆娘弄得來像瘦猴。”這通精血與健康的道理過去從未聽過。我暗自想,怪不得那些結(jié)了婚的男社員大都皮包骨頭,走路干活都蔫梭梭的。看來,羅幺爸臉上的白里透紅不僅與他常吃肉有關(guān),與他養(yǎng)精蓄銳也有關(guān)。這次見面,羅幺爸給我留下一個身不潔心潔的印象。
不料割完麥子的時節(jié),羅幺爸就卷進了桃色事件。那天晚上月色朦朧,正在田坎上轉(zhuǎn)悠的我隱約聽到府河邊有人哭鬧,急步趕上前去。“打,打,打!打死他狗日的!”哭聲罵聲越來越近,走到河邊,見圍著一群人,不知在罵誰打誰。撥開他們,見隊里人稱“朝天辣”的春妹子一邊抹眼睛,一邊指著地上抱頭蹲著的人怒罵:“你這個老怪物,平時裝得像和尚,摸黑來偷看我,打不死你才怪呢!”
“我沒看,確實沒看。”
聽聲音,是羅幺爸。問怎么回事,旁邊鄧二爸的幺娃子憤憤地說:“春妹子在河頭洗完澡正脫光了換衣裳,羅老漢偷看不說,還想——”他吞吞吐吐沒把話說完,其他的老少爺們七嘴八舌地吼起來。
“說,你還想干啥?!”
“不承認再揍他!”
“狗日的裝憨,不說就把他脫光!”
沒待人們動手,羅幺爸連忙作揖磕頭地哀求:“脫不得脫不得,我承認看了——”
“看到啥了,是前面還是后面,是上頭還是下頭,說明白!”
“沒看清楚,只看到白晃晃的一條像個人,我就站住了。”
“你又不是雞盲眼只看到白晃晃,說,還看到啥?!”
“還看到、還看到像個女的。”
“他媽的不老實,打打!”
不忍看到羅幺爸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模樣,我勸大家都回去,明天找隊長解決這事。好在平時我與鄉(xiāng)親們的關(guān)系友善,大家給了面子。春妹子一甩水珠四濺的長發(fā),沖出人群跑了,其他人“媽的”“娘的”罵著也就散了。我扶起羅幺爸叫他回去,他抱著我的雙腿哭叫著“好兄弟,明天我來給你砌新灶。”這話讓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隊長叫我?guī)退伊_幺爸問話。在保管室里見到了羅幺爸,他浮腫的臉像個調(diào)色盤,青一塊紫一團的。我和隊長坐在一根長條凳上,羅幺爸坐在一只反扣在地的籮筐上,隊長劈頭劈腦地問:“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瘋了,嗯?!”
“想啥女人嘛,我從來不沾女人的邊。‘男活精,女活血’——”
“呸!少跟我說這些假正經(jīng)的話,你不想咋去看春妹子洗澡?”
“我哪知道她在那里洗澡,從高埂子李家吃完新灶飯,抄河邊近路回家,我看到前面白晃晃的東西以為是個鬼,嚇得腳手軟地立在哪兒,那個死女子一見我就驚風扯火地喊人,看熱鬧的龜兒子跑來就把我打一頓。”羅幺爸邊說邊用手去摸臉上發(fā)亮的腫塊。
我插話問他為什么昨晚不在現(xiàn)場說明真相,他抖動著發(fā)烏的嘴唇說:“真相?哪敢講真相,那還不把我打成糍粑坨坨。”
隊長板著臉叫羅幺爸以后走夜路小心點,揮揮手讓他走了。我很意外事情就這么簡單地了結(jié),問隊長咋給社員解釋,隊長說:“這點小事解釋個鳥,不就是晃了一眼,又沒給她弄進去。不瞞你說,我年輕時還藏在河邊芭茅中看過女人洗澡呢。”這話讓我愣了好一陣。
羅幺爸真冤。大概是為了躲難聽的流言蜚語,他悄悄離開生產(chǎn)隊,到遠地找活路去了。后來聽往隊里運化肥的拖拉機司機講,羅幺爸在外鄉(xiāng)一個寡婦家砌完灶住了好些天,那個寡婦還為他縫了一身新衣服。他放話說,過兩年回生產(chǎn)隊修新房辦喜事,請大家吃一頓九斗碗,算是給社員同志們賠罪。
(選自《干天全散文詩歌選·散文卷》,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作為虛構(gòu)的小說、戲劇等作品的題材需要藝術(shù)的真實,而不是局限于生活的真實。需要強調(diào)的是,藝術(shù)真實是不能背離生活真實的,因為它是以生活真實為基礎(chǔ)并高于生活的真實。小說、戲劇作品的題材是經(jīng)藝術(shù)加工虛構(gòu)而成的,即便是寫真人真事,也有不少虛構(gòu)的成分,但它們并不是作者脫離生活隨心所欲、胡編亂造出來的,它們表現(xiàn)的是生活中已有的、可能有的或應(yīng)該有的人和事。它們的真實,是指反映生活規(guī)律和本質(zhì)的真實。同時,它們還必須具有“細節(jié)”的真實,沒有“細節(jié)”的真實,虛構(gòu)的人和事便很難體現(xiàn)出整體的藝術(shù)真實。
四、選擇能出新意的題材
作品的題材陳舊或者雷同而又缺乏新意,讀者是不感興趣的。追求新鮮感,是人們生活中的一種正常心理。閱讀作品,希望從題材上獲得新意也是讀者審美和藝術(shù)享受的一種自然心理。正如冉欲達在談人們的欣賞習(xí)慣和藝術(shù)心理時所說:“喜新厭舊,如果從哲學(xué)和美學(xué)的角度而不是從婚姻戀愛的道德角度,它是完全正確的。……就像植物的向陽性一樣,是一種自然的與合理的社會思想傾向。”在平時的作文練習(xí)中,我們不難看到,不少同學(xué)作文中寫親人、友人和戀人以及學(xué)生時代的生活內(nèi)容大同小異,有的甚至于如出一轍,看不出新意。實際上,我們的生活豐富多彩、復(fù)雜多變,是大有新意的。社會在不斷發(fā)展,家庭生活和人際關(guān)系也在不斷變化,人的認識也在不斷提高,這一切都能給我們帶來“新意”。面對生活,我們應(yīng)具有必要的敏感性和發(fā)現(xiàn)力,要善于積累和選用那些能出新意的寫作題材。這樣寫出來的作文才能讓人耳目一新,看到作者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和感受,也才能從中受到啟迪和獲得新鮮的審美趣味。
能出新意的題材既包括新鮮事物,也包括陳年舊事。新鮮事物作為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題材,無疑蘊含著一定的新意;陳年舊事往往被歲月所淹沒,一經(jīng)發(fā)掘,也自有新意,即便是被人寫過的相同題材,只要站在與人不同的角度、獲得與人不同的感受,也同樣能寫出新意。如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這篇散文的題材雖然屬于陳年舊事,但我們讀起來卻仍然感到新鮮。它之所以讓人感到新鮮,就在于作者所寫的父子關(guān)系及生活內(nèi)容與他人不同。作者的父親有良好的生活修養(yǎng)和藝術(shù)修養(yǎng),對孩子如兄如友,其品格行為深深地影響著孩子的成長。文中選擇了不少有新意的生活細節(jié)來表現(xiàn)作者的立意。父親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為她做四時不缺的各種款式的冥衣;春天帶領(lǐng)著孩子們踏青放風箏,閑時為他們雕鏤別致的“西瓜燈”;兒子作文得了佳評,他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數(shù)學(xué)成績不好,也不責怪;兒子和同學(xué)演戲,他拉胡琴伴奏;兒子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兒子學(xué)抽煙,他竟然先給他點上火。父親那“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言行影響著作者,作者也以父兄友人的態(tài)度善待自己的兒子。文中那些蘊含新意的題材匯成了作品充實而感人的內(nèi)容,最后揭示出了作者所要宣揚的父子關(guān)系和人生主張:“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xiàn)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yīng)由他們自己來設(shè)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yīng)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同學(xué)們習(xí)作階段常寫到父與子、母與子及家庭生活這類情感題材,不妨讀一下汪曾祺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他認為樂器中最難的其實是胡琴,看起來簡單,只有兩根弦,但是變化很多,兩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現(xiàn)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層。他的胡琴音色剛亮。胡琴碼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認為買來的不中使。他養(yǎng)蟋蟀,養(yǎng)金鈴子。他養(yǎng)過花,他養(yǎng)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從此他就不再養(yǎng)花。我母親死后,他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里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fā)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著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lǐng)一群孩子到麥田里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里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jié)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jié)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里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鉆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里面養(yǎng)了金鈴子。從外面可以看到金鈴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扎了一只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的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罵瓜”)上開小口挖凈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里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xué)業(yè)是關(guān)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了了,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shù)學(xué)不好,他也不責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少時也喜歡畫畫,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余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太會欣賞,只是畫一些鮮艷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后,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xiàn)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xué)有幾個能唱戲的。學(xué)校開同樂會,他應(yīng)我的邀請,到學(xué)校去伴奏。幾個同學(xué)都只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xué)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碟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只是一個趙廉,搖著馬鞭在臺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郡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么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里,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xué)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guān)系,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guān)系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nóng)村勞動,他那時還從幼兒園剛畢業(yè),剛剛學(xué)會漢語拼音,用漢語拼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趕緊學(xué)會漢語拼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么還給他打酒?”只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按規(guī)定,春節(jié)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著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xué)。他這個同學(xué)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lǐng)。這個同學(xué)在北京已經(jīng)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guī)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學(xué)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于“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么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臥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lián)上档乃枷胧怯顾椎摹N覀儗鹤雍屯瑢W(xué)之間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xué)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態(tài)度是“聞而不問”。了解,但不干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后,他悄悄和一個小學(xué)時期女同學(xué)好上了,結(jié)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xiàn)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xiàn)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yīng)由他們自己來設(shè)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yīng)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選自《汪曾祺全集》,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的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情感豐富的人,他的好脾氣使孩子們很喜歡和他親近,這樣父子之間溝通起來就十分方便和暢通。父親也注重兒子的學(xué)業(yè)卻從不強求,而是讓兒子任性發(fā)展,甚至是有些“放縱”兒子,即使是朋友也很難做到。現(xiàn)實社會中更多的是那種試圖用自己的模式來塑造孩子的父母,因此這種父子關(guān)系更為難得。
【原典閱讀】
中將與中尉
趙毅衡
你一進門,我就認出了你——活脫你父親當年模樣,比他還高大魁梧。
坐,坐,喝茶。聽你父親說起過,十年前吧,他來看我的那次,一九八四年。說起過有個兒子。你母親是藏族,還健在吧!你該有三十二了。
好記性?還沒有糊涂就是。馬上八十了,哪一年的什么事,都沒忘記。唉,你父親在天之靈有慰了——兒子成材了!叫什么名?在哪兒工作?河湟農(nóng)場外貿(mào)公司。光是個牌子?牌子有用。牌子比真貨有用。有什么可讓我?guī)兔Φ模M管說,什么港商臺商的。
讓我說你父親的事?我只是好好為新社會做個反面教員嘛,叫作臭名昭著。剛才我以為又是什么記者來。我不讓他們進門,討厭。喔,開門的是我夫人。對對,老妻前年去世,不像你父親那么有福!年輕漂亮?咳,讀歷史的,看我的書入了迷。兩廂情愿。今晚我讓她好好露一手,買些上好羊肉。便飯。不恭。不恭。你遠道來,如見故人。
來跟我說你父親的事?當年的事?當然你是讀過我的書的羅?一九六五年一本,一九八〇年一本。這幾年還在寫一大人物?——不好寫呀!怕牽累你父親,怕把你父親案子弄復(fù)雜。第三本書要大寫特寫,打我回鄉(xiāng)看到你父親把他帶出來寫起。你父親幾次大險都和我在一起,救過我命,跟我做機要秘書十三年,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〇年。我倆最了解,最知心,再核心的機密我都讓他知道。說句笑話,我們跟女人們的事,也互相知道。這才叫患難與共,刎頸之交。我只比他癡長五歲,他稱我大哥,那時我可能樣子年輕些,我們長得也像。有人說我們像孿生兄弟。其實那時我們年齡比現(xiàn)在還小,共產(chǎn)黨年齡也不大。那個亂世嘛!
一九五〇年的事?唉唉,不堪回首。所謂川西反共抗俄聯(lián)軍。我是臨危受命,拉起幾萬人開進山里。孤注一擲——想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做一番英雄奇跡。羞愧啊!
最后攻破的事?咳,非正規(guī)軍,不像打仗樣子。最后只是比跑馬。連衛(wèi)隊都四散了,目標小些。只有你父親跟我在一起。在大涼山一個洞里躲了幾天。風聲小了些,想好好睡一覺,結(jié)果被共軍查到了。那時我想自裁,你父親勸了我。我才四十,你父親三十五,你父親說留得青山,來日方長。咳,都是一腦子反動念頭哇。我被押到成都一野司令部,后來關(guān)在戰(zhàn)犯所。你父親罪輕些,勞改農(nóng)場。
待遇天差地別?那時誰知道后來的事。當時我肯定自己準槍斃,你父親不會死。什么特赦戰(zhàn)犯,什么文史委員,什么政協(xié)委員、統(tǒng)戰(zhàn)對象,都是后來的事。我知道,你父親勞改十年釋放,有家難歸,留場做了農(nóng)工。正是三年饑荒時期,回鄉(xiāng)反而可能餓死,不餓死“文革”也會打死。我很同情嘛,我還在鐵屋里,一無所知。
你父親比我苦?我知道。“文革”我也不好過,被造反組織搶來搶去,要我指證叛徒。為我大打出手,一夕三驚。還是中央文革認為叛徒應(yīng)當由他們定,這才把我保護起來。你父親到八四年才敢來找我嘛,白發(fā)相見,人生何堪啊!沒想到他回去不久就去世了。怕是旅途勞頓。
是生氣死的?大家都冤,都撞進歷史漩渦,身不由己,想跳也跳不出來。原先挑的角色,越演越不像了。
要翻案?不明白。
你父親臨終時全說了?當然,當然。
說他是我,我是他?有趣。
說我冒名頂替,欺世盜名?他是軍統(tǒng)少將謝醒,我是中尉文書李光程?他干嘛不早說,要多少年后讓你來說。害怕?怕我這個無權(quán)之人?他可以對共產(chǎn)黨說嘛!共產(chǎn)黨何必放一個假的軍統(tǒng)頭目在這兒?
他說過的?就在八四年回去之后想想氣不過?那就奇了,連共產(chǎn)黨都不愿相信,我有什么辦法?我想跟他換,讓他來北京做政協(xié)委員,也沒用。
準備打官司?準備到港臺報上捅出來?好好!共產(chǎn)黨說不通跟國民黨說。我跟你說白了:我現(xiàn)在最擔心的就是人老珠黃,貨色賣光,沒誰再想看謝醒的書了。你去打個真假謝醒官司,正中下懷。要不我給你找?guī)讉€港臺駐京記者?你這身衣著不像少將公子,我給你換換行頭。說實話,哪怕你這官司打贏了,我是個中尉文書,冒充了大半輩子軍統(tǒng)少將,還寫了幾本書,這將是二十世紀一件大奇事,把我的一生總結(jié)的更加有聲有色。
所以,讓我全部告訴你吧,趁我老婆去買羊肉。你父親說的是實情,但不能說命運不公平。那天半夜時分共軍已漫山開槍搜尋。你父親驚醒了,抓過衣服,那是我的衣服。我不知他是有意無意,半夜黑洞洞看不清。你父親一世英雄,我最崇拜的人,我想他是抓錯了。他先摸出洞去。我把衣服穿好,發(fā)現(xiàn)是你父親的將官服,于是我就坐在洞里。我做了你父親十多年秘書跟班,夢里也想當將軍,我就坐在那里做了五分鐘將軍。
歷史就在那五分鐘里翻了個兒。
(選自凌鼎年《歐洲華文微型小說選》,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思考練習(xí)題
1.你怎樣理解題材這一概念?
2.文章怎樣才能做到“言之有物”?
3.為什么提倡寫自己熟悉的生活?
4.圍繞作品的主題(立意)選材是否有必要?為什么?
5.怎樣看待題材的典型性?
6.作文:自擬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