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詩三百首》選詩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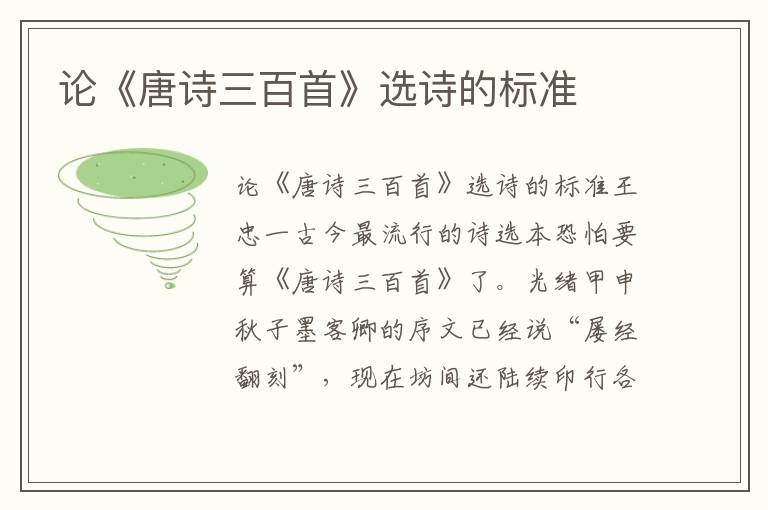
論《唐詩三百首》選詩的標準
王忠
一
古今最流行的詩選本恐怕要算《唐詩三百首》了。光緒甲申秋子墨客卿的序文已經說“屢經翻刻”,現在坊間還陸續印行各種標點白文、箋釋、注疏或語體翻譯,連窮鄉僻壤的唱本書攤也分配到,可見自印行以來三百余年迄未少衰,一直擁有各階層的讀者呢。
章燮注疏本卷首有選者蘅塘退士乾隆癸未年春的短短的題辭:
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于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七言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專就唐人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均數十首,共三百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
原來選詩的動機完全因為不滿流傳不廢的《千家詩》,因為第一,它標準不嚴,“隨手掇拾,工拙莫辨”;第二,體裁不備,“止七言律絕二體”;第三,體例不一,“唐、宋人雜出其間”。自然還有選者未直說的一個理由,就是“千家詩”太多,兒童成誦不易。于是才自己動手編選,希望這個新的選本代替《千家詩》流傳不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不是正與舊選本較一日之短長嗎?而標目的《唐詩三百首》,自然用的便是“熟讀唐詩三百首”的字面,與《詩經三百篇》的典實完全無關。
書名《唐詩三百首》,其實準確的數目應該是三百零二首。計五言古詩三十六首;五古樂府十一首;七言古詩二十八首;七古樂府十六首;五言律詩八十首;七言律詩五十三首;七律樂府一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五絕樂府八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七絕樂府七首。排列次序略依作者時代先后,每人所取不止一首時即連續排下去,并不再以詩的性質加以類別。
原始的《唐詩三百首》有注釋、解意、批等,道光十五年乙未秋九月上虞范廷懋替章燮的注疏本作序,說:
建德上舍章君象德,績學士也。嘯傲林泉,暇日輒取蘅塘原本檢閱,其注釋、解意、批所有者悉仍其舊,并采各家之說而增衍之。
子墨客卿也說:
蘅塘退士手編《唐詩三百首》,以聞見山水等指點初學,頗具苦心。
其選詩大意,具見旁注,亦復要言不煩。間有箋釋,足資考證。這便是《唐詩三百首》原本可考的一個大概的輪廓。
二
《唐詩三百首》正因為不滿《千家詩》隨手掇拾、不辨工拙才感而重選,自然有嚴格的標準了。但原始本已不可得,而章燮注疏原是雜采各家之說而增衍之,并未守疏只解注的體例,于是轉刻幾次之后,注釋完全混在一起。除非有“蘅塘退士曰”的顯明提抉,根本無法分辨了。至于旁批往往分析組織結構,有關選詩標準處也嫌語焉不詳,幾乎無從著手研究。幸好我發現一個初選根據的底本,比較參稽,可以重新找出選者取詩依據的標準和對詩的種種意見了。
這個底本便是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以時間言,《別裁》康熙五十六年即梓行,與《唐詩三百首》題辭同年秋七月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云:“鐫板問世,已四十余年矣!”因此蘅塘退士的利用本書是可能的。
再就分詩的方法看,《唐詩三百首》除分出樂府為獨立的體格、不選長律外,完全與《唐詩別裁》相同。
以所選詩比較,《唐詩三百首》五言古詩共三十六首,有三十二首與《別裁》同,五古樂府七首全同;五言律詩八十首,有五十五首相同;七言律詩五十三首,有四十三首相同。現在再就選詩的標準研究。《唐詩別裁集》凡例云:
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谷《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群推善本,亦不及李、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甚。是集以李、杜為宗,元圃夜光,五湖原泉,匯集卷內,別于諸家選本。
而《唐詩三百首》收杜甫詩三十首,占全數十分之一,為所選七十家中第一位;李白詩二十七首,僅次于王維,為第三位。沈歸愚既說別于諸家選本,如果《唐詩三百首》受任何一種選本的影響,除《唐詩別裁集》還會有第二部嗎?
又《唐詩別裁》的作者提到他自己對一詩去取的根本態度說:
詩貴渾渾灝灝,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干開張,意趣洋溢,斯為上乘。若但工于琢句,巧于著詞,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著圈點而氣味渾成者收之,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
《唐詩三百首》也有類似的意見。白居易“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于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后,蘅塘退士曰:“一氣貫注,八句如一句,與少陵《聞官軍》作同一格律。”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旁批乃是:“一氣旋折,八句如一句。”如果我們知道選者只收“一氣旋折,八句如一句”的氣味渾成的詩,“有佳句可傳而中多闕敗者”便要被汰除。《唐詩三百首》不選賈島的五律與李賀的五古、七古便毫不足怪,因為這正是它的選詩標準。且因只收三百余首詩,能夠嚴格遵守,幾乎沒有偶然逾越的例外。
對杜詩的意見,二者也完全相同。《唐詩三百首》《月夜憶舍弟》旁批云:
錄杜少陵律詩只就其綱常倫紀間至性至情流露之詩可以感發而興起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幾養正之義云。
這和《唐詩別裁》的:
蘇、李十九首以后,王言所貴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諷。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為國為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離,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于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
雖一言律詩,一論五古,重綱常倫紀與養正之義,不是如出一口嗎?
最后我們還得提到關于所謂艷詩,他們也有一部分觀點相同。《唐詩別裁》云: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為艷詩發也。雖三百以后,《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托之男女,義實關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讀曲》專詠艷情,而唐、宋香奩體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集中所載,間及夫婦男女之詞,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褻,概從闕如。
而《唐詩三百首》鄭畋《馬嵬坡》旁批云:
唐人馬嵬詩極多,惟此首得溫柔敦厚之意,故錄之。
韓偓《已涼》旁批云:
此亦通首布景,并不露情思而情愈深邃。
可見“不露情思”“溫柔敦厚”的艷詩才入選,這是《唐詩三百首》收李義山詩獨多的原因,也正是《唐詩別裁》好色不淫之旨。但我們只能說一部分標準相合,因為《唐詩三百首》獨對這標準不肯嚴格遵守,已加選《別裁》付之闕如的《無題》之類“淫哇私褻”的艷詩,不過仍然維持著相同的論調罷了。
三
正因為《唐詩三百首》還經過一番選擇,便不完全抄襲《別裁》而另有自己選詩的體例與標準。首先便是另標樂府名目這一明顯的差異。《唐詩別裁》凡例云:
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制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弦也。故雜錄于各體中,不易標名目。
而《唐詩三百首》恰巧相反,不憚煩地把樂府分為各體。原來他已接受郭茂倩的意見,給樂府詩別立一個發展演變的系統,不以入樂與否抹殺樂府詩的特性。王維《秋夜曲》后有一則選者的按語:
蘅塘退士曰:“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
可見連作者的異說也無條件依據郭本了。但這還是無關重要的分詩方法,進一步研究原來選詩標準也有差異呢。
《唐詩三百首》選定的時代正是三種詩論鼎峙的局面最初形成。王漁洋的“神韻說”勢力未衰,前后七子倡導的格調說得沈歸愚的發揮與修正也能堅強地屹立,而新興的袁隨園的性靈說正風靡一時。《唐詩三百首》正是一個調和三家意見的詩的選本。雖以格調派的理論做中心,并未廢神韻派與性靈派的意見。
王漁洋在康熙間創神韻說,以為詩須沖淡清遠,含蓄不盡。他的《唐賢三昧集》便是根據這標準選詩,完全不錄李、杜而選王維獨多。現在《唐詩三百首》取王維詩二十九首,僅次于杜甫,尚比李白多一首,可見有意推尊王維儕于李、杜之間。《師友詩傳續錄》云:
(漁洋)曰:“格即品格,韻謂風神。”
《漁洋詩話》上云:
“古人詩但取興會超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又《池北偶談》十八“王右丞”條云:
“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唐詩三百首》也喜言“神會”,言“神味”。盂浩然《與諸子登峴山》旁批云:
“憑空落筆,若不著題而自有神會。”
又宋之問《題大庾嶺北驛》“陽月南飛雁”等前四句旁批云:
“四句一氣旋折,神味無窮。”
復次,神韻派多以禪論詩。《蠶尾續文》貳《畫溪西堂詩序》云:“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居易錄》貳拾亦云:
唐人如王摩詰、孟浩然、劉眘虛、常建、王昌齡諸人之詩,皆可語禪。
《唐詩三百首》選孟浩然詩十三首,為第五位;王昌齡詩八首,為第八位。而白居易“問劉十九”旁批云:
“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詩家三昧,如是如是!”
“三昧”二字,正是王漁洋取以名集的《唐賢三昧集》的三昧。
格調說與神韻說能夠調和嗎?答案是肯定的。翁方綱說:
“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即格調耳。”(《復初齋文集》捌《格調論》上)
因此可以同時談格調又談神韻,正是潘德輿所謂“神理意境”,他說:
《三百篇》之體裁音節,不必學,亦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文有盡而意無窮,四也。(《己畦文集》壹)
《唐詩三百首》選者好像特別看重第四項“文有盡而意無窮”。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等四句旁批云:“四句十八層。”韓翊《酬程近秋即事見贈》“長簟迎風早”等四句旁批云:“四句當作十七八層看。”王之渙《登鸛雀樓》旁批云:“二十字氣象萬千。”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旁批云:“十字十層,咀味無盡。”都是明證。
四
隨園以性靈說神韻,他自己雖沒有選過詩,但從詩論可以發現一個重要意見,就是重視中晩唐詩。他一反明代前后七子詩必盛唐之說,也不局限于漁洋所重的王、孟一派詩人,范圍擴大,題材也擴大了。他說:
余嘗教人曰:“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晩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細,播入管弦,音節亦多未協。中晩名家便清脆可誦。”(《隨園詩話》柒)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初備,故不過樹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已。而其中洞房曲室、網戶羅窗,尚未齊備,至中晩而始備。”(《隨園詩話》陸)
我們再回頭看《唐詩三百首》所選的近體詩:五言律詩八十首,中晩唐有三十七首;七言律詩五十三首,中晩唐二十四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中晩唐十六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中晩唐三十八首。中晩唐詩幾乎占了一半,這對《唐詩別裁》是一個重大的修正。
《唐詩別裁》論五言律云:
“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秾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并推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于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范圍者矣!”
又論七言律云:
少陵胸次閎闊,議論開辟,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余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有搜羅,概從其略。
完全不脫詩必盛唐的偏見,除了對李義山詠史還認為少陵余響,其余中晩唐詩便都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可有可無了。但《唐詩三百首》卻不肯略中晩唐近體,不是與隨園意見正相同嗎?
又《小蒼山房文集》拾柒《再與沈大宗伯書》云:
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詩之奇平艷情,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集中不特艷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后詩之體備而選之道盡。
而《唐詩別裁》的作者則說:
《詩》一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為艷情發也。……自《子夜》《讀曲》專詠艷情,而唐末“香奩”體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集中所載,閑及夫婦男女之詞,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褻,概從闕如。
因此不收李義山的“無題”詩,溫飛卿、韓偓等的“香奩”詩。但《唐詩三百首》卻取李義山詩至二十二首,占第四位,“無題”詩更收羅無遺。韓偓《香奩集》中的詩也取,溫飛卿的艷詩也取。雖然還主張“不露情思”,在沈歸愚看來,已經“淫哇私褻”,應該刪除了。這是《唐詩三百首》接近隨園性靈派的另一個證據。
五
最后給本書一個品評。大體說來,《唐詩三百首》每類詩都能選出代表作品。這并不完全屬于選者的功績,歷代多少選本參與這工作,許多詩話對全詩或一章一句的精密分析也對這工作有相當貢獻。《唐詩三百首》的時代已有不少傳誦人口普遍流行的好詩或佳句了。而且有唐三百年詩的總成績僅就現存的《全唐詩》統計也有四萬余首,三百首可以百中挑一,真是沙里淘金,容易得水準以上的詩。但《唐詩三百首》多所折中,不囿于一家一派,范圍相當廣闊,每類詩選取的多少又完全就詩論詩,心目中無初盛中晚之分,可以適合各種趣味,這是它所以廣泛流行的原因,也是它本身的價值。
如果我們還要勉強吹求的話,第一,它標準嚴限于“溫柔敦厚”四字,不取質直淺露的元、白社會詩,于是唐詩中呼號民生疾若這一極有價值的傾向被抹殺了。一個流行民間的詩選本遂只完全表現士大夫的生活思想與感情。第二,《唐詩三百首》以時代先后排列,原可以當作通俗的唐代詩史的代表作看,但選者過于嚴守主觀的標準,除韓詩存下一部分,許多影響很大的詩人如賈島、姚合的五律一篇也不取,李賀的五古七古也不入選,使我們失去不少應該認識的詩人。
但瑕不掩瑜,直到今天,《唐詩三百首》還是唐詩中最好的一個選本。
八月十五日清華園
(原載《國文月刊》第73期,19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