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文學(xué)成就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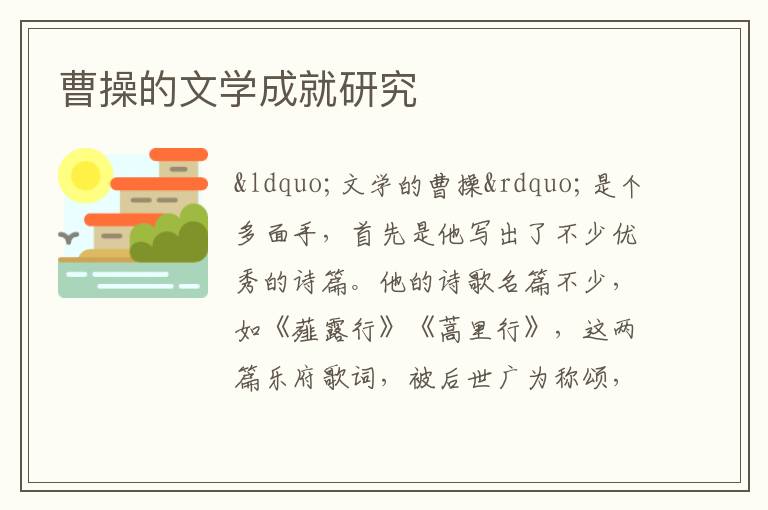
“文學(xué)的曹操”是個(gè)多面手,首先是他寫出了不少優(yōu)秀的詩篇。他的詩歌名篇不少,如《薤露行》《蒿里行》,這兩篇樂府歌詞,被后世廣為稱頌,明代詩論家鐘惺譽(yù)之為“詩史”,說“漢末實(shí)錄,真詩史也”(《古詩歸》卷七)。古代能夠膺此殊榮的詩人極少,它們被稱為“詩史”,自有一定道理。
以《薤露行》為例,本篇開頭寫的真是一段歷史:“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漢代第二十二位皇帝,重用了壞人。”接下來仍然是敘述歷史:“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猶豫不敢斷,因狩執(zhí)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這是說外戚何進(jìn)任大將軍,但他能力很差,處事不當(dāng),坐視少帝被宦官們劫持,最終自己亦被殺。接著寫的還是歷史:“賊臣執(zhí)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yè),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這是說董卓作亂,殺害少帝,裹挾獻(xiàn)帝和朝廷西遷長安,局勢不可收拾。漢末靈帝死后政局迅速走向衰敗的一段復(fù)雜歷史,被他以很簡括的語句寫出來了。《蒿里行》寫法類似。“關(guān)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寫的是董卓作亂后,關(guān)東各路實(shí)力派人物起兵討董之事。這是緊接著的另一段歷史。兩篇寫的都是以歷史事實(shí)為主。不僅是這兩篇,曹操今存的其他詩篇,不少也都具有這種以詩寫史的特點(diǎn)。如《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等等,寫的是他在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征伐并州高干之事;《步出夏門行》組詩,“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等等,寫的就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三郡烏丸之事;《秋胡行》“晨上散關(guān)山,此道當(dāng)何難”等等,寫的是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西征漢中張魯之事,《魏志》本傳記載該年“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guān),至河池”。可知曹操以詩寫史,是他的常用寫作方式,是他詩歌取材內(nèi)容上的重要特點(diǎn)。
以詩寫史,中國早有傳統(tǒng)。《詩經(jīng)·大雅》中就有多篇作品,如《生民》《文王》《大明》《綿》等,寫周族的發(fā)源和壯大經(jīng)過,它們早就被《詩經(jīng)》學(xué)者認(rèn)為是上古“史詩”性質(zhì)的作品。至于文人筆下的以詩寫史,漢代已有班固《詠史》,寫漢文帝時(shí)緹縈救父事件,它被公認(rèn)是中國詠史詩的濫觴。不過比起班固來,曹操的寫歷史,又有自身特點(diǎn)。最重要的一點(diǎn),就是曹操寫的多是歷史大事件。從歷史角度說,“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當(dāng)然比“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更大更重要。其次就是他所寫的基本上都是本人親身經(jīng)歷的事件,他寫漢末外戚宦官掀起的朝廷大亂,寫關(guān)東軍聯(lián)合討伐董卓,寫北征三郡烏丸,寫征伐并州高干,寫征伐漢中張魯,這些事件他都親身參與過,并且是事件的主角。因此他的“詩史”更有現(xiàn)實(shí)分量,更有歷史內(nèi)涵。
曹操為何喜歡寫作“詩史”?這就必須聯(lián)系他的身份和人格來說了。曹操為人精明強(qiáng)干,頭腦極其清醒,他“性不信天命”,是一位徹底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者,所以他深知,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在于做好一個(gè)“政治曹操”“軍事曹操”,然后才會有“文學(xué)曹操”。他的文學(xué)活動,包括寫作內(nèi)涵,都不能脫離政治軍事,他寫“歷史”,實(shí)際上就是寫重大的現(xiàn)實(shí)社會事件。所以他的詩歌,盡管具有不少娛樂色彩,有的還寓有很強(qiáng)的想象力,甚至寫及天庭神仙等等,但根本上他還是不能忘懷現(xiàn)實(shí)時(shí)勢。他不會本末倒置。
不過曹操以詩寫史之際,也不會忘了抒情。《薤露行》最后兩韻,寫了“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這里是誰在“號泣”?是那些被董卓強(qiáng)迫西遷的官員及被裹挾的百姓。是誰在“哀傷”?就是曹操自己了。他在詩的末尾,站出來以商朝的微子自居,為民眾苦難和國家衰敗而哀傷。這是點(diǎn)睛之筆,“哀傷”情緒十分濃郁。抒情當(dāng)然是詩歌的本色,所以本篇是以寫歷史開頭,而以抒情作結(jié),他終于跳出歷史敘述的框架,進(jìn)入文學(xué)的領(lǐng)域。
《蒿里行》同樣如此,詩篇后半寫的是“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dāng)嗳四c。”詩人現(xiàn)身出來,為“萬姓”“生民”身受戰(zhàn)亂禍害、以致大量死亡而悲痛。“白骨”云云,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是對現(xiàn)實(shí)狀況的深切概括,所以這四句也成了廣為傳誦的千古名句。而最值得我們重視的,乃是詩人“念之?dāng)嗳四c”的表態(tài),這里表現(xiàn)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立場。
說到這里,需要討論的一個(gè)問題是:曹操詩中表現(xiàn)出的同情民眾的“哀傷”情緒,是他的真情流露嗎?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yàn)椴懿偈浅雒?ldquo;亂世之奸雄”,他在不少場合都曾有“雄詐”或“多譎”的表現(xiàn)。那么他在詩中說的“悲”“哀傷”“念之?dāng)嗳四c”之類,是否也可能是“詐”的?對此,我們說曹操其人性格上確實(shí)存在兩面性,但不可能事事都“詐”,時(shí)時(shí)皆“譎”。一個(gè)人如果在任何事情上都無誠信可言,那就無人愿意為他效力,他就絕對成不了大氣候。曹操感情真?zhèn)蔚膯栴},只能通過客觀分析來判斷。以《薤露行》《蒿里行》兩篇為例看,曹操寫作當(dāng)時(shí),是站在反對外戚、宦官和軍閥董卓淆亂朝政的立場。他當(dāng)時(shí)自稱“吾等合大眾、興義兵”(《魏志》注引王沈《魏書》),可謂名正言順,所以應(yīng)當(dāng)認(rèn)可他具有一定的正義性,至少在他自己心中認(rèn)為是正義的。在關(guān)東實(shí)力派人物聯(lián)合對抗董卓的軍事行動中,袁紹等面臨彪悍的董卓關(guān)西軍,心生懼怕,又想保存實(shí)力,因此原地觀望、畏縮不前,而曹操則明知自己實(shí)力不足,卻能挺身而出,對袁紹慷慨陳詞說“諸軍北面,我自西向”(同上),獨(dú)自奮戰(zhàn),雖然他戰(zhàn)敗了,卻贏得了尊重,雖敗猶榮。當(dāng)此之時(shí),曹操的表現(xiàn)與其他關(guān)東軍閥形成鮮明對照,他確實(shí)顯示了一股正氣、勇氣。在此背景下產(chǎn)生的詩歌,其中描寫戰(zhàn)爭的殘酷,表達(dá)對老百姓疾苦和不幸命運(yùn)的同情,不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譎”“詐”的產(chǎn)物。說它們表現(xiàn)了人道主義精神,不算溢美之詞。
曹操詩歌還有一個(gè)特色,即它充滿著慷慨悲涼情調(diào)。他的詩歌中好用“悲”“哀”“憂”“傷”等語詞,寫出濃厚強(qiáng)烈的悲涼情緒氣氛來。鐘嶸《詩品》早就指出過:“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除上述《薤露行》《蒿里行》外,曹操《短歌行》寫“慨當(dāng)以慷,憂思難忘”“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秋胡行》寫“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等等。“慨當(dāng)以慷,憂思難忘”,實(shí)際上就是曹操詩歌風(fēng)格的自我概括。他的《苦寒行》,堪稱是抒寫憂思和悲情的代表作: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fēng)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yuǎn)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yuǎn),人馬同時(shí)饑。擔(dān)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這是他親征袁紹外甥高干時(shí)作的。高干盤踞在并州(今山西),曹操從鄴城出發(fā),進(jìn)軍的方向是“北上太行山”。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情勢對他非常有利,敵弱我強(qiáng),對比分明,但是我們在這篇詩里,卻看到他寫了許多行軍中不利條件,氣候、地形、道路、自然環(huán)境十分險(xiǎn)峻惡劣,連熊羆虎豹這些動物都似乎對“我”表現(xiàn)出嚴(yán)重?cái)骋猓凰媾R著本方軍糧缺乏、迷失道路、人疲馬饑等情況,直露地寫出自己的悲哀心情:“北風(fēng)聲正悲”“悠悠令我哀”。他甚至說“思欲一東歸”,想返回去的念頭都有了。曹操不寫克敵制勝的愿望,不寫必勝的信念,卻寫出許多困苦、一片哀傷,他就不怕自沮軍心?其實(shí)這些當(dāng)然會在曹操的考慮之中。他對戰(zhàn)爭無疑懷著必勝信念,他清楚地知道高干已經(jīng)窮途末路,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正因?yàn)槭潜貏贌o疑的,所以他敢于寫“思欲一東歸”“悠悠令我哀”,他不擔(dān)心軍心問題。更何況,他寫“悲彼東山詩”,這是以周公自擬的寫法,《詩經(jīng)·豳風(fēng)·東山》篇就是寫周公東征的,曹操寫作本篇的思路,就是循著《東山》篇而來的。這思路就是:“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也,說(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毛詩序》)原來曹操極力寫出軍旅生活的艱難困苦,是對軍士們的“序其情而閔其勞”,是對他們“情”(苦衷)的一種體諒和慰勞,目的是為了讓士兵們高興(“說”)起來,高興起來之后就可以供他所“使”,鼓勵(lì)他們“民忘其死”,勇敢戰(zhàn)斗!曹操在這里采取的是尊重現(xiàn)實(shí)、體諒士兵的態(tài)度,這比起那種所謂“鼓舞人心”的高調(diào)來,恐怕更起作用,更能激勵(lì)下屬為他效力,更能提高軍隊(duì)的戰(zhàn)斗力。我想這也是曹操的高明之處。
曹操詩歌慷慨悲涼的情緒,我認(rèn)為主要有兩個(gè)來源。一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來源。他生當(dāng)漢末戰(zhàn)亂時(shí)期,社會受到極大破壞,滿目瘡痍,民生凋零,社會大環(huán)境充滿悲哀凄涼氣氛,他要如實(shí)表現(xiàn)自我感受,只能是以悲涼為主。二是傳統(tǒng)的來源。從漢代以來,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就存在一種“以悲為美”的取向。王充說:“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論衡·自紀(jì)篇》)“悲”成了優(yōu)美情調(diào)的代名詞。我們看漢末《古詩十九首》中,多以悲情為主調(diào),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古憂”“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等等,都顯示出作者以悲為美的深層審美意識。曹操詩歌中多悲情,也是傳統(tǒng)審美意識在他創(chuàng)作中的表露,使得曹操詩歌形成獨(dú)特的風(fēng)格:慷慨悲涼。慷慨是充滿激情,悲涼是一種深沉的感傷情調(diào)。慷慨悲涼格調(diào),給曹操詩歌增添一種雄豪深沉的魅力,格外感人。
總體上說,曹操詩歌成就不在曹丕、曹植之下。清代吳喬認(rèn)為:“魏武終身攻戰(zhàn),何暇學(xué)詩?而精能老鍵,建安才子所不及。”(《圍爐詩話》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