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問》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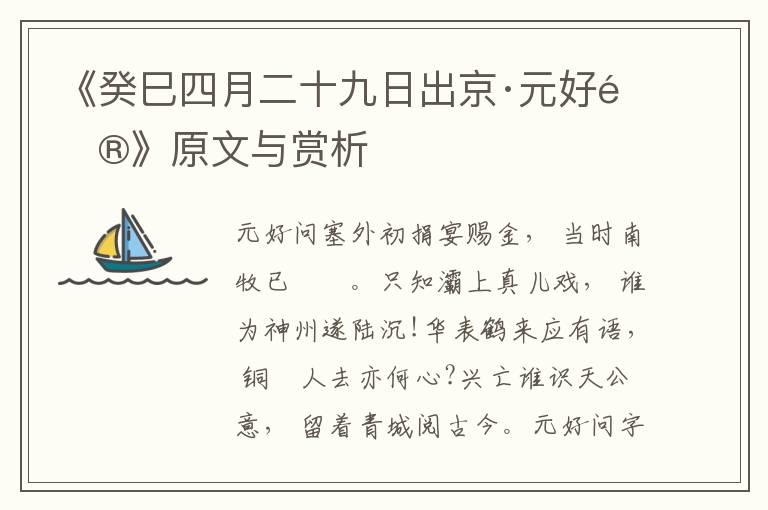
元好問
塞外初捐宴賜金, 當時南牧已骎骎。
只知灞上真兒戲, 誰為神州遂陸沉!
華表鶴來應有語, 銅槃人去亦何心?
興亡誰識天公意, 留著青城閱古今。
元好問字裕之, 自號遺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人,是拓跋氏后裔,自北魏孝文帝時改為姓元。他生長于女真族完顏氏建立的金朝,金朝雖在建國時攻占了宋朝的北中國,但到金哀宗完顏守緒的時候,由于內部矛盾,自相殘殺,后來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興起,與南宋結盟,南北夾擊金人,終于在哀宗天興三年(1234)金朝被蒙古族滅亡。
元好問當時任金朝的左司都事,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蒙古大軍兩次圍攻京城汴京(即北宋都城,今河南開封市),他在汴京過著“圍城十月鬼為鄰”的生活,至十二月,哀宗出城渡河,次年春,金守將崔立開城投降蒙古,四月間,元好問和金朝其他大官一起,被蒙古軍“羈管聊城(今山東聊城)”,成為一楚囚。
癸巳即金天興二年(1233),四月二十九日是他們被蒙古軍“羈管”,押解出京的日子。
這首詩以回憶往事開頭,金朝自完顏亮正隆年間開始,為了與逐漸強大頻頻人侵的蒙古人和好,常常舉行“宴賜”,明昌二年起規定每五年宴賜一次,金統治者把這筆支出轉嫁于民,詩人第一句就說當塞外一開始要百姓捐“宴賜金”的時候,蒙古人南下的“牧馬”就飛奔起來了,表現了詩人對統治者向外族屈膝求和的不滿。
次聯“灞上真兒戲”指的是金朝的一大蠹政,即所謂“簽軍”,劉祁在《歸潛志》中記載:“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有丁男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乎道路。”這樣的軍心,又怎能作戰。這在詩人是早就“知”的,但是他“只知”此舉之腐敗,卻未料其嚴重結果是“神州遂陸沉”,國家竟就這樣斷送了。對統治者的抨擊和滅國的憤懣,不言自明。
第三聯用了兩個典故,“華表鶴來”是一個神話,說漢朝遼東人丁令威學道成功,化為白鶴,飛到遼東城門的華表柱上,說:“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學冢累累。”詩中采用“城郭如故人民非”之意,如今國亡人去,即使神仙回來也要發出這樣的感嘆,這就是“鶴來應有語”之意。
第二個典故“銅槃人去”,指魏明帝曹叡下詔命宮官把漢武帝所造承露銅盤和銅制仙人以掌擎玉盤者都拆下來,運到洛陽放在魏宮前殿,宮官拆下后裝上車時,這個銅人流下了眼淚。這里表示連銅人尚有亡國之悲痛,我們難道能一無所感?
結聯詩人誤將國家興亡歸之于“天公意”,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觀點,然而從這興亡中能得出什么教訓呢?歷史將留待后人來評說,只要青城在,人們就能從這里“閱”出歷史的真髓。想當年,在宋的大梁城南五里稱為“青城”的地方,金國粘罕接受北宋徽、欽二帝投降,金兵將后妃、皇族、宮人盡俘而北去。而今崔立開城降元,蒙古軍亦于青城下寨,將金國的后妃、皇族亦如法炮制。歷史以何其殘酷的手段在相似地重復,“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
詩人在國亡被虜,押解離京時,極其清醒地回憶了歷史,指責了金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對故國的滅亡,流露著無限的眷戀之情,同時也充滿了回腸蕩氣的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