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魯儒·李白》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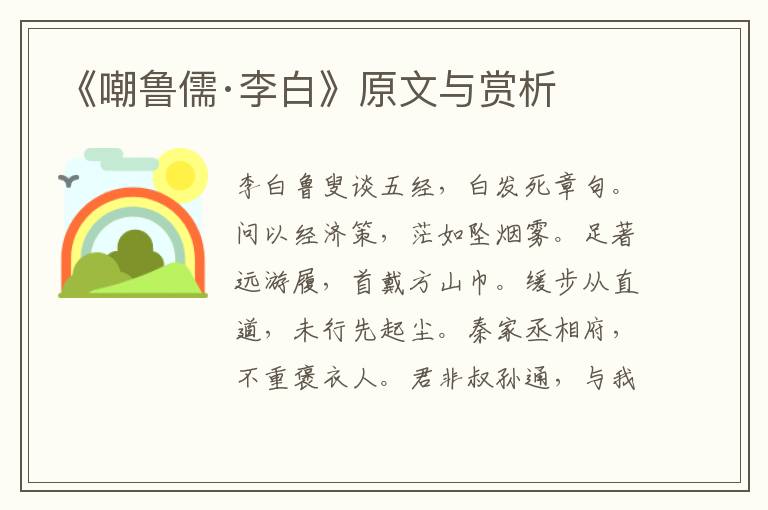
李白
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邊。
李白游歷山東時,曾遇到一些腐儒。他們嘲笑李白的狂放不羈和不識窮通之理,李白則瞧不起他們的迂腐泥古和不達時務,因而寫了這首詩給以嘲諷。
詩的前四句,嘲笑魯儒只知讀死書,而遇到實際問題則一竅不通。“五經”,即《詩》、《書》、《禮》、《易》和《春秋》,被儒家奉為經典。魯儒談論“五經”,只會在分章、斷句和字義訓詁上兜圈子,再也談不出其他的意義。李白用一個“死”字來形容他們鉆入章句的牛角尖而跳不出來的呆板情景,十分準確貼切;“白發”與“叟”字相呼應,描繪他們至死不悟的死讀書形象,更是生動傳神。很顯然,他們讀書如此食而不化,當然無法靈活運用于現實,所以,一旦“問以經濟策”,他們就“茫如墜煙霧”了。李白的世界觀比較復雜,儒、墨、道各家思想對他都有影響,但占主導地位還是儒家思想,所以他有經國濟世的抱負。腐儒雖然也信奉儒學,但他們熟知的不過是儒學中陳腐過時的教條,并不能面對各種社會現實去考慮治國之道,所以也就無法理解李白的胸襟以及理想難于實現的苦悶。李白用“茫如墜煙霧”來嘲笑他們在現實問題面前茫然無措、昏頭轉向,不但進一步強化了對他們“白發死章句”的批評,而且為末尾“時事且未達”的斷語預設了根據。
魯儒思想上的泥古不化,必然會導致行動上的生搬硬套。接下去的四句,便從形貌舉止上作漫畫式的勾勒,對他們處處地方都仿古擬古的可笑行為作了冷嘲熱諷。“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畫其裝束和形貌。“遠游履”和“方山巾”都是古代人的鞋帽。今天的魯儒們從頭到腳,一切都按古人的式樣裝束自己,不是一副滑稽可笑的模樣嗎?他們不僅在裝束上仿古,而且在行動上仿古。“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便是畫其可笑的舉止。《論語·鄉黨篇》曾記述孔子在衣食言行方面的種種煩瑣規矩,今日的魯儒竟把孔子的古訓視為準則,“足蹜蹜如有循”, 目不斜視,一步一蹬,以一種裝腔作勢的古怪步伐走路,這不更是令人捧腹嗎?漫畫的特征之一是夸張。李白對魯儒舉止形貌的勾勒,正是用了這種夸張的藝術手法,所以能讓讀者對其產生深刻的印象,在笑聲中達到嘲諷的目的。
由于前八句對魯儒已經從靈魂到形貌、從思想到行動作了徹里徹外的剖視,因此,后六句就能夠從正面對魯儒進行徹底否定。詩人首先借用兩個典故,指出魯儒們不過是無能之輩、無用之材。“秦家丞相”指秦國丞相李斯,他反對儒生“不師今而學古”,故借此說明“褒衣”者(穿著寬大儒服的儒生)是不會受到重用的。“叔孫通”曾為漢高祖制定朝儀。詩人借此典故指出魯儒們根本不是那種敢于創新和有所建樹的人,當然也就為向有抱負的詩人所不齒。既然如此,他們讀了書又有何用呢?還不如回到汶水邊上去耕田吧!結句語言俏皮,嘲諷辛辣,否定徹底,既含諧趣,又有份量,堪為寓莊于諧的典范。
李白對魯儒的嘲諷,今天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我們應以魯儒為鑒,免蹈其泥古不化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