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津夜泊·周致堯》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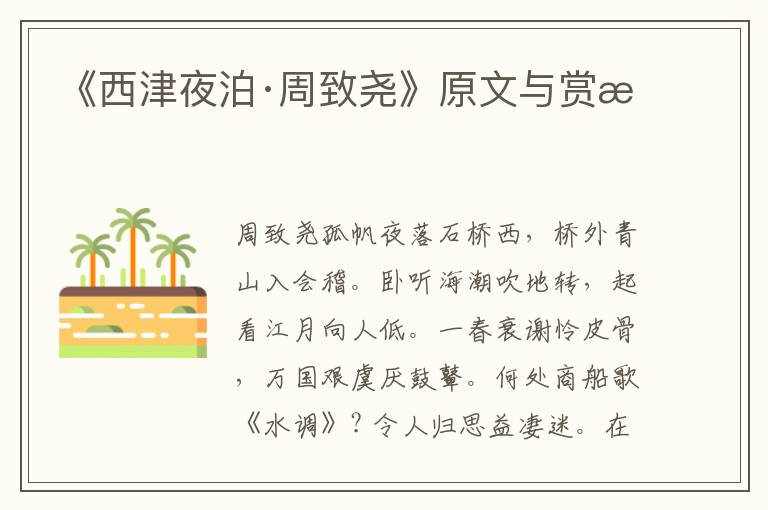
周致堯
孤帆夜落石橋西,橋外青山入會稽。
臥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
一春衰謝憐皮骨,萬國艱虞厭鼓鼙。
何處商船歌《水調》? 令人歸思益凄迷。
在中國文學史上,明代詩歌遠遜于唐詩、宋詞和元散曲,成就不大。但是其中也不乏抒發真情實感的較好作品。周致堯的這首《西津夜泊》,把抒發個人羈旅之情與反映人民的生活情緒融為一體,就屬于這類較好的作品之列。
“孤帆夜落石橋西,橋外青山入會稽。”首聯寫作者行蹤,兼寫所見之景。詩人乘船來到會稽(今紹興),暮色之中,船只停泊在西津渡口旁的石橋西邊。石橋、青山,正在落下的孤帆,構成詩人眼前的紹興一景。表面看來,首聯意緒似較清淡。然而,孤帆夜落的客行,橋外青山的陌生,已經透出詩人的孤寂之感,為結句中的“歸思”埋下了伏筆。
“臥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一春衰謝憐皮骨,萬國艱虞厭鼓鼙。”頷聯重在寫景,頸聯重在抒情。“錢塘自古繁華”,“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柳永:《望海潮》)紹興雖不在錢塘江畔,但和杭州一樣,都屬杭州灣周圍地區。頷聯抓住這一地區海潮壯觀的總體特點寫景,不可在地理位置上過于拘泥。“吹地轉”,形容海潮聲勢壯偉;一個“轉”字,寫盡海潮旋轉天地之力。正由于潮勢浩大,濤接星漢,因此,連錢塘江上空的月亮也似乎變低了。一個“低”字,既寫了月景,又回襯了潮景,極為準確、熨貼。詩人先是“臥聽”,后來又是“起看”,是為海潮所吸引,還是被海潮所煩惱?也許兼而有之。但聯系下面的抒懷來看,詩人的心潮猶如海潮,奔騰澎湃,無法平息,似乎煩惱更多于吸引。聽著濤聲,想起自己和百姓的遭遇,詩人無法入睡,便索性起身佇立于船頭了。頷聯接下去便從自己和百姓兩個側面抒情。春末已臨,開了一個春天的百花都已凋謝;自己長期在外奔走,年華流逝,青春消失,瘦得只剩一把皮包骨頭了。如果詩人只就個人的遭遇抒發情懷,也未嘗不可,但他沒有停留于個人命運的慨嘆,更想到了百姓。“萬國”,泛指全國各處;“艱虞”,艱難憂患;“鼓鼙”,戰鼓,這里喻代戰爭。作者的生卒年代不詳,所生活的時代難以確定。但在明代的中后期,內訌不絕,外患時至,人民的厭戰情緒很強烈。詩中的“厭鼓鼙”,可能就是這一情緒的反映。詩人想到全國各地的百姓衣食無著,生活艱難,對戰爭十分厭惡,心中就更難以平靜了。詩人能把一己之悲與萬眾之苦聯系起來,由個人的羈旅異鄉想到百姓的不能安居樂業,就更加深了詩人的羈旅愁懷。
“何處商船歌《水調》?令人歸思益凄迷。”“水調”原為大唐曲名,這里泛指歌曲;“凄迷”,凄楚、迷惘。這兩句是說:哪里的商船,竟有人在歡樂地歌唱?這真使人的歸鄉之情中更增添了凄楚和迷惘。“何處”暗解起首的“孤帆”,言商船系后至或泊于遠處;“歸思”照應首聯的“入會稽”,聯系頸聯的“憐皮骨”,點出詩歌的主旨;“歌《水調》”與“萬國艱虞”形成反照,寓含了詩人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某種反感,也是詩人在“歸思”之中更增添凄楚和迷惘的直接原因。
這首詩感情深沉、痛切,寫景也頗具特色,尤其在抒發游子羈旅之情時容納了較深廣的社會內容,這都是應予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