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陣子·李煜》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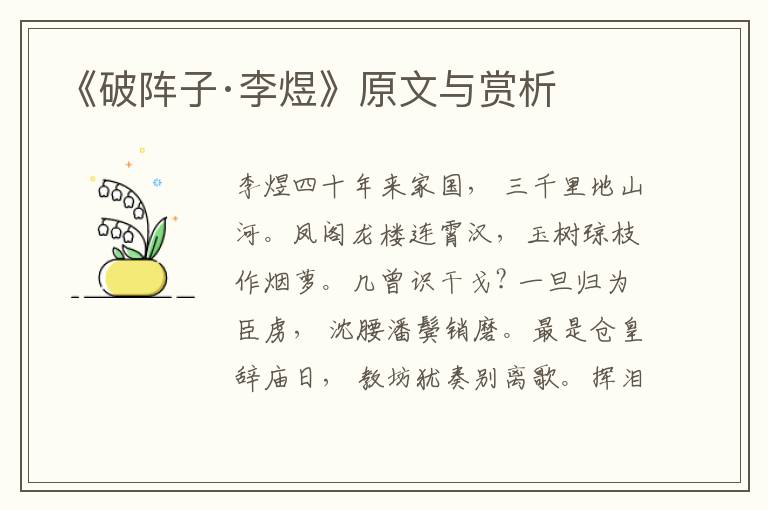
李煜
四十年來家國, 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shí)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 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duì)宮娥!
李煜(937—978),字重光,號(hào)鐘隱、蓬峰居士等。他是五代十國時(shí)期南唐的最后一個(gè)國主,一個(gè)亡國之君。太祖死后,太宗趙光義繼位,改年號(hào)太平興國。李煜在汴京被軟禁,“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并不停地寫詞抒亡國之怨。太宗聞“小樓昨夜又東風(fēng)”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大怒,命其弟趙廷美賜牽機(jī)藥毒死,李煜死狀慘不忍睹。
李煜的詞可以開寶八年(975)被俘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多寫宮廷生活、男女戀情與離愁別緒,是花間派詞風(fēng)。后期多寫軟禁生活,抒發(fā)懷念故國的痛苦與悲愁,深刻、典型地表現(xiàn)了愛“家國”、“鄉(xiāng)國”、“邦國”,包括愛南唐王朝,愛祖、父傳下的王位的真情。后期的詞以白描手法、高度的藝術(shù)概括和單純明凈、準(zhǔn)確精煉的語言,抒寫生活中的深刻體驗(yàn),從而突破了花間詞題材與手法的局限,在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宋詞的興起與繁榮,是與后主的貢獻(xiàn)分不開的。
《破陣子》是后主被俘北上所作,寫被迫離開南唐時(shí)的景況,抒發(fā)亡國之恨。
詞的上片極寫南唐全盛期的繁榮與豪華。“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從時(shí)間看, 自后晉天福二年(937)李昪禪吳位建南唐到宋太祖開寶八年(975)作者“肉袒出降”南唐亡國止,已近四十年。從地域看,馬令《南唐書·建國譜》:“共三十五州之地,號(hào)為大國。”陸游《南唐書·本紀(jì)二》:“唐有江淮, 比同時(shí)割據(jù)諸國,地大力強(qiáng),人材眾多,且據(jù)長江之險(xiǎn),隱然大邦也。”其版圖包括今江蘇、安徽、江西,極盛期曾占有湖南、福建。因此,這起兩行高度概括了南唐歷史與國威,贊揚(yáng)先輩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充溢著自豪感和對(duì)祖國的摯愛之情。接兩行“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寫南唐繁華與宮中豪華。帝王宮中用龍鳳圖案裝飾的樓閣高接云天;嘉樹美草好象是用美玉瓊瑤雕琢而成,它們似罩在霧氣里的女蘿一樣繁密茂盛,一片迷茫,一片朦朧。后主早年就活動(dòng)于其間,“生于深宮之中, 長于婦人之手”,二十五歲登極,南唐已是趙宋附庸,他只得權(quán)用忍辱負(fù)重、保國安土的政策,“幾曾識(shí)干戈”?這是說,南唐從未想對(duì)趙宋實(shí)施武力反抗。可是,趙匡胤最后卻陰忍地殘害南唐。因此這一句含義很深,寄寓了作者的悔恨,隱含著對(duì)宋太祖的貶斥。上片感情復(fù)雜,國由祖父創(chuàng)之,家由父親興之,最后統(tǒng)統(tǒng)由自己失之,感到羞愧、懊惱、內(nèi)疚、自省……
下片寫告別故國時(shí)的悲慘場面和被擄后精神的折磨。“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一國之主淪為俘虜,從高峰跌入低谷,生活的痛苦,精神的煎熬,可以想見。作者以兩個(gè)典故,用兩個(gè)歷史人物打比方,來表現(xiàn)自己的心境。“沈腰”用梁代沈約之事,《南史·沈約傳》:“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言己老病,百日數(shù)旬,革帶常應(yīng)移孔,以手握臂,率計(jì)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后人將“沈腰”作為腰身一天天瘦減的代稱。“潘鬢”用西晉潘岳之事。潘岳《秋興賦》:“斑鬢發(fā)以承弁兮,素發(fā)颯以垂領(lǐng)。”后人將“潘鬢”看做兩鬢斑白的代稱。兩行說,一旦成了俘虜,就在悲哀、怨恨、憂愁、苦悶中苦度光陰,人很快消瘦、衰老了。這兩個(gè)典用得是很妥貼的。“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duì)宮娥!”這是回憶最難堪的鏡頭。“倉皇辭廟”是痛苦的,他沒有想到要被押到汴京去,只得心驚肉跳地匆匆忙忙地去拜別祖先,“辭廟”就是離開祖先創(chuàng)建的國家。作者失魂落魄、慌慌張張的情態(tài)如在眼前。“猶奏別離歌”也是痛苦的。“教坊”是宮中掌管妓樂的機(jī)構(gòu),這里是指宮中的歌舞班子。樂工歌姬見后主離國,不能再回歸故土,于是奏起別離的悲樂送行。“垂淚對(duì)宮娥”,這是最痛苦的,因?yàn)槭凰夭偷拇蟪夹煦C等人早就改換門庭,投奔趙宋去追求榮華富貴去了,有那一位來送行?只有后主平素尊重的宮女黃保儀、流珠、喬氏、慶奴、薛九、宜愛、意可、窅娘、秋水、小花蕊等來送行。據(jù)歷史記載,李煜待人寬厚誠懇,與宮女相處極好,待之甚厚。現(xiàn)在亡國了,她們失卻保護(hù),反而來送別,后主十分感激。面對(duì)著活生生的人,千言萬語從何說起,他只得揮著淚水,失聲慟哭。下片寫自己離國時(shí)的悲慘場景,哀婉欲絕,后主哭廟,樂工歌姬哭別,宮娥哭主,哀樂聲、悲歌聲、痛哭聲混為一片,上干云霄,“寧復(fù)知人間何世耶”!
這首詞在思想上有下列價(jià)值。作者愛家鄉(xiāng),愛故國,愛和平,愛先輩開創(chuàng)的基業(yè),愛同情自己的樂工、歌姬、宮娥,恨自己未盡守業(yè)之責(zé)任,恨趙匡胤的毒辣,恨自己淪為連普通百姓也不如的虜奴,恨自己不能再保護(hù)部屬了……這些都具有相當(dāng)?shù)恼x性和正當(dāng)性。正是這些莊嚴(yán)的感情,千百年來叩響了讀者的心弦。
這首詞吐真情實(shí)感,自然率真。用個(gè)別表現(xiàn)一般,扣緊事物特點(diǎn),進(jìn)行高度概括,有代表性和形象性。語言單純明凈,許多不便說出或不易明白表達(dá)的內(nèi)容,他竟脫口而出, 自然率真,且用語清雋,形成了一種獨(dú)特的疏淡風(fēng)格,達(dá)到“疏而能深,淡而能遠(yuǎn)”的藝術(shù)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