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樓記文言文翻譯|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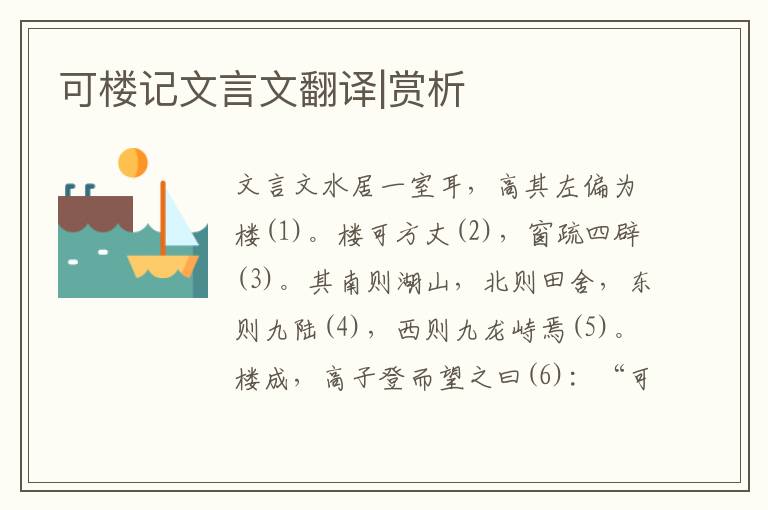
文言文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1)。樓可方丈(2),窗疏四辟(3)。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4),西則九龍峙焉(5)。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6):“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7),于水有悠然之旨焉(8),可以被風之爽(9),可以負日之暄(10),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11),優哉游哉(12),可以卒歲矣(13)!”于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時(14),慨然欲游五岳名山(15),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16),托而棲焉(17)。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逾齊魯殷周之墟(18),觀覽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飽。極力以營居處(19),而所安止幾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20),而止于歲時十一之游觀耳(21),將焉用之!
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22),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為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于茲樓也(23),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24)。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其贅矣。
翻譯
有一間水上的居室,室內偏左往上搭一間小樓。小樓一丈見方,四面開辟流通空氣的窗戶。南邊有湖有山,北面有農田茅舍,平原延展在東,九龍山聳立在西。小樓筑成,高子登臨縱目四望,說道:“可以了!我對山有和順舒暢的感覺,對水有悠遠閑靜的情義,可以享受清風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溫暖,可以迎接皓月的來臨,又歡送它的歸去,多么悠閑,多么自在呀!可以終老此地了!”于是起名叫“可樓”,意思就是我心滿意足以為可以了。
從前我年輕時,志向很大,想要游遍天下名山,尋找一個像桃花源那樣美好的處所,棲居下來。北方去了燕趙,南方到過閩粵,中原跨越了齊魯殷周的故地,觀覽所及的沒有可以滿我之意的,憑什現在對這間小樓就以為可以了呢?咦,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最大的危害,產生于有不滿足的心意。心意有不滿足,則產生于不滿足的事物;反之,沒有什么不滿足的心理,這就沒有什么事物不滿足了,這就沒有什么不使你快樂了。現在的人極力謀求口腹的享受,而得到的只是吃飽肚子罷了,極力建筑高樓大廈,頂多享受起居活動的幾席之地罷了極力營造亭臺花園,一年之中只是去游賞一兩次罷了,這些都有什么用呢?況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游玩,只要可以寄托我的志趣就行了。凡成為山水景物的處所都是一樣的,那么我對這座小樓,也認為是可以的了。雖然如此,有所可以也就會產生有所不可以,猶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對待的一樣。我將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如此說來這座可樓也是多余的了。
注釋
1.高:使……高。
2.方丈:面積方一丈,即俗稱“一丈見方”。
3.窗疏四辟:四壁開窗。
4.九陸:當是無錫平原地名。
5.九龍:山名,即惠山,在無錫,一名九隴山。惠山為九龍山第峰。峙:屹立、聳立。
6.高子:高攀龍自稱。
7.穆然之思:和順暢悅的感覺。《詩經》有“穆如清風”句,形容和悅清微之風。
8.悠然之旨:悠遠閑靜的志趣。旨:意志。
9.被風之爽:享受清風的爽快。被:受到。
10.負日之暄:得到冬日的溫暖。負暄,太陽照在背上。
11.賓:這里作動詞用,意思是像客人那樣接待它。
12.優哉游哉:《詩經》有“優游爾休矣”句,就是這個意思。后人加上“哉”字,變成感嘆詞,意思是:多舒適呀!多快樂呀!
13.卒歲:終老。卒:終結
14.曩:從前、過去。
15.五岳:古稱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衡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這里作為名山的總稱。
16.丘壑:陵谷。壑:山溝。桃花源: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理想安樂之鄉,這里泛指景色優美的山水勝地。
17.托而棲焉:寄居。棲,住下。
18.齊、魯、殷周之墟:齊魯指山東,殷周指河南。墟,故址、舊地。營其口腹:貪求美食。
幾席之地:起居活動的地方。幾席,形容所處地方之小。
19.營居處:建造居住的地方。營,建造,建筑。
20.苑囿:栽植林木、馴養禽獸的園地。
21.歲時十一: 文中指從每年適合游賞的時節中拿出十分之一的時間。歲時,每年一定的季節或時間。十一,十分之一。
22.日:名詞做狀語,這里是每天的意思。
23.茲:此。
24.與物為耦:與事物對等的。與物,相與附的事物。耦,與偶同,成雙作對。囚贅:多余、多而無用。
賞析
《可樓記》是明代文學家高攀龍創作的一篇散文。此文從作者名其樓為“可樓”的原因開始寫起,記述了其四面開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靜穆悠遠、優游自得,繼而引出了作者對對人生和處世哲理的探索,間接表達了他的不論窮達而主持正義,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精神。全文夾敘夾議,雖不以文名,但寫得簡潔而含蓄,平平略記,讀來卻飽含哲理。
為亭臺樓閣作記,在高攀龍之前,早有佳構。即以明代為例,劉基的《苦齋記》、宋濂的《閱江樓記》就頗具特色;歸有光的《項脊軒志》更是精美而真摯感人。高攀龍這篇《可樓記》卻異乎前人,名曰“記”,實則重在“議”,即只是平平略記其樓之建構和登望之樂,而把主旨和重心放在“可”與“不可”、“足”與“不足”的哲理與感嘆上。
文章開篇用一個自然段寫自己為什么名其樓為“可樓”,雖記述了四面開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靜穆悠遠、優游自得心態但在全篇中,它卻只是為議論蓄勢,有如放矢前的張弓。按常理推之,接下來作者當就可與不可展開題旨了,然而文章又故作遷回,寫了一小段自己年輕時所理想的“可”,以及觀覽祖國名勝后“無足可吾意”的“不可”。二者對舉,似乎又否了第一自然段說的“可”和年輕時企望的“可”。從文氣上看,似乎仍是引而不發;從邏輯和內蘊上看,這一段卻是作進一步的鋪墊,并迂回曲達,擺出了“不可”與“可”這矛盾和作者的疑惑心理。當然這樣寫正反映了作者經歷、人格和他所處明末社會環境的真實情感和心路歷程,但在寫法上,也避免了平庸和淺露。
第三自然段,既是文章的高潮所在,也是作作記的主旨所在。以傳統的觀念言之,“知足不辱”、“知足常樂”,而今人不知足,雖所得“止于一飽”,所安“止幾席之地”,仍要“極力以營其口腹”、“極力以營居處”凡此種種,既是對現實的影射,也是對傳統觀念的懷疑,更是對人生和處世哲理的探索。雖然高攀龍明言這種“不足”產生的“不可”是“人之大患”,并表明“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但明白人看來,其中隱含著作者的不平、憤與不記個人得失的操守。他的不論窮達而主持正義,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精神于此文之中亦可窺其一斑。
一般來說,明代散文總體說來,前期沉寂,貌岸然而無生氣。其后,文派紛起,但又復古、擬古,散文創作頗多優孟冠,不能“自為其言”。到隆慶、萬歷之際,企圖擺脫古人束縛而要求“直抒胸臆,唐宋派也提出了寫“新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的主張,公安派還倡導“獨抒性靈”。高攀龍雖不以文名,但他順應潮流,寫出這種簡潔而有自己見解的,有含蓄特色的散文,是難能可貴的。
作者簡介
高攀龍(1562—1626),明代文學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從、景逸。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歷十七年(1589年)進士,授行人。上書指責“陛下深居九重”,被貶謫為揭陽縣典史,又逢親喪家居,三十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間,他與顧憲成在家鄉東林書院講學,抨擊閹黨、議論朝政,影響較大,時人稱為“東林黨”。高攀龍為首領之一。天啟六年(1626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稅監李實奏本,誣告高攀龍等人貪污,魏忠賢借機搜捕東林黨人。該年三月,高攀龍不堪屈辱,投水自盡,時年六十四歲。著有《高子遺書》1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