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宗泰《游焦山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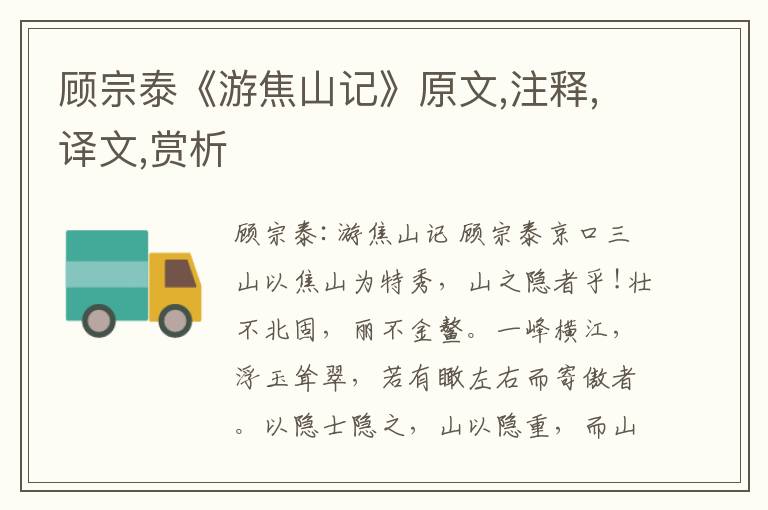
顧宗泰:游焦山記
顧宗泰
京口三山以焦山為特秀,山之隱者乎!壯不北固,麗不金鰲。一峰橫江,浮玉聳翠,若有瞰左右而寄傲者。以隱士隱之,山以隱重,而山可為隱士所隱,即謂山之隱者亦宜。
余自金山放舟,距山十五里,乘風(fēng)駕帆,雪浪層疊。遠(yuǎn)望山色,如黛螺之隱現(xiàn)水中,而不可即也。及抵山,則環(huán)峰竹木,縈煙繚云,佛舍精藍(lán),夤緣曲折,不露山骨,而若忘其為山。
始自東麓而西,過(guò)枯木堂,訪所為古鼎者,獰然伏地,指不敢捫,雷回云紜,龍翔夔躍,制何古也!至焦隱士祠,祠在瘞鶴巖下。華陽(yáng)之逸與孝然之隱,有后先輝映者乎!西行而上,石磴紆曲。經(jīng)三詔洞,升觀音羅漢諸巖,叢木蒼郁,路逼仄矣。峰回境轉(zhuǎn),憩吸江亭,造雙峰閣,此山之顛也。倚天而望,大江趨海,浴日浮天;北固、金鰲,指顧而得。吳楚之山川,英雄之割據(jù),有懷古浩然而塵襟頓豁者。昔人孤蹤幽抱,歸隱茲山,其有所寄于斯歟?夫漢未鼎沸,時(shí)事滔滔,獨(dú)焦孝然脫然身世,三詔不出,至今為山靈增色,山故名譙山,又名樵山,今易名焦山。
嗚呼!山以隱士隱,而山直欲寄傲于三山間矣,是亦山之幸矣!至山中青玉塢、碧桃灣諸勝,春時(shí)聽(tīng)鶯最幽處也。其山之余支,東出分峙于鯨波淼渺中者,為海門山,亦名松寥,夷山。孟浩然詩(shī)所云:“夷山對(duì)海濱”是也。未及游,故不詳記。
顧宗泰的游記散文,善于抓住所描寫事物的特點(diǎn)。鎮(zhèn)江的三座山,焦山的壯麗比不上北固山、金鰲山(即金山),然而以特秀見(jiàn)長(zhǎng)。本文不僅寫出了焦山特秀的外貌,更突出了它特秀的神骨,所以開(kāi)頭直接點(diǎn)明焦山是“山之隱者”。這不是一般的比喻,自古只聽(tīng)說(shuō)過(guò)人有隱士,未聞山也有隱者。士以山隱,山以隱重,二者有不可解之緣。原來(lái)作者是借人寫山,依山寫人,有一箭雙雕之巧,故而文中所寫“山之隱者”乃是全篇的文眼。
描繪這座隱者,筆法有兩大特色:一是描寫的角度變化多端。有遠(yuǎn)望:從距山十五里放舟寫起,山色如黛螺隱現(xiàn)水中,與江水雪浪層疊形成鮮明的色彩對(duì)比,動(dòng)靜相形。這又與下面“倚天而望, 江趨海,浴日浮天,北固金鰲,指顧而得、遙相呼應(yīng),可是二者又有區(qū)別。前文的遠(yuǎn)望,是從低處望,是山外望山;后文的遠(yuǎn)望,是從高處望,是山中望外。有近觀:環(huán)峰的竹木,縈繞的煙云,佛寺禪院,夤緣曲折,給山披上了盛裝,不露山骨,叫人忘記這是山。有詳察:枯木堂中古鼎的花紋,“雷回云紜,龍翔夔躍。”游歷的方向,先自東而西,寫了枯木堂、焦隱士祠。后自下而上,經(jīng)過(guò)三詔洞,登上觀音羅漢諸巖,在吸江亭上小憩一會(huì),到雙峰閣,到了山頂。從高低內(nèi)外描繪出焦山的靈秀和氣勢(shì)。二是敘述的安排錯(cuò)落有致。先看夾敘夾議:如開(kāi)頭寫到焦山”以隱士隱之,山以隱重,而山可為隱士所隱,即謂山之隱者亦宜”,這是作者的觀點(diǎn),貫穿全文的線索。寫到枯木堂中古鼎,一句慨嘆:“制何古也!”寫到焦隱士祠,發(fā)出議論說(shuō):“華陽(yáng)之逸與孝然之隱,有后先輝映者乎!”前者指南朝的陶弘景,自號(hào)華陽(yáng)真逸,隱于茅山;后者指漢末的焦光,字孝然,隱于焦山。作者認(rèn)為他倆都是高尚的隱者,能與之相輝映的實(shí)在不多了。寫到焦山歷代之隱者,又說(shuō):“其有所寄于斯歟?”這是揣測(cè)古人的心志。“嗚呼! 山以隱士隱,而山直欲寄傲于三山間矣,是亦山之幸矣!”這是直抒自己的情懷。再看縱橫捭合,貫古歷今。作者寫焦山的秀美,從空間上看,是通過(guò)自己的所見(jiàn),由外入內(nèi),又由內(nèi)到外來(lái)描述的;從時(shí)間角度看,除抒發(fā)自己的所感外,著筆的重點(diǎn)在焦山的得名上。從枯木堂的古鼎,到結(jié)尾引孟浩然的詩(shī),都彌漫一股懷古的氣息。把焦山的歷史與眼前的景物聯(lián)系起來(lái),情景交融,相映生輝。
這篇短文,用了十二個(gè)“隱”字。“山色如黛螺隱現(xiàn)水中”,“不露山骨而若忘其為山”,這是外形之隱。焦山多古跡,以隱士得名,這是神骨之隱,以“隱”寫焦山,以山托隱情,作者的立意正在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