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晏子春秋·晏子論和與同(外上·五)》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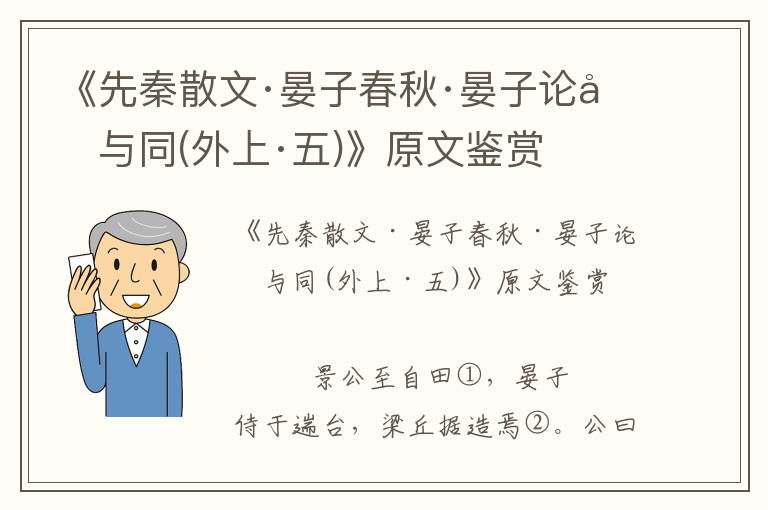
《先秦散文·晏子春秋·晏子論和與同(外上·五)》原文鑒賞
景公至自田①,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jù)造焉②。
公曰:“維據(jù)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jù)亦同也③,焉得為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④,水火醯醢鹽梅⑤,以烹魚肉,“”之以薪⑥。宰夫和之⑦,齊之以味⑧,濟(jì)其不及⑨,以泄其過⑩。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11)。臣獻(xiàn)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xiàn)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12),民無爭心。故《詩》曰(13):‘亦有和羹,既戒且平(14)。艘嘏無言(15),時靡有爭。’先王之濟(jì)五味,和五聲也(16),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17)、二體(18)、三類(19)、四物(20)、五聲(21)、六律(22)、七音(23)、八風(fēng)(24)、九歌(25)、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cè)帷⑦t速、高下、出入(26)、周疏(27),以相濟(jì)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28):‘德音不瑕(29)。’今據(jù)不然,君所謂可,據(jù)亦曰可;君所謂否,據(jù)亦曰否。若以水濟(jì)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國之不可也如是。”
公曰:“善。”
【注釋】 ①田:狩獵,打獵。 ②造:到。 ③同:一樣,相同。 ④和:調(diào)和,和洽。羹(geng耕):帶汁的肉,此言烹制肉羹。⑤梅:梅子,梅醢。梅子味酸,用來調(diào)味。 ⑥燀(chan 產(chǎn)):炊。⑦宰夫:庖廚,廚師。 ⑧齊(ji 濟(jì)):調(diào)和,調(diào)味使酸咸適中。 ⑨濟(jì):補(bǔ)助,增加。 ⑩泄(xie屑):減少。 (11)否:不可,指與“可”相反的事物和道理。 (12)干:犯,此指事物相互抵觸背逆。 (13)《詩·商頌·烈祖》。 (14)戒:告戒,指告戒宰夫要慎重調(diào)味。平:此指滋味適中。 (15)鬷(zong 宗)嘏(jia 甲):即“奏假”,“奏格”。奏:獻(xiàn)上,指獻(xiàn)羹。格:至,到來,指神來享。無言:無所指摘。 (16)五聲:古稱宮、商、角、徵(zhi)、羽為五聲。 (17)氣:氣息,氣勢。 (18)體:由身體表演的舞樂動作,古有文舞和武舞。 (19)類:指樂曲的類別。三類:即風(fēng)、稚、頌。 (20)四物;四方之物,指制作樂器的材料取自四方。(21)五聲:即五音。 (22)律:古代用來定音的一套竹管,共十二律,陰陽各六,陽稱六律,陰稱六呂。 (23)七音:在五音之外,再加“變宮”、“變征”。 (24)八風(fēng):八方的樂調(diào)。 (25)九歌:多種題材的歌舞。 (26)出入:奏樂時的呼氣與吸氣。 (27)周疏:周密與稀疏,指音節(jié)的繁密與稀疏。 (28)《詩·邠風(fēng)·狼跋》。 (29)德音:美好的名聲,盛名。瑕:遠(yuǎn)。
【今譯】 齊景公打獵回來,晏子在遄臺服侍他,梁丘據(jù)也趕到了。
景公對晏子道:“只有梁丘據(jù)與我是和洽的!”
晏子回答道:“梁丘據(jù)與國君只是相同而已,哪里稱得上是和洽?”
景公問道:“和與同有差別嗎?”
晏子答道:“有差別。和就像制做肉羹,要有水、火、醋、醬、鹽、梅等物,這樣烹制魚肉,再燒柴來炊制。由宰夫來調(diào)和滋味,要使味道酸咸適中,酸威不夠要加鹽加醋,過酸過咸要加水淡化。這樣君子吃了肉羹,平和其心。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也如此。國君所認(rèn)可的事情,里邊就有不可的因素。臣下進(jìn)言指出不可的地方,這樣就使國君的認(rèn)可更加全面。國君所否認(rèn)的事情,里邊也含有可行的成份。臣下進(jìn)言指出可行的事,這樣就排除了不合適的否認(rèn)。所以這樣制定的政令就不會自相矛盾,人們聽了政令就沒有爭議。因此《詩》中說:‘作好了和美的肉羹,告戒宰夫要調(diào)好五味。獻(xiàn)上肉羹神到來也無可指摘,人們也不會再有什么爭執(zhí)不和。’前代的君王所以重視調(diào)濟(jì)五味,調(diào)和五聲,為的是用來平和人心,取得政治的成就。音樂和滋味一樣,是多種條件的調(diào)和,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爿律、七音、八風(fēng)、九歌是相輔相成的。音樂曲調(diào)和節(jié)奏的清濁、大小、短長、快慢、哀樂、剛?cè)帷⑦t速、高下、呼出吸入、周密稀疏,是互相補(bǔ)充的。君子聽了五音諧和的音樂,平和其心。心意和平道德完美,所以《詩》中道:‘美好的名聲傳之久遠(yuǎn)。’如今梁丘據(jù)可不是這樣,國君認(rèn)可的,梁丘據(jù)也隨聲附和;國君所否認(rèn)的,梁丘據(jù)也跟著說該否。假若制作肉羹,只用白水加白水,誰能吃出滋味?若是演奏樂曲,只用琴瑟彈奏一個聲音,誰能聽到和諧的樂曲?同是要不得的道理就如此。”
景公道:“好。”
【集評】 明·楊慎評《晏子春秋》:“一語(晏子謂和與同異)展宕,文瀾可觀。多數(shù)之(晏子論聲亦如味),乃見不同。聲、味參喻,喻中設(shè)喻。”
【總案】 這篇?dú)v史故事與《左傳》昭公二十年的記事相同。
故事明確地提出“和”與“同”的論題。在晏子的思想中,二者存在著差異。他以生活中的事例作比,作了精辟的論述。晏子認(rèn)為,“和”就是把多種不同的事物或因素在一定條件下調(diào)和統(tǒng)一起來,使它獲得新的特質(zhì);而“同”則是同一事物或因素的簡單的量的增加,如同“以水濟(jì)水”、“琴瑟之專一”一樣,不會產(chǎn)生新的事物。他把這道理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說明兩種君臣關(guān)系的差異及利弊。故事中所講述的“和”與“同”這一對帶有哲理性概念,反映了古代人們對現(xiàn)實(shí)事物中存在的辯證關(guān)系的樸素認(rèn)識。
【附錄】
《論語·公冶長》:“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漢·司馬遷《史記·晏子列傳》(摘錄):“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jié)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
“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也。既見其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后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jìn)思盡忠,退思補(bǔ)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zhí)鞭,所欣慕焉。”
漢·劉向《晏子春秋·敘錄》(摘錄):“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qiáng)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jié)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nèi)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鐘之祿。……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jīng)》之義。又有復(fù)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fù)列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jīng)術(shù),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fù)以為一篇,凡八篇。”
漢·劉歆《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史記·晏子列傳·正義》引)
唐·柳宗元《辯晏子春秋》(摘錄):“吾疑其(指《晏子春秋》)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jié)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shù)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言不若是。后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柳河?xùn)|集》卷四)
明·楊慎《晏子春秋總評》:“楊升庵曰: ‘《六韜》述兵法,多奇計(jì);《申子》核名實(shí);《韓子》攻事情;《管子》多謀略;《晏子》危言行,善順衡,施之后主,正中其病,其藥要在對病而已。吾就《晏子》而觀其顯名當(dāng)世,誠不可及,而孔明偏疾之,亦不識時務(wù)矣。’
“又曰:‘《晏子春秋》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其《說苑》及《晏子春秋》口載以諷而從,不可勝數(shù)。蘇洵作《諫論》,欲以管、晏之術(shù)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當(dāng)時諷諫之妙,惟晏子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并垂不朽。’
“又曰:‘《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晏子顯名天下,而意念常有以自下,太史公稱之,蓋其謙而有終也。若夫王莽之下白屋,則又謙之賊矣。’
“又曰:‘鄭肅不入牛、李之黨,晏嬰不入崔杼之黨。《易》曰:“馬匹亡。”二子有焉。’
“又曰:‘《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多虛而可效,《法言》錯雜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獨(dú)《晏子春秋》一時新聲,而功同補(bǔ)袞,名曰《春秋》,不虛也。’”(引自《合諸名家批點(diǎn)諸子全書》)
明·余有丁《晏子春秋題辭》(摘錄):“自漢及隋、唐(《晏子》)皆列于儒家,惟柳柳州謂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shù)者,當(dāng)列之墨家。……第篇中眷眷忠愛,可為人臣事君盡言者法程,間有淆雜,或后人附蓋之,不得直概之墨也。”(緜眇閣本《晏子春秋》,見《先秦諸子合編》)
明·李茹更《晏子春秋題辭》(摘錄):“《晏子》八篇,即《孔子三朝記》之類,殆后人錄其言論諷議成書,書號‘春秋’,亦同‘記年’之意。其文多平實(shí),少奇崛,少波瀾,疑當(dāng)時記者手筆稍不逮故耶?然其書亦多傳古意,不可廢也。”(緜眇閣本《晏子春秋》,見《先秦諸子合編》)
清·惲敬《讀晏子一》(摘錄):“《晏子春秋》……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復(fù)重多……其為書淺隘不足觀覽,后之讀者未必為所惑。”(《大云山房文稿》二卷)
清·洪亮吉《論晏子獨(dú)成一家》(摘錄):“晏子不可云墨家,蓋晏子在墨子之先也。前人以之入‘儒家’,亦非是。……其(晏子)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愚以為管子、晏子,皆自成一家。前史《藝文志》入之‘儒家’既非,唐柳宗元以為墨氏之徒,亦前后倒置,特其學(xué)與墨氏相近耳。”(《曉讀書齋初錄》)
清·孫星衍《晏子春秋序》(摘錄):“《晏子》文最古質(zhì)。”(平津館刻本)
清·管同《讀晏子春秋》(摘錄):“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后人偽為者耳。……其文淺薄過甚,其六朝后人為之者與?”(《因寄軒文初集》卷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傳記》:“案《晏子》一書,由后人摭其軼事為之,雖無傳記之名,實(shí)傳記之祖也,舊列‘子部’,今移入于此。”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晏子春秋》八卷,撰人名氏無考,舊題晏嬰撰者,誤也。書中皆述嬰遣事,實(shí)《魏征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與著書立說者迥別,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體裁未允,改隸《傳記》,庶得其真。”
羅焌《晏子》(摘錄):“況子家敘事,多涉寓言,尤未可據(jù)為信史乎!今案:《晏子》一書,所載行事及諫諍之言,大抵淳于髡、優(yōu)孟、優(yōu)旃之流,故當(dāng)時稱為天下之辯士(《韓詩外傳》卷十)。擬之唐魏鄭公、李相國,殊未當(dāng)也。清儒馬輔氏著《繹史》,多采《晏子春秋》,而于《晏子使吳章》(《內(nèi)篇雜下》)則謂其詼諧;于《晏子使楚章》(同上)則謂其以謔對謔;于《諫景公飲酒七日七夜章》(《內(nèi)篇諫上》)則評曰‘談言解紛,滑稽之所以雄也。’(《繹史》卷七十七)……今以諸子十家衡之,當(dāng)屬俳優(yōu)小說一流(俳優(yōu)即古之稗官……)。非晏子為小說家也,輯是書者小說家數(shù)也。……”(《諸子學(xué)述》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