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定法、執(zhí)法、審法分而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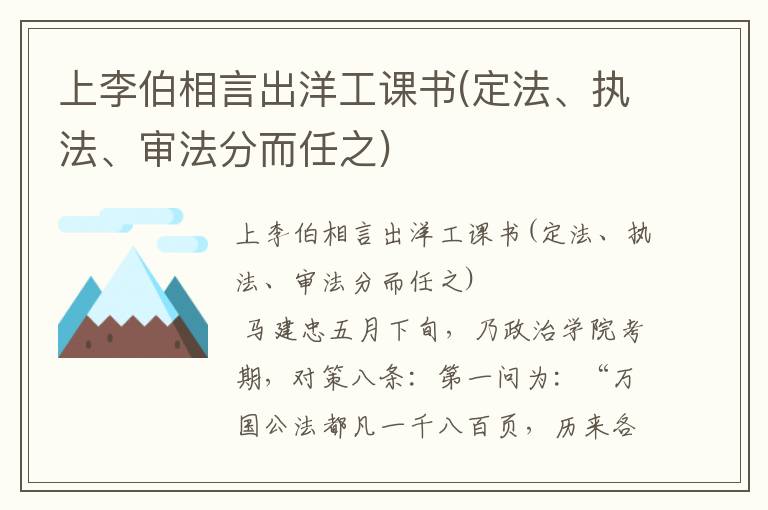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定法、執(zhí)法、審法分而任之)
馬建忠
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為:“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興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為:“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quán)量、錢幣、佃漁、監(jiān)犯及領(lǐng)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為:“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chuàng)興,而其要領(lǐng)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巨,要之以信,不患其眾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shù)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為:“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后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tǒng),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GF8CC]]縷而陳也。”第五問為:“英、美、法三國政術(shù)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蔽,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為:“普、比、瑞、奧四國政術(shù)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lián)絡(luò)各部,比為局外之國,奧為新蹶之后,措置庶務,孰為得失·”第七問為:“各國吏治異同,或為君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zhí)法、審法之權(quán)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quán)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于鄉(xiāng)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quán),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為:“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于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yōu)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lǐng),非徒鉆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為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余,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制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復質(zhì)證,而后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為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托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為借口。美之監(jiān)國①,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jiān)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茍非族類而欲得一優(yōu)差,補一美缺,戛戛乎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于各國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匯為一編,名曰聞政,取其不能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為進益也。西人以利為先,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lián)邦交焉。現(xiàn)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無所學,涉獵不廣,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②栽培之意,下無忘西學根本之論,敢云立說也哉。作于1877年夏選自《適可齋紀言紀行》
〔注釋〕 ①監(jiān)國:指美國由選舉而產(chǎn)生的總統(tǒng)。 ②中堂:指李鴻章。〔鑒賞〕 馬建忠(1845—1900)所說的定法、執(zhí)法、審法三權(quán),“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quán)不相侵”,就是三權(quán)分立的學說。這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建忠出身于江蘇丹徒(今屬鎮(zhèn)江)一個天主教的家庭。1853年去上海耶穌會徐匯公學讀書,學法文與拉丁文。后與四哥馬相伯(復旦大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一起,到該會設(shè)立的初學會當修道士。因熟悉西洋文化,為李鴻章賞識并當上他的幕僚。該篇是馬建忠向上司李鴻章匯報留法期間的情況與見聞。今天,它是反映近代中國中西思想交匯的珍貴實錄。國人最早對西方三權(quán)分立學說作介紹的是馬建忠:“各國吏治異同,或為君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zhí)法、審法之權(quán)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quán)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定法”權(quán),就是制定法律以及修正或廢止已經(jīng)制定的法律的權(quán)力。“執(zhí)法”權(quán),是執(zhí)行立法機關(guān)意志的權(quán)力。“審法”權(quán),也就是司法權(quán),是懲罰犯罪和裁決私人爭訟的權(quán)力。立法權(quán)、行政權(quán)與司法權(quán),由三個不同的權(quán)力機構(gòu)來掌握和行使,是三權(quán)分立學說的基本思想。這一思想由英國哲學家洛克明確提出,而成為一種系統(tǒng)的學說,是法國哲學家、政治學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一書面世后的事情。孟德斯鳩指出,這三種權(quán)力是獨立的,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以權(quán)力制約權(quán)力,彼此互相牽制,協(xié)調(diào)前進。否則的話,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自由:“如果司法權(quán)不同立法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在他看來,“一切權(quán)力合而為一,雖然沒有專制君主的外觀,但人們卻時時感到君主專制的存在”。三權(quán)分立學說,在歷史上有它的進步作用。三權(quán)分立的制衡原則為資產(chǎn)階級設(shè)立了一個反封建專制和依法治國的完整方案,為防止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倒退到封建專制增設(shè)了一道障礙。為什么馬建忠能充當這一角色呢·這與馬建忠出洋留學的經(jīng)歷及其貨真價實的洋務派思想相關(guān)。187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成為洋務派的首領(lǐng),馬建忠投奔其門下幫辦洋務。1876年,馬建忠受李鴻章選派赴法學習。在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期間,兼任中國駐法大使郭嵩燾的翻譯。1880年回國后,李鴻章把他從一般隨員,提升為主要幕僚。1884年,被派為輪船招商局總辦。1890年,又調(diào)為上海織布局總辦。“歷上書言借款、造船、創(chuàng)設(shè)海軍、通商、開礦、興學儲材,北洋大臣李鴻章頗賞之,所議多采行。”(《清史稿·馬建忠傳》)對西方各國富強的原因,馬建忠的認識已從“末”轉(zhuǎn)向了“本”:“此次來歐一載有余,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制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西方國家富強之本,不在于制造精、兵紀嚴,而在于保護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與議院制度的建立。其見識已超過一般洋務派的水準。在國人尚停留在仰慕船堅炮利、聲光化電(“末”)時,馬建忠敏銳地覺察到了西方各國強大的緣由,是因經(jīng)濟與政治制度(“本”)造成的。他高度贊揚三權(quán)分立,以為付諸實行能使“政事綱舉目張”,是對君主專制的強有力挑釁。在奉天承運、口出天憲的皇權(quán)專制的現(xiàn)實情況下,馬建忠如實地介紹三權(quán)分立學說,站在了時代的前列,無疑是有啟蒙意義的。梁啟超稱贊馬建忠說:“每發(fā)一論,動為數(shù)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議,皆為數(shù)十年以后治中國者所不能易。”(《適可齋記言記行·序》)20世紀初,嚴復動手翻譯《論法的精神》,把中譯本命名為《法意》;不過書的出版已是1909年的事情了。馬建忠把三權(quán)分立的政治學說介紹到中國,比嚴復早了差不多二十多年。《馬關(guān)條約》訂立后,在政治上心灰意懶的馬建忠,集中精力于著述。其《馬氏文通》一書,是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該書的語法分類、定義和許多概念至今仍在使用。講到馬建忠,人們都會想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