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秋蟲的地方》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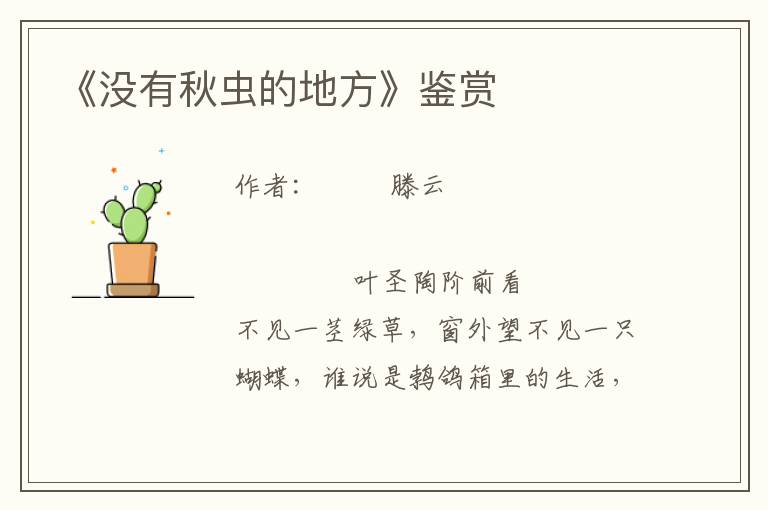
作者: 滕云
葉圣陶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只蝴蝶,誰說是鵓鴿箱里的生活,鵓鴿未必這樣趣味干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弦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并起的清晨,無論你靠著枕兒聽,憑著窗沿聽,甚至貼著墻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并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里本沒有秋蟲這東西。呵,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閑;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云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著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它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仿佛曾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眾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人間絕響的呢。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嘆,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于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為生活不空虛了。假如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著笑意來體味它;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著眉頭來辨嘗它;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為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的夢,一口苦水勝于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于哀樂兩忘。但這里并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里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于是足系戀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妙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它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里。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征的意味豐富極了。
秋天來了,秋天是使人思緒清飏的季節。
古人有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真是的啊,春不是使人意萌?夏不是使人情暢?秋不是使人思遠?冬不是使人氣凝?
四時物候,都能撼動人心,就中唯有秋最逗人思量也最耐人思量。為什么這樣誰能說得清?可又為什么定要說清?世人都認同了天時與人心交接的這一點玄秘,都認同了“思”與“秋”連屬,“思”是“秋”之韻秋之神。
于是在秋朝秋暮時,秋風秋雨邊,秋水秋云外,秋蟲秋聲里,就有“勞人的感嘆,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了,就有文人們從古到今不絕如縷地吟詠的秋思。
葉圣陶的秋思別是一格。他是在“沒有秋蟲的地方”寄托他的秋興的。
沒有秋蟲的地方哪里會有秋聲啊?的確沒有。深夜,清晨,靠著枕兒,憑著窗沿,貼著墻角——無論如何尋如何覓,沒有一絲秋蟲的聲息。要知道這正是鄉野間蛩鳴漫世界的時令哪!那或高或低,或宏或細,時疾時徐,時作時歇的蟲聲,雖然足以引起勞人、秋士、獨客、思婦的憂思與愁懷,但蟲兒們自己卻是在向宇宙抒唱它們生命的華采樂章啊!那活躍在大自然懷抱里的生命的音籟,盡管使人類感受到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但卻是無窮雋永的讓人想起生命之神妙與靈趣的味道啊。
然而這里沒有蟲聲,只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泥地,根本不能容留秋蟲。沒有秋蟲,也就沒有宇宙生命的交響了,只有錮閉與空虛。不能容留秋蟲,也就不能容留自然生命的合奏了,只有淡漠與無味。可人類與人生總該是要體嘗生命的味道的啊。哪怕是嘗出酸苦愁怨,也遠勝麻木。哪怕是耽于熱夢,也遠勝冷漠渾沌的醒。哪怕是長歌當哭,也遠勝哀樂兩忘。哪怕是秋蟲最后生命的吟唱,也遠勝身如枯木心如古井。
難道人不應振起生命的律動,贏得生命的升華么?看啊,這錮閉的庭院,這灰色的空間,連秋蟲都不屑于滯留了,它們都飛到生命環舞與喧鬧的原野上去了,人還要死守在這井底這灰色中么?
作者的文章做到這里,做成這樣,就已經不只是寫秋蟲,賦秋聲了。
秋蟲是寫的,秋聲是賦的,通篇都在賦寫;但又不止于此。文章首段,從尋秋蟲覓秋聲始,尋尋覓覓,那樣執著,終于找不到,一句這里是“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留的地方”,就把并非為秋蟲而寫的作意,逗露著了。文章頷段,由此處無秋蟲秋聲,引起對鄉野間秋蟲秋聲的思憶,狀寫入神,秋的天籟與秋的情懷交回復沓。文章頸段,從秋聲引發的人生況味宕開去,說到人應當有生命情味的體嘗,而麻木的淡漠無味的生活狀態不可取。文章尾段,回接首段而加以申發,從秋蟲不見容于也不屑留連于這“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返顧人類,籌思人類;假若人不如秋蟲,不想也不能飛出跳出這“井底”這“鉛色”,去尋覓、爭取、創造、開拓能夠發揮生命的極致的空間,反而死守這井底這灰色,那才是可感喟的啊,才是真的秋聲啊。
是的,金風颯颯,蛩吟陣陣,涼意初透,把古往今來多少勞人、秋士、獨客、思婦的秋心都摧動了,何況慧業文人?
我們的作者也受著感動。但他不作秋的清吟淡唱。他的心沉實,并不隨秋氣的搖落而散入杳冥。他執著于大地人間,他寫秋蟲賦秋聲,秋思卻只為“沒有秋蟲的地方”而發,為人的生存境況而發。別人聞秋蟲凄切起興,他的秋思卻在無秋蟲可覓處。別人所賦秋聲在天籟,他所賦秋聲在天籟更在人籟——他賦的是人間秋聲。他手寫此處,目注彼處,筆下生命的繁響與生命的寂然同構,秋蟲秋聲與人的生存境況渾融。他的寫法不是機械比附,不是具體象征,而是整體寫實與整體象征的統一。文章意旨切實而不鑿實,境界沉著而宏遠。文字也好,求精煉而不求精巧,有深意又樸素自然,沒有雕琢之痕。其意其文,一新歷來文士吟秋之作面目——大概是可以這樣說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