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廷晴《樹上的姑娘》散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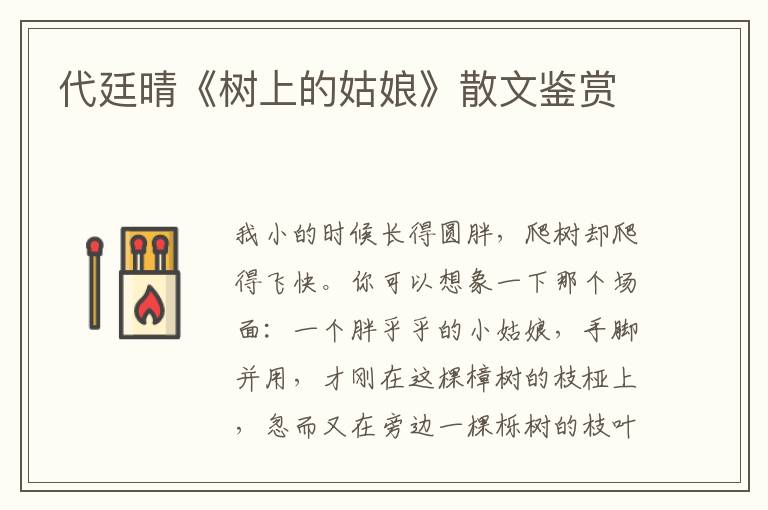
我小的時候長得圓胖,爬樹卻爬得飛快。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場面:一個胖乎乎的小姑娘,手腳并用,才剛在這棵樟樹的枝椏上,忽而又在旁邊一棵櫟樹的枝葉間冒出頭來。
我們吃的水果和干果,基本上都是自己家種的。父親是個很勤快的人,種了許多果樹。果子成熟了,父親卻忙于農活,往往沒有更多的時間幫我摘下來。
要吃上這些果子,單靠我哥是不夠的,雖然他常常坐在樹杈上拋給我一個個歪屁股的粉紅桃子或里面帶了欲滴“果油”的青脆李。我想我得自己學爬樹。
開始的時候只能爬上低矮的樹,后來慢慢地越爬越高,甚至可以爬到樹巔上,摘到最熟最好吃的果子。
屋后有一棵老梨樹,每年春天開雪白的花。風一搖,花瓣厚厚地覆在樹底下稀疏的茅草上。秋天的時候,卻只在高高的樹巔上顫巍巍地懸著幾只碩大的梨。有一天,我爬了上去,摘到了曾經仰頭看了許多次的那幾個梨。我先坐在樹杈上吃了一個。梨子很好吃,我想著給母親帶下來。常年勞累沒有笑容的母親,吃一個甜甜的梨,也許會笑一下吧,我想。
那天穿的衣服還薄,且沒有口袋。我只能一只手拿著梨,一只手抱著樹,慢慢地往下滑。卻不想梨樹上原是長刺的,上去的時候沒覺察到,現在我滑下來,那根刺剛好劃到我肚子。我盡量吸著氣,把肚皮往里縮。刺沒有把肚子劃穿,但還是留下了一條深深的剮痕。現在也還有一條淡褐色的印跡。
除了摘自己家種的果子,我還會爬樹摘野果。
那時候山里的野果是很多的。野酸棗,野生的獼猴桃,還有八月瓜,隨處可見。八月瓜長得像個豬腰子,表皮綠色帶麻點。成熟之后,瓜皮呈褐黑色。再熟些,中間的那條縫會自己裂開,里面的肉瑩白如澧酪,籽黑亮如珍珠。八月瓜的藤是牽在別的樹上的。柏楊樹啊,杉樹啊,都是它攀緣的對象。“緣木求瓜”是我常做的事。
我會爬到那高高的樹枝上坐著,手一伸,便摘到已經自己裂開了縫的八月瓜。有一次我摘了一大堆,數下來竟有三十八個!
學會爬樹也不全是為了找吃的,也是為了要掙零花錢用。雖然我父親那時承包了村里的小煤廠,日子并不拮據,但孩子們自己掙零花錢卻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一種習慣。七八歲時,我就可以去山里摘金銀花賣錢了。
春暮夏初,鄉村的山間道旁,野嶺荒地,金蕊銀花到處怒放,那就是“金銀花”。 它的藤依附在樹上,枝蔓交錯。開花時節,蔚為壯觀。花初開時是白色,后漸次變黃。我爬上它纏著的樹,把花摘回來攤在竹編的篩子里。把摻雜在花朵里的細葉兒再一次揀干凈,用筲箕裝上,再用開水快速汆一下,瀝干,大太陽下曬一天,第二日便可以拿到村里小小的收購站去賣了。曬干的金銀花,不論生前是黃是白,此際都是一種透明的暗黃色。它們曾經鮮妍的青春,現在留下一縷幽香的夢。
下午,太陽落山,我把曬干的金銀花小心地裝在塑料袋里,封好口。夜里睡下,腦子里想著上次趕集時看上的粉紅襯衫。那上面印著一朵一朵小小的星星,會在夢里晃我的眼。
為了掙錢,小小年紀的我,已經會做許多事情,比如“割棕”。
老家的田邊地角,棕樹褐身綠冠,葳蕤成林。晴日可遮陽,雨天可躲雨。同時,那棕皮還是我的一筆財富。我不知道它的具體用途,只知道小收購站會以八毛一斤的價格收購。
把一把小尖刀磨得飛快,刀尖順著長棕葉的那一側,往下輕輕一劃,輕脆的“呲啦”一聲,再繞著棕樹干往棕片底部劃一圈子,一塊棕皮便被揭下來了。緣著棕葉的另一側再劃一刀,然后一塊塊碼整齊,待其干透,捆扎好,便又可拿去收購站換錢了。
遇到長得過高、站在地上夠不著的棕樹,我也自有辦法,那就是借助“割棕棒”。“割棕棒”比用梯子方便許多。尋一截七八寸長、手臂般粗的木棍,再弄一段竹篾,做成牢實的繩子。繩子一頭固定在木棍上,一頭是活動的結。要用時,只需把繩子往棕樹上一繞,活動的那一頭套在木棍的另一端,再旋轉至緊。我兩個腳板往割棕棒上一蹭,刺溜就爬上棕樹去了。
那時的鄉下孩子,基本都會爬樹。但是一個女孩子,像我這樣“野道”的,不多。
我不僅摘過金銀花,割過棕,還打過桐子和棬子。
據老人說,桐子開花時,天氣都會變冷。農諺云:“放牛娃兒不要夸,還有三月桐子花。”桐子花開的時節,是要冷幾天的,叫“凍桐花”。粉紅粉白的桐花漸飄漸落,融入土里,天氣便是真的轉暖了。
父親曾用一上聯考我:“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樂。”我敲著腦袋想,當然是想不出下聯的。父親便呵呵笑,綻開一臉的皺紋。
山里的桐子樹,因為要爭陽光,會長得很高。主干是筆直的,枝椏是一圈兒一圈兒地長。遠看,是一座座綠色的小寶塔。
桐子由綠轉黃,再變為褐黑色,熟了,密密沉沉掛在樹上。長得低矮的,可以用竹竿撲打下來。再高一點的,需要爬上樹去打。桐子樹的皮是光滑的,對于我這樣一只靈活的胖猴子來說,那是毫無難度的啊。
打下來的桐子,堆放在雜屋間五六天,要把外面一層果肉漚爛掉才能剝出桐子瓣來。剝的時候,母親忙完七七八八的活兒,便在燈下坐下來幫我。看著母親粗糙的手上黑乎乎的爛果殼,我莫名鼻酸。
一背篼桐子,四五十斤重。我背去賣了,欣欣然買一件衣服,剩下的錢會如數交給母親。
打棬子的活兒更多的時候是大人去做,小孩子只是幫幫忙,而且賣了錢也歸大人。
棬子的殼在秋天成熟后會自動奓開成四瓣。它的籽凈白如玉,撫之潤滑。棬子尖圓的葉紅黃綠相間,繽紛絢麗。被大人們用柴刀斫下的枝葉躺在焦黃的草地上,枯敗的美讓我覺得憂傷。
現在,許多棬子樹都砍掉了,偶爾還有一兩棵,身上疤痕累累,在長滿野茼蒿的田埂上寂寞地站著。
多年我才知道,棬子也叫“烏臼”。《西洲曲》里說“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也不過是尋常物事啊。
小時候的我,性乖而口訥,說話囁囁嚅嚅,怕與人交往,但與植物們,卻向來覺得親切。曾用葛藤編織成一個大大的網,把它掛在櫟樹上。我鉆進網里,晃晃悠悠,渾然欲睡,不知算不算“筑巢而居”。又曾把木頭架在兩棵并排的樹中間做成梯子,一個人坐在上面,仰頭望葉隙間碎碎的藍天,或低頭看一朵白色的山茶花,怎樣一瓣一瓣打開它羞澀的心。我也在打開著我自己。
老家的櫻桃又紅時,我女兒站在樹下,軟白的手撫摸著粗糙蒼老的樹皮。見我在枝上葉間伸展自如,她一臉的羨慕和驚奇。
(作者單位:貴州省遵義市余慶縣他山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