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散文名篇·梅圣俞詩集序》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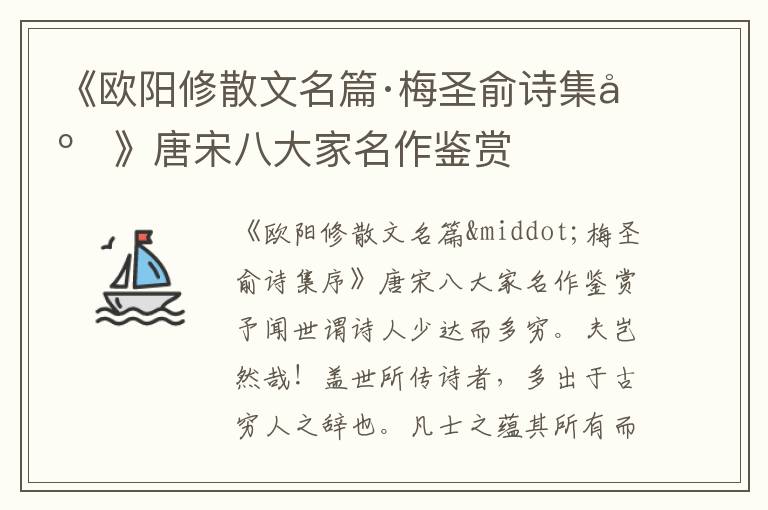
《歐陽修散文名篇·梅圣俞詩集序》唐宋八大家名作鑒賞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①,少以蔭補②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馀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③,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④,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⑤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⑥,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馀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⑦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注】
①梅圣俞:名堯臣,北宋詩人,為詩力主平淡,反對浮艷,當時影響很大,有《宛陵先生集》。②蔭補:因上代官爵而推恩補官。③辟書:聘書。古代地方長官可自行延聘幕僚。④宛陵:今安徽宣城市。⑤王文康公:王曙,官至宰相,卒謚文康。⑥薦之清廟:推薦到太廟。太廟,皇帝的祖廟。⑦掇其尤者:選擇其中優秀的作品。掇,選取。
梅堯臣,字圣俞。他雖然生活在宋朝比較強盛、開明的時代,但個人的人生遭遇卻頗為不幸,一身的才華“不得奮見于事業”。他的作品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風格平淡樸實,有矯正宋初靡麗傾向之意。他注重詩的政治內容,并認為寫詩須“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這一審美創作思想對后世影響頗大。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0),歐陽修為梅堯臣作了這篇詩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堯臣在矯正宋初浮艷詩風方面的功績,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宣揚自己“窮而后工”的文學主張。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就是因為提出了“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
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入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郁感憤、然后興于怨刺的產物;最后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后工。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構思。其后,歐陽修分層論述梅堯臣其人、其詩,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后工”的道理。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嘆其懷才而不得用于世,可悲可嘆,這悲嘆的底蘊還是“窮”和“工”。
工者,美也。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后,有感而發,順勢而帶出嘆梅終不得志的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則必將功德宏偉,這是大起大揚;后文突轉,通過實寫久而將老不得志,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表達對友人無限的欽佩和懷念,感人至深。
后人評論
儲欣《唐宋八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稱贊歐陽修的文章是“千古絕調,此移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