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柔》原文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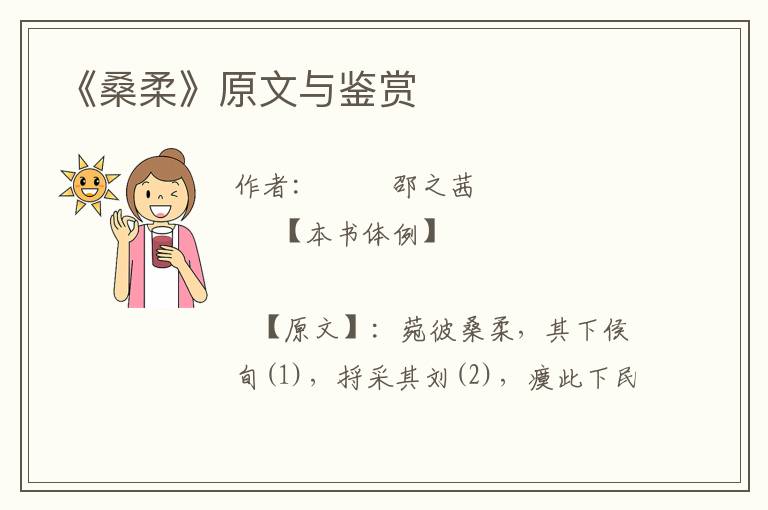
作者: 邵之茜 【本書體例】
【原文】: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1),捋采其劉(2),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3)。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4),旗旟有翩(5)。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6),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慇慇(7),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8),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溯風,亦孔之僾(9)。民有肅心,荓云不逮(10)。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11)。哀恫中國(12),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13)。朋友已譖,不胥以穀(14)。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圣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15)。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16)。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17)。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18)。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鑒賞】:
這是一首典型的政治諷喻詩。它是周厲王時的卿士芮良夫為諷刺厲王而作的。《詩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左傳·文公元年》有秦伯賦周芮良夫之詩的記載,而所賦的詩句就是本詩第十三章。《潛夫論·遏利篇》中寫道:“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我們參照《國語·周語》、《逸周書·芮良夫解》等有關資料來看,過去的說法是一致的,可靠可信的。芮良夫是姬姓,封于芮,即現在陜西同州朝邑縣,良夫是他的名字,至于此詩寫作的時間,一說在周厲王統治之時;另一說法是厲王被流放到彘之后。吳闿生說:“今考詩明言‘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必非無故而為此危悚之詞。其為厲王流彘后作甚明。其時天下已亂,芮伯蓋憂亡之至,而追原禍本作為此詩。”我們認為,這一說法是比較合理的。
統治階級在其政權相對穩定或鞏固之時,其內部矛盾會趨于緩和,相對和平,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則是“頌聲大作”,頌美貴族德行和勛業以及家業興旺的詩篇,在《雅》、《頌》之中比比皆是。而當社會動蕩,內憂外患,國勢衰微的情況下,統治階級的內部也常常發生紛爭與對立。少數對現實有較為清醒認識的有識之士,他們作為統治階級的成員,目睹和了解了統治集團黨爭的內幕、政治的黑暗腐敗,站在替貴族階級的前途和命運憂慮以及維護當時政權的立場上,來揭露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指斥當權者的惡德惡行,申明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主張。反映這類內容的詩歌,就是貴族階級的政治諷喻詩。所謂諷喻,即是用委婉的語言進行勸諫,但有些詩歌語言并不委婉,甚至就是諷刺和批判。雅詩中的政治諷喻詩大多產生于厲王、幽王時期,因為厲王和幽王暴虐、昏庸,實行暴政,這兩個朝代也是西周最為黑暗的時期。這篇詩歌反映的就是厲王時期傷亡亂離的景象。西周王朝到了周厲王時期發生了嚴重危機。周厲王是一個極其暴虐的君主,他任用榮夷公作執政卿士,實行專利政策,當時以貧民為主體的國人對厲王的專利政策表示強烈的不滿,議論紛紛,嚴厲譴責,厲王則采了殘酷的手段,對國人進行鎮壓殺戮,并從衛國找來一個巫士監視國人,禁止國人議論,當時國人不敢說話,只能“道路以目”,(見《國語·周語上》)厲王因此而非常得意,召公勸諫他不聽,芮良夫勸諫他不要用榮夷公,他也不聽,終于造成了國人大暴動,鎬京大亂,迫使厲王狼狽逃走,芮良夫也逃難東去,作此詩以指斥執政大臣、諷刺厲王。這就是此詩的寫作背景。
全詩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后八章每章六句。首章以形象的比喻總寫當時暴政虐民的政治局勢以及作者憂心如焚的心情,作者內心的憂慮之情無處訴說,只好呼天自訴。次章寫由于頻繁的征戰,使人民四處逃難,死傷無數,到處都是傷亡亂離的悲慘景象。第三章先寫國家的窮困與災亂,繼而寫到要追尋造禍的根源。第四章寫自己生不逢時的悲怨和憂國憂民之心的殷切。第五章寫作者關心王朝命運,希望任用賢人,救國安民,迅速消除蔓延的禍亂。第六章寫作者提出了要重視稼穡的建議,想以此來挽救危急的局面。第七章寫天降災害,而無力拯救,只好對天呼叫。第八章寫人君有順理與背理之分,用人有恰當和不當之別,痛惜厲王咎由自取。第九章寫由于集團的內訌,使賢者陷入進退維谷的地步。第十章、十一章寫人君有賢愚之別,贊美賢者才高品優,揭露愚人殘忍狠毒,并指出厲王縱恿惡人正是國人暴動的根源。第十二章用大風來自深谷,比喻人的善惡各有原因。第十三章寫厲王任用貪利之人,拒絕善言。第十四章警告同僚:胡作非為,必定自食其果。第十五章寫人民作亂的原因是為政者貪暴無度,反復無常。第十六章歸結作詩之由。
從全詩的內容來看,它描寫了周厲王時期在全國蔓延著的災禍動亂的政治局勢,人民大量傷亡,社會動蕩不安,國內呈現出一片悲慘景象。它既是時事風云的逼真記錄,又是國家興衰的生動概括。作為生活的藝術再現,此詩對現實的反映是具有一定的深度與廣度的。詩中反映了國人的抗暴斗爭。如詩的最后兩章“民之罔極”、“民之回通”、“民之未戾”等句子,不是從正面來寫,是間接來寫的。同時也指出了大暴動的原因在于厲王的“職涼善背”、“職競用力”、“職盜為寇”。誠然,詩人還不能夠正確理解人民抗暴斗爭的正義性,但仍以同情的態度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而且極為大膽地將國人暴動的原因歸罪于厲王的倒行逆施和兇殘暴虐,這是十分可貴的思想,已超越了當時卿大夫的傳統觀念。詩中強烈地譴責了周厲王執政邪辟,獨斷專行,目光短淺,自以為是,貶退忠良,庇護群小的昏惡行為。詩人筆鋒所向,直指君惡,慷慨陳辭,痛徹淋漓,同時對榮夷公貪財嗜利,助王為惡的罪惡也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表現出盡瘁國事,不避權貴的無畏精神。詩中還表達了作者憂國憂民的思想。對國家命運深切關注,對人民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從而表現出詩人面對現實的積極態度。總之,此詩反映了周厲王時的社會現實,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和認識價值。
此詩在寫作上運用了夾敘夾議、正反對比的方法來進行勸諫和說理,并將敘事、說理與抒情融為一爐,字里行間灌注了作者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因而使詩歌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欣賞價值。大量運用生動、貼切的比喻,是本詩在寫法上的又一特色。此外,還運用了豐富的語匯,尤其是諍諫語言既莊重陳情,又不乏激憤嚴猛的辭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