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三首)》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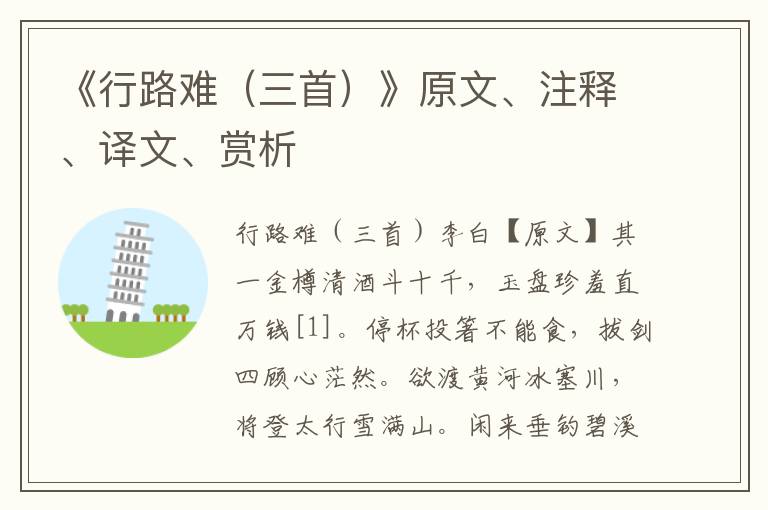
行路難(三首)
李白
【原文】
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1]。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2]。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3]。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羞逐長安社[4]中兒,赤雞白雉賭梨栗。
彈劍作歌[5]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6]。
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7]。
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
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
行路難,歸去來!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8],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9]苦不早。
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10]?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
【注釋】
[1]金樽:古代盛酒的器具,以金為飾。清酒:清醇的美酒。斗十千:一斗值十千錢(即萬錢),形容酒美價高。珍羞:珍貴的菜肴。羞,同“饈”,美味的食物。直:通“值”,價值。
[2]“閑來”二句:暗用典故:姜太公呂尚曾在渭水的蹯溪上釣魚,得遇周文王,助周滅商;伊尹曾夢見自己乘船從日月旁邊經過,后被商湯聘請,助商滅夏。這兩句表示詩人自己對從政仍有所期待。
[3]長風破浪:比喻實現政治理想。云帆:高高的船帆。船在海里航行,因天水相連,船帆好像出沒在云霧之中。
[4]社:古二十五家為一社。
[5]彈劍:戰國時齊公子孟嘗君門下食客馮諼曾屢次彈劍作歌怨己不如意。
[6]賈生:洛陽賈誼,曾上書漢文帝,勸其改制興禮,受到大臣反對。
[7]擁篲:燕昭王親自掃路,恐灰塵飛揚,用衣袖擋帚以禮迎賢士鄒衍。篲(huì),掃帚。
[8]含光混世貴無名:此句言不露鋒芒,隨世俯仰之意。
[9]稅駕:猶解駕,休息之意。
[10]“華亭”二句:寫李斯。《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倶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倶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太平御覽》卷九二六:《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門,不可得矣。”
【賞析】
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李白奉詔人京,擔任翰林供奉。李白本是個積極人世的人,才高志大,很想像管仲、張良、諸葛亮等杰出人物一樣干一番大事業。可是入京后,他卻沒被唐玄宗重用,還受到權臣的讒毀排擠,兩年后被“賜金放還”,被變相攆出了長安。《唐宋詩醇》以為《行路難三首》皆是李白于天寶三載(744年)離開長安時所作。這三首詩聯系緊密,不可分割。
“行路難”多寫世道艱難,表達離情別意。李白《行路難》共三首,以“行路難”比喻世道險阻,抒寫了詩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艱難時,產生的不可抑制的激憤情緒;但他并未因此而放棄遠大的政治理想,仍盼著總有一天會施展自己的抱負,表現了他對人生前途樂觀豪邁的氣概,充滿了積極浪漫主義的情調。
第一首詩開頭寫“金樽清酒”“玉盤珍羞”,描繪了一個豪華盛大的餞行宴飲場面。接著寫“停杯投箸”“拔劍四顧”,又向讀者展現了作者感情波濤的沖擊。中間四句,既感嘆“冰塞川”“雪滿山”、又恍然神游千載之上,看到了呂尚、伊尹忽然得到重用。“行路難”四個短句,又表現了進退兩難和繼續追求的心理。最后兩句,表達了盡管理想與現實有著巨大的距離,盡管詩人內心痛苦,但還是在沉郁中振起,堅定了信心,重新鼓起了滄海揚帆的勇氣。
全詩在高度彷徨與大量感嘆之后,以“長風破浪會有時”忽開異境,堅信美好前景終會到來,因而“直掛云帆濟滄海”,激流勇進。蘊意波瀾起伏,跌宕多姿。
第二首詩表現了李白對功業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頓中仍然想有所作為的積極用世的熱情,他向往像燕昭王和樂毅等人那樣的風云際會,希望有“輸肝剖膽效英才”的機緣。
詩一開頭就陡起壁立,讓久久郁積在內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噴發出來。亦賦亦比,使讀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內容十分深廣。用青天來形容大道的寬闊,照說這樣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緊接著卻是“我獨不得出”,就讓人感到這里面有許多潛臺詞。這樣,這個警句的開頭就引起了人們對下文的注意。“羞逐”以下六句,是兩句一組分別寫自己的不愿意、不稱意與不得志。“君不見”以下六句,深情歌唱當初燕國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對建功立業的渴望,表現了他對理想的君臣關系的追求。但唐玄宗這時已經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沒有真正的求賢、重賢之心,下詔召李白進京,也只不過是裝出一副愛才的姿態,并要他寫一點歌功頌德的文字而已。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對“行路難”作具體描寫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么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難,歸去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只有此路可走。這兩句既是沉重的嘆息,也是憤怒的抗議。
篇末的“行路難,歸去來”,只是一種憤激之詞,只是比較具體地指要離開長安,而不等于要消極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時他還抱有它日東山再起“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幻想。
第三首詩純言退意,與第一篇心情有異。通篇以對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須含光混世,不務虛名;中八句列舉功成不退而殞身者,以為求功戀位者誡;最后贊成張翰唯求適意的人生態度。一篇之意三層而兩折。言虛名無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則須及時退身,一為避禍,二求適意自由。這是李白人生哲學的基調。
如果說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宮廷的腐敗,此首則在揭露宮廷政治的黑暗和險惡,兩方面都是詩人在長安宮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辭官的理由。最后他對及時身退的張翰表示贊賞,正如前兩首的結尾一樣,不過是無可奈何之下的強自寬解,也是對現實表示抗議的激憤之詞。這種執著于現實人生的積極態度,既是李白悲劇的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詩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