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詩(shī)甄辨柿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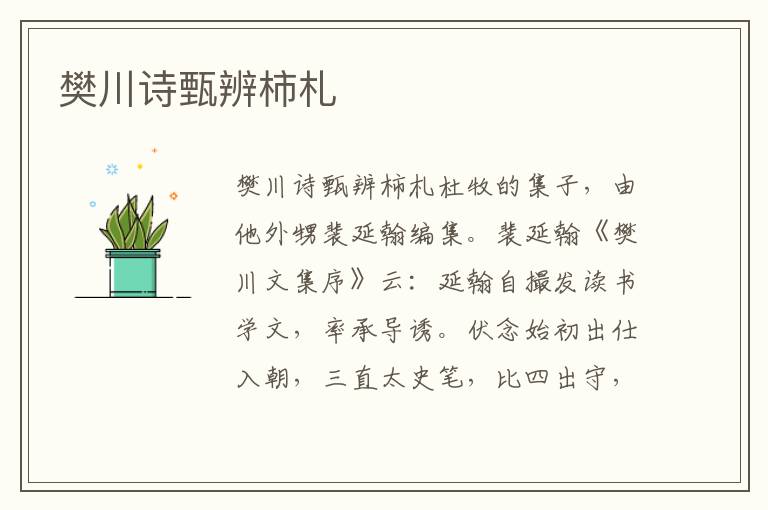
樊川詩(shī)甄辨柿札
杜牧的集子,由他外甥裴延翰編集。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云:
延翰自撮發(fā)讀書(shū)學(xué)文,率承導(dǎo)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yuǎn)數(shù)千里,必獲寫(xiě)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簽?zāi)浚刃7偻猓嗥甙恕5迷?shī)、賦、傳、錄、論、辯、碑、志、序、記、書(shū)、啟、表、制,離為二十編,合為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
既是親屬手編,樊川詩(shī)該是很可靠的;但自宋代以來(lái),仍有人廣事捃采,編成《樊川外集》、《樊川別集》,這固然保存了一部分杜牧詩(shī),然而隨之也就混入了不少他人的作品。清編《全唐詩(shī)》,擷摭圖全,又未加考訂,因而,《全唐詩(shī)》杜牧集中混入了更多的他人作品。中華書(shū)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排印清馮集梧《樊川詩(shī)集注》,據(jù)《全唐詩(shī)》校補(bǔ),增加《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其中大量詩(shī)作和許渾集重出。
為此,筆者參證諸書(shū),摘錄一些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則,因?yàn)橛嘘P(guān)樊川詩(shī)的疑點(diǎn)還很多,有不少問(wèn)題還有待研究探討;二則,本文是隨筆性的,漫無(wú)詮次,因而命之為《樊川詩(shī)甄辨柿札》。
一 《樊川外集》、《樊川別集》及其他
《新唐書(shū)·藝文志》著錄《樊川文集》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同;晁公武《郡齋讀書(shū)志》卷十八始多出外集一卷,陳振孫《直齋書(shū)錄解題》卷十六所載同。陳氏云:“外集皆詩(shī)也,又在天臺(tái)錄得集外詩(shī)一卷,別見(jiàn)詩(shī)集類(lèi)(企按:《直齋書(shū)錄解題》卷十九“詩(shī)集類(lèi)”未收錄樊川集外詩(shī),疑脫漏),未知是否?”然而,早于晁、陳兩氏的鄭樵,已在《通志·藝文略》里著錄《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鄭樵早年周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所見(jiàn)極博。田槩在宋仁宗熙寧六年三月編集的《樊川別集》,他已經(jīng)見(jiàn)到,所以《通志》中能加以著錄。余嘉錫《四庫(kù)提要辨證》卷二十一云:“所謂集外詩(shī),疑即指別集言之。”這個(gè)推測(cè),未必切當(dāng)。田槩編書(shū)后,有《樊川別集序》冠其首,標(biāo)其書(shū)為《樊川別集》。晁、陳兩氏未能見(jiàn)到田槩此書(shū),所以未加著錄,他們斷不會(huì)誤把《樊川別集》當(dāng)作集外詩(shī)。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楊守敬定它為北宋槧本,原藏日本楓山官庫(kù)。楊守敬于東京使館時(shí),“不惜重費(fèi),使書(shū)手就庫(kù)中影摹以出。”(見(jiàn)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楊守敬題跋)這個(gè)刊本被發(fā)現(xiàn),不僅可以證明鄭樵《通志·藝文略》的著錄是正確的,也可以證明晁公武、陳振孫、劉克莊等人,當(dāng)時(shí)都還沒(méi)有見(jiàn)到過(guò)這個(gè)本子(此說(shuō)采自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楊壽昌題跋)。
最令人奇怪的是,劉克莊在《后村詩(shī)話(huà)》中說(shuō):“樊川有續(xù)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shī)。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劉克莊所謂的三卷“續(xù)別集”,其他書(shū)籍均未見(jiàn)著錄。楊守敬認(rèn)為,“則知后村所見(jiàn)續(xù)別集,更為后人所輯。”(見(jiàn)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楊守敬題跋)余嘉錫認(rèn)為:“恐止是南宋末葉書(shū)坊偽造之本耳。”(《四庫(kù)提要辨證》卷二十一)楊、余兩氏之說(shuō)可信。“續(xù)別集”當(dāng)是南宋時(shí)好事者誤將許渾詩(shī)輯成的,書(shū)坊又不加考索,率然刊刻,造成混亂。
二 《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絕大多數(shù)是許渾詩(shī)
《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共補(bǔ)錄杜牧詩(shī)五十六首。
這些詩(shī),《全唐詩(shī)》編者指出與許渾詩(shī)重出者為六首。計(jì):《泊松江》,一作許渾詩(shī),題作《夜泊松江渡寄友人》;《宣城送蕭兵曹》,一作許渾詩(shī);《寄兄弟》,此詩(shī)又見(jiàn)許渾集,題作《寄小弟》;《寄桐江隱者》,一作許渾詩(shī);《送大昱禪師》,一作許渾詩(shī);《題白云樓》,一作許渾詩(shī),題作《漢水傷稼》。
《全唐詩(shī)》問(wèn)世后,馮集梧注釋《樊川詩(shī)集》四卷,附錄《樊川別集》、《樊川外集》未注。他的《樊川詩(shī)注自序》云:“牧之詩(shī)向多有許渾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別集各一卷,茲多未暇論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jiàn)者,非其所欲存也。”他或許認(rèn)為《全唐詩(shī)》杜牧集中大批和許渾集重出的詩(shī),不是杜牧所作,所以他在輯《樊川詩(shī)補(bǔ)遺》時(shí)把它們剔除在外,未加補(bǔ)錄。(有九首不和許渾詩(shī)重出而見(jiàn)于《全唐詩(shī)》的杜牧詩(shī),錄入《樊川詩(shī)補(bǔ)遺》中。)
開(kāi)封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全唐詩(shī)》校訂組,于一九六二年發(fā)表《<全唐詩(shī)>重出失注索引》,指出《全唐詩(shī)》中杜牧集和許渾集重出互見(jiàn)詩(shī)共有五十五首:《樊川詩(shī)集》一首,題為《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jiàn)迎,李趙二秀才同來(lái),因書(shū)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樊川外集》一首,題為《愁》;馮集梧補(bǔ)輯的《樊川詩(shī)補(bǔ)遺》二首,題為《吳宮詞》二首;《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五十一首,除《宣州開(kāi)元寺贈(zèng)惟真上人》、《川守大夫劉公,早歲寓居敦行里肆,有題壁十韻,今之置第,乃獲舊居,洛下大僚,因有唱和,嘆詠不足,輒獻(xiàn)此詩(shī)》、《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jiàn)贈(zèng),凡二十韻,走筆依韻》、《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留題李侍御書(shū)齋》等五首詩(shī)以外,《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中的絕大多數(shù)詩(shī),都和許渾集重出互見(jiàn)。即使開(kāi)封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全唐詩(shī)》整理小組未指出的五首詩(shī)中,也還有四首不是杜牧的作品,詳見(jiàn)下文。
劉克莊“樊川有續(xù)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shī)”這句話(huà),很值得重視。因?yàn)椤斗ㄔ?shī)集》、《樊川別集》和《樊川外集》中僅有二首詩(shī)和許渾詩(shī)重出。“十八九皆許渾詩(shī)”,當(dāng)然不是針對(duì)這些詩(shī)集講的。那么,為什么會(huì)在《全唐詩(shī)》中有大量的杜牧、許渾重出詩(shī)呢?顯然,這是《全唐詩(shī)》編纂者的過(guò)失,他們把劉克莊所見(jiàn)過(guò)的、“十八九皆許渾詩(shī)”的樊川續(xù)別集,混入《全唐詩(shī)》杜牧集中。
《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所收錄之杜牧詩(shī),絕大多數(shù)該是許渾詩(shī),除上述諸點(diǎn)外,還有如下兩點(diǎn)可以補(bǔ)充:
(1) 許渾手書(shū)真跡可證《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中有二十九首詩(shī)為許渾作,絕不會(huì)是杜牧作品。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shū)贊》卷六載:“唐許渾烏絲欄詩(shī)真跡”,手跡前有許渾題記,云:
余丱歲業(yè)詩(shī),長(zhǎng)不知難,雖志有所尚,而才無(wú)可觀。大中三年,守監(jiān)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謁,堅(jiān)乞東歸。明年少閑,端居多暇,因編集新舊五百篇,置于幾案,聊用自適,非求知之志也。時(shí)庚午歲三月十九日,于丁卯澗村舍,手寫(xiě)此本。
岳珂于手跡后,加上按語(yǔ):“右唐郢州刺史許渾所書(shū)烏絲欄詩(shī)一百七十一篇真跡,分上下二卷,織組間錯(cuò),辭格華古,筆妙爛然,見(jiàn)為三絕。”經(jīng)逐一核對(duì),《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中有二十九首詩(shī),見(jiàn)之于許渾真跡,各詩(shī)題名如下:
聞開(kāi)江相國(guó)宋公下世二首出關(guān)過(guò)鮑溶宅有感寄兄弟秋日卜居招書(shū)侶西山草堂貽隱者夜泊松江渡寄友人(《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題作《泊松江》)石池送蘇協(xié)律從事振武懷政禪師院送荔浦蔣明府赴任秋夕有懷秋霽寄遠(yuǎn)經(jīng)古行宮宣州開(kāi)元寺贈(zèng)惟真上人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留題李侍御書(shū)齋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越中聞范秀才自蜀游江湖綠蘿貽遷客宿東橫山瀨陵陽(yáng)送客贈(zèng)桐江隱者(《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題作《寄桐江隱者》)送太昱禪師
(2) 《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所收錄之《題白云樓》,在許渾集中題作《漢水傷稼》(見(jiàn)《全唐詩(shī)》卷五百三十五)并有序云:“此郡雖自夏無(wú)雨,江邊多穡,油然可觀。秋八月,天清日朗,漢水泛濫,人實(shí)為災(zāi),軫念疲羸,因賦四韻。”詩(shī)云:“西北樓開(kāi)四望通,殘霞成綺月懸弓。江村夜?jié)q浮天水,澤國(guó)秋生動(dòng)地風(fēng)。高下綠苗千頃盡,新陳紅粟萬(wàn)箱空。才微分薄憂(yōu)何益,卻欲回心學(xué)釣翁。”序言與詩(shī)意全合,可見(jiàn)這首詩(shī)原為許渾作品,不知何許人隨意刪去序言,改易題目,混入杜牧詩(shī)中去。
三 《聞開(kāi)江相國(guó)宋下世二首》是許渾的感事詩(shī)誤入樊川集
《聞開(kāi)江相國(guó)宋下世二首》,許渾集題作《聞開(kāi)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宋岳珂《寶真齋法書(shū)贊》卷六“許渾烏絲欄詩(shī)真跡”錄此詩(shī),題作《聞開(kāi)江相國(guó)宋公下世二首》。這兩首七言律詩(shī)當(dāng)是許渾作。許渾集中另有一首五言律詩(shī)《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云:“清湘吊屈原,垂淚擷蘋(píng)蘩。謗起乘軒鶴,機(jī)沈在檻猿。乾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冤。寧有唐虞世,心知不為言。”《全唐詩(shī)》于題下注云:“詠宋相申錫也。申錫為王守澄所抅,謫死開(kāi)州,文宗太和五年事。”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三云:“此惟退相可以當(dāng)之。文宗朝,宋申錫謀去宦官,反為宦官所抅,謫死。考本傳有王守澄欲遣騎就靖恭里屠申錫家語(yǔ),知此為申錫作無(wú)疑。”
靖恭里感事詩(shī)和《聞開(kāi)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字句基本相同:“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瑤瑟奠蘋(píng)蘩。誰(shuí)能力制乘時(shí)鶴,自取機(jī)沈在檻猿。位極乾坤三事貴,謗興華夏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敢言。”前人作詩(shī),沿襲詩(shī)意者有之,詩(shī)意偶合者有之,但只是個(gè)別地方偶同。象《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和《聞開(kāi)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第二首這樣,詩(shī)意和詞句基本相同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因此,這兩首詩(shī)決不會(huì)一是許渾作,一是杜牧作。筆者認(rèn)為這兩首詩(shī)是一詩(shī)兩稿。許渾先作《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后又作《聞開(kāi)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第一首。意猶未了,遂改五言律《太和初靖恭里感事》詩(shī)稿成為《聞開(kāi)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后人裒集許渾詩(shī),把原稿、修改稿都收入集中。這種現(xiàn)象,在李白集中有好幾個(gè)例子。
四 辨證《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中的兩首詩(shī)
《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中有一首《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jiàn)贈(zèng),凡二十韻,走筆依韻》,當(dāng)是許渾作,誤入樊川詩(shī)中。
這首詩(shī)首敘梁秀才的身世經(jīng)歷,次敘梁和自己的友情。又云:“渭陽(yáng)連漢曲,京口接漳濱。”原注云:“某自監(jiān)察御史謝病歸家,蒙除潤(rùn)州司馬。”杜牧并沒(méi)有這樣的經(jīng)歷,他在《自撰墓銘》中對(duì)自己一生的仕途出處,敘述得非常清楚準(zhǔn)確:“牧進(jìn)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shū)郎試左武衛(wèi)兵曹參軍,江西團(tuán)練巡官,轉(zhuǎn)監(jiān)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節(jié)度掌書(shū)記,拜真監(jiān)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tuán)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nèi)供奉,遷左補(bǔ)闕、史館修撰,轉(zhuǎn)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zhuǎn)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shū)舍人。”據(jù)此,可知杜牧既未“謝病歸家”,又未被除“潤(rùn)州司馬”,所以,《全唐詩(shī)》、《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以此詩(shī)為杜牧作,均誤。
《唐才子傳》卷七許渾傳云:“少苦學(xué)勞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為潤(rùn)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jiān)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辛文房這一段記載,和《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jiàn)贈(zèng),凡二十韻,走筆依韻》一詩(shī)的原注,有幾個(gè)地方吻合:一,許渾曾任“潤(rùn)州司馬”,二,許渾曾為“監(jiān)察御史”,三,許渾羸弱多病,“以伏枕免”。但是,辛文房以為許渾先為潤(rùn)州司馬,后為監(jiān)察御史,敘述時(shí)序比較含糊。我認(rèn)為這首詩(shī)的原注較為清楚,而許渾又別有《臥病(時(shí)在京都)》、《余謝病東歸王秀才見(jiàn)寄今潘秀才南櫂?lè)畛辍返仍?shī),可為助證。可見(jiàn),《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jiàn)贈(zèng),凡二十韻,走筆依韻》一詩(shī),確是許渾作。
《樊川集遺收詩(shī)補(bǔ)錄》中還有一首《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決非杜牧作。詩(shī)云:“賜第成官舍,傭居起客亭。”詩(shī)下原注:“某六代祖,國(guó)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屬官舍,今于履道坊賃宅居止。”仁和里,履道坊,均是東都洛陽(yáng)的里坊名。杜牧曾拜“真御史”,分司東都,但在他的詩(shī)文中,都未提及洛陽(yáng)仁和里的舊第及寓居過(guò)的履道坊。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上宰相求杭州啟》、《自撰墓銘》則多次提到長(zhǎng)安安仁里舊第,與此了不相涉。
詩(shī)云:“商歌如不顧,歸棹越南靈。”詩(shī)下原注:“某家在朱方,揚(yáng)子江界有南靈、北靈。”朱方,即唐代的潤(rùn)州丹徒縣,《舊唐書(shū)·地理志》:漢縣屬會(huì)稽郡,春秋吳朱方之邑地。”杜牧從未在潤(rùn)州任職過(guò),也沒(méi)有在丹徒安過(guò)家,“某家在朱方”云云,顯系他人的鄉(xiāng)里。
考許渾集中有《下第歸朱方寄劉三復(fù)》一詩(shī),和前云“某家在朱方”語(yǔ)相合。集中又有《南海府罷歸京口經(jīng)大庾嶺贈(zèng)張明府》、《京口閑居寄京洛友人》、《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等詩(shī),許渾家在潤(rùn)州,是無(wú)疑的。許渾又有《江上喜洛中親友繼至》云:“全家南渡遠(yuǎn),舊友北來(lái)頻。罷酒松筠晚,賦詩(shī)楊柳春。誰(shuí)言今夜月,同是洛陽(yáng)人。”《郊園秋日寄洛中友人》云:“嵩陽(yáng)親友如相問(wèn),潘岳閑居欲白頭。”則知許渾在洛陽(yáng)的親友很多,這也和前云“某六代祖,國(guó)初賜宅在仁和里”語(yǔ)相合。由此可見(jiàn),《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當(dāng)為許渾所作。前代編集杜牧詩(shī)的人,只知杜牧“分司東都”,就把這首詩(shī)誤收入樊川集中。
五 《樊川別集》中亦有他人詩(shī)混入
《樊川別集序》云:“予往年于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shī)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企按:指樊川詩(shī)集和外集)所逸者,其《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shī),乃知外集所無(wú),取別句以補(bǔ)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
魏野、盧訥焉能無(wú)誤!
《子規(guī)》,明系李白詩(shī)混入;《蠻中醉》,亦見(jiàn)之張籍集。杜牧行跡未嘗至蜀地、嶺南,寫(xiě)不出《子規(guī)》、《蠻中醉》一類(lèi)的詩(shī)篇來(lái)。
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人們誤認(rèn)為杜牧詩(shī)的《兵部尚書(shū)席上作》,系好事者偽托,未加考訂,誤收入集。詩(shī)云:“華堂今日綺筵開(kāi),誰(shuí)喚分司御史來(lái)?偶發(fā)狂言驚滿(mǎn)座,三重粉面一時(shí)回。”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于此詩(shī)后無(wú)注。《全唐詩(shī)》于詩(shī)后注出本事,然未標(biāo)明出處。馮集梧注本則注明此事出于《古今詩(shī)話(huà)》,誤。這件本事,最早見(jiàn)之于唐孟棨的《本事詩(shī)》:
杜為御史,分務(wù)洛陽(yáng)。時(shí)李司徒罷鎮(zhèn)閑居,聲伎豪華,為當(dāng)時(shí)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jiàn)之。李乃大開(kāi)筵席,當(dāng)時(shí)朝客高流,無(wú)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dá)意,愿與斯會(huì)。李不得已,馳書(shū)。方對(duì)花獨(dú)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lái),時(shí)會(huì)中已飲酒。女奴百余人,皆絕藝殊色,杜獨(dú)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mǎn)三卮,問(wèn)李云:“聞?dòng)凶显普撸胧?”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jiàn)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kāi),誰(shuí)喚分司御史來(lái)?忽發(fā)狂言驚滿(mǎn)座,兩行紅粉一時(shí)回。”意氣閑逸,旁若無(wú)人。
宋以后詩(shī)話(huà)、筆記,多所征引。阮閱《詩(shī)話(huà)總龜》前集卷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huà)》后集卷十五、魏慶之《詩(shī)人玉屑》卷十六、計(jì)有功《唐詩(shī)紀(jì)事》卷五十六、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均載此事。長(zhǎng)期以來(lái),此事此詩(shī),成為文壇美談。
胡仔曾對(duì)此事提出過(guò)疑問(wèn)。他在《苕溪漁隱叢話(huà)》后集卷十五征引《古今詩(shī)話(huà)》后,又引《侍兒小名錄》,然后加上一段自己的看法:“《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于何書(shū)?疑好事者附會(huì)之也。”
這首詩(shī)確如胡仔所疑那樣,是好事者附會(huì)出來(lái)的。杜牧為御史,分務(wù)洛陽(yáng),是在唐文宗開(kāi)成元年。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文宗皇帝改號(hào)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其年(指開(kāi)成二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yáng)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bǔ)闕。”這段自述,和他的《自撰墓銘》的記述,完全符合:“拜真監(jiān)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tuán)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nèi)供奉,遷左補(bǔ)闕。”李司徒是李愿。《舊唐書(shū)·李愿?jìng)鳌吩疲?ldquo;寶應(yīng)(中華書(shū)局一九七五年版《舊唐書(shū)》卷一三三校勘記:寶應(yīng)為代宗年號(hào),李愿卒于穆宗長(zhǎng)慶之后,當(dāng)為寶歷之誤。《合鈔》卷一八四《李愿?jìng)鳌纷鲗殮v)元年六月卒,贈(zèng)司徒。”唐文宗開(kāi)成元年,杜牧分司東都時(shí),李愿早已物故,怎能在洛陽(yáng)邀宴詩(shī)人,并于席間惠贈(zèng)歌伎呢?
又,李愿從未做過(guò)兵部尚書(shū)。考之史傳,李愿承父蔭,召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guó)。后又歷仕左衛(wèi)大將軍、檢校禮部尚書(shū)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jié)度使、徐州刺史、武寧軍節(jié)度使、刑部尚書(shū)、檢校尚書(shū)左仆射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jié)度使、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寧武軍節(jié)度使、左金吾衛(wèi)大將軍、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jié)度使等。
據(jù)上數(shù)證,可知《本事詩(shī)》“杜為御史,分務(wù)洛陽(yáng),時(shí)李司徒罷鎮(zhèn)閑居”,“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kāi)……”云云,殆為好事者所為,不足據(jù)信。
六 贈(zèng)杜詩(shī)訛為樊川詩(shī)
《樊川外集》載《走筆送杜十三歸京》,前人早已指出這不是杜牧作品。
馮集梧于題下注云:“胡震亨云:牧之卒年五十,此云六十,或非牧詩(shī)也。按:杜十三即牧之,此是送杜之詩(shī),內(nèi)兄年六十,作者自謂也。”馮集梧這個(gè)注極確。李商隱集中有《贈(zèng)司勛杜十三員外》詩(shī),杜牧曾任司勛員外郎,其姓氏、行第和官職均相吻合。岑仲勉《唐人行第錄》亦云:“故對(duì)此詩(shī)之較合理解釋?zhuān)?dāng)是送者乃牧內(nèi)兄之為郡守者,后人不求甚解,將此詩(shī)混入樊川集內(nèi)也。”
又,詩(shī)云:“應(yīng)笑內(nèi)兄年六十,郡城閑坐養(yǎng)霜毛。”按杜牧《樊川詩(shī)集》卷四有《寄內(nèi)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云:“歷陽(yáng)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或許寫(xiě)《走筆送杜十三歸京》一詩(shī)的,就是這一位和州崔太守。杜牧前妻為河?xùn)|裴氏,《自撰墓銘》云:“妻河?xùn)|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shí)卒。長(zhǎng)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這位任和州崔太守的內(nèi)兄,當(dāng)是“別生二男”的后妻崔氏的哥哥。
七 杜牧詩(shī)混入許渾集中一例
《樊川詩(shī)集》卷四有《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jiàn)迎,李趙二秀才同來(lái),因書(shū)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此詩(shī)亦見(jiàn)之于許渾集,題作《春雨舟中次和橫江裴使君見(jiàn)迎李趙二秀才同來(lái)因書(shū)四韻兼寄江南》。《全唐詩(shī)》和馮集梧《樊川詩(shī)集注》都未注明兩詩(shī)重出。開(kāi)封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全唐詩(shī)》校訂組于《<全唐詩(shī)>重出失注索引》一文中指明兩詩(shī)互見(jiàn)。
兩詩(shī)題略異,文字亦小有不同。杜牧集“雁初浴”,許渾集作“雁初落”;“吟暗淡”,許渾集作“吹暗淡”;“悵望春陰”,許渾集作“悵望青云”。盡管如此,兩詩(shī)實(shí)為一詩(shī)。
這首詩(shī),當(dāng)是杜牧作,混入許渾集中。
首先,《樊川詩(shī)集》四卷為裴延翰親手編集,他熟知舅父杜牧的行跡交游,這首詩(shī)有明確的人事、地望,裴不會(huì)誤編。其次,這首詩(shī)的前后,有若干首與之相關(guān)的詩(shī)作,如《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和州絕句》、《題橫江館》,可證為同時(shí)之作。再次,這首詩(shī)后來(lái)傳至許渾處,許有酬答的詩(shī)篇,題為《酬杜補(bǔ)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jiàn)寄》,現(xiàn)存于許渾集中。詩(shī)云:“江館維舟為庾公,暖波微漾雨蒙蒙。紅橋迤邐春巖下,朱旆聯(lián)翩曉樹(shù)中。”此情此景,和杜牧的寄詩(shī)切合。后人編集許渾詩(shī)時(shí),以為《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jiàn)迎,李趙二秀才同來(lái),因書(shū)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一詩(shī)為丁卯所作,又感詩(shī)題于義不通,故將題末“許渾先輩”四字刪去,傳鈔時(shí)文字亦有訛誤。
八 《隋苑》非李商隱作
《樊川外集》載杜牧《隋苑》一首,《全唐詩(shī)》云:“一作李商隱詩(shī),題云《定子》。”
這首詩(shī)并不是李商隱寫(xiě)的。詩(shī)云:“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dāng)筵睡臉新。卻笑丘墟隋煬帝,破家亡國(guó)為誰(shuí)人?”
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于詩(shī)題下注云:“一云定子,牛相小青。”這里的牛相,指牛僧孺。他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罷相,出為淮南節(jié)度使,一任六載。(見(jiàn)《舊唐書(shū)·牛僧孺?zhèn)鳌?按太和六年到開(kāi)成二年,李商隱僅二十多歲,忙于習(xí)業(yè)、應(yīng)舉,也曾從太原幕、兗州幕。至開(kāi)成二年,登進(jìn)士第,東歸省親,冬,赴興元幕。史載沒(méi)有李商隱佐牛僧孺幕的材料,《隋苑》,也不可能是李商隱的作品。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huì)箋》卷四云:“《赤壁》,見(jiàn)杜牧集,《定子》,見(jiàn)杜牧外集,……案以上八首,皆非本集,由后人采摭附入者。”
杜牧曾去淮南佐牛僧孺幕,《隋苑》詩(shī)當(dāng)在此時(shí)所作。
九 杜牧《懷吳中馮秀才》誤作張祜詩(shī)
杜牧《樊川外集》有一首題為《懷吳中馮秀才》詩(shī),云:“長(zhǎng)洲苑外草蕭蕭,卻算遊程歲月遙。唯有別時(shí)今不忘,暮煙秋雨過(guò)楓橋。”已被錄入《全唐詩(shī)》卷五百二十四杜牧集中。
這首詩(shī),亦見(jiàn)于《全唐詩(shī)》卷五百十一,云張祜作,題為《楓橋》。詩(shī)中文字,與杜牧《懷吳中馮秀才》詩(shī)大體相同,小有出入:“遊程”,張祜集作“游城”,“秋雨”,張祜集作“疏雨”。
這兩首重出詩(shī),當(dāng)是杜牧作,誤為張祜詩(shī)。在北宋時(sh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這種互見(jiàn)現(xiàn)象。孫覿《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shī)紀(jì)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天下。”(見(jiàn)《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二)王楙《野客叢書(shū)》卷二十三“楓橋”條,還提到尤延之作《楓橋植楓記》,也征引了張繼、張祜詩(shī)為證,可惜尤袤其文今已散佚。范成大撰《吳郡志》,也都征引了張繼、張祜的楓橋詩(shī)。然而,王楙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張祜《楓橋》詩(shī)和杜牧詩(shī)重出的問(wèn)題。他在《野客叢書(shū)》卷二十三“楓橋”條,首先記載杜牧之詩(shī),曰“長(zhǎng)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guò)楓橋”,又云:“近時(shí)孫尚書(shū)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shī)為證,以謂楓橋名著天下者,由二人之詩(shī),而不及牧之。按,牧之與祜正同時(shí)也。”范成大的《吳郡志》,也是既征引張祜的楓橋詩(shī),又征引杜牧的《懷吳中馮秀才》。
筆者根據(jù)以下幾點(diǎn),認(rèn)為這首詩(shī)當(dāng)是杜牧作的:一,北京圖書(shū)館藏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十卷本、明龔半千編《中晚唐詩(shī)紀(jì)》之《張祜集》,均未收錄《楓橋》一詩(shī)。洪邁《萬(wàn)首唐人絕句》卷三十二僅收杜牧《懷吳中馮秀才》詩(shī),而張祜名下未見(jiàn)有《楓橋》詩(shī)。《全唐詩(shī)》卷五百十一,列《楓橋》詩(shī)于張祜集之最后一首,補(bǔ)入的痕跡極為顯明。二,杜牧集之詩(shī)題《懷吳中馮秀才》,與詩(shī)意比較吻合。詩(shī)從憶念著筆,回想與吳中馮秀才離別時(shí)過(guò)楓橋的情況,景與情融,抒寫(xiě)了深厚的友誼和不勝緬懷的情愫。而誤記為張祜的那一首,詩(shī)題與全詩(shī)詩(shī)意無(wú)關(guān)涉。大致是杜牧詩(shī)在傳鈔過(guò)程中,脫漏題目,后人誤以為張祜詩(shī),漫取詩(shī)尾“楓橋”二字為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