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寧夏文學中的苦難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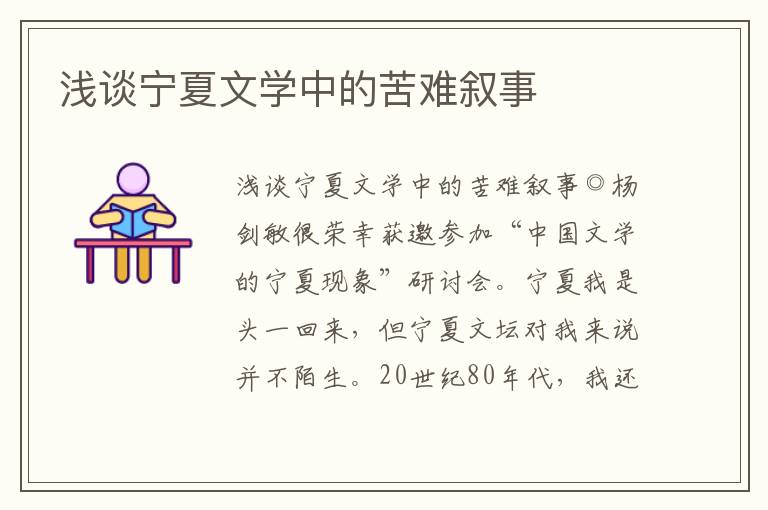
淺談寧夏文學中的苦難敘事
◎楊劍敏
很榮幸獲邀參加“中國文學的寧夏現象”研討會。寧夏我是頭一回來,但寧夏文壇對我來說并不陌生。20世紀80年代,我還是個學生,張賢亮的一系列作品極大地震撼了我的心靈,《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說,稱之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啟蒙讀物,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接下來,寧夏“三棵樹”中的兩棵樹石舒清、陳繼明我都有所接觸,其中石舒清剛登上文壇時,在我擔任編輯的《百花洲》雜志連續發表了四五個中短篇小說,這也是我二十多年的文學編輯生涯中引以為傲的一件事;陳繼明在《朔方》上編發過我的一篇小說。更年輕的作家里,了一容是我魯迅文學院第三期高研班的同學,記得當時他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一位,《百花洲》也發過他的小說。此外,我還編發過季棟梁的小說。所以,我和寧夏文學的淵源還是頗深的。
接到參加研討會的通知后,就我讀過的寧夏作家作品的印象,做了些粗淺的思考。寧夏文學給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苦難敘事:無論是大自然的貧瘠,還是政治運動和宗教文化的沖突,還是個人命運的坎坷,在寧夏作家的筆下寫來,都顯得特別沉重,特別刻骨銘心。這可能和寧夏這片土地近代、現代、當代歷史上的苦難特別深重有關。
張賢亮是寧夏文學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家,他在20世紀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大潮中的杰出表現和突出貢獻,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壇的崇高地位。寧夏后來的名家如陳繼明、石舒清、郭文斌等,在各種場合談到走上創作道路時,都表示最初的興趣來自張賢亮的影響。同時,我認為張賢亮作品中特有的對苦難的描寫,也奠定了寧夏文學的基調。實際上20世紀60至70年代的政治運動造成的苦難是普遍的,但各個地域的作家書寫出來的感覺卻不盡相同,比如史鐵生的作品中較多的是懷舊和感傷;叢維熙也被打成右派、坐過牢,但他的作品里更多的是詩性;至于張承志的作品,幾乎透著一種奇特的浪漫情懷;而張賢亮對苦難的描寫,可以說是深入骨髓的。我查過資料,張賢亮50年代后期就被打成右派,流放到一個荒僻的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從1958年到1976年的十八年間,張賢亮兩次被勞動教養,一次被收容管制,一次受到“群眾專政”,一次被投入土牢監獄。經濟困難時期,他曾因饑餓從勞教農場逃跑三次,到蘭州火車站討過飯,被抓回來后受到餓飯一周的懲罰,曾餓得昏死過去,被送進死人堆后又爬了出來。他的命運就像阿·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里所說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一點也不夸張。在很長時間里,苦難對于他來說是生命的常態,饑餓是他刻骨銘心的記憶。《綠化樹》里面有一段文字,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我有一個從外面帶來的五磅裝的美國‘克林’奶粉罐頭筒。這是我從資產階級家庭繼承下來的一筆財產。我用鐵絲牢牢地在上面繞了一圈,擰成一個手柄,把它改裝成帶把的搪瓷缸,卻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徑雖然只有飯碗那么大,飯瓢外面哩哩啦啦的湯汁雖然犧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狀容器的容量為最大這個物理和幾何原理,總使炊事員看起來給我舀的飯要比給別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飯時都要給添一點。而這‘一點’,就比灑在外面的多得多。”這段文字說的是主人公在打飯時利用視覺上誤覺給自己爭取多一點食物,這種對饑餓的描寫極其震撼人心,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是絕對寫不出來的。這段文字給我留下的印象,幾乎可以和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開頭部分,還有杜拉斯《情人》的開頭部分媲美。
當然,張賢亮的寫作并沒有一味沉浸在苦難的悲愴和沉淪當中,相反,超越苦難的精神氣質,造就了張賢亮開闊博大的胸襟、深沉剛毅的思想、生活和創作的巨大熱情。
張賢亮之后,苦難敘事似乎成了寧夏小說的一種傳統,這也是寧夏文學和其他省份不太一樣的地方。比如我所在的江西,本就少有傷痕和反思方面的作品,這股浪潮也消逝得很快,江西文學(包括影視)很快就進入了田園牧歌式的鄉土文學寫作。
其實張賢亮的寫作并不具有典型的寧夏本土意義。他的苦難敘事可以說是政治性的、命運性的、普遍性的,他只是在寧夏工作,于是成了寧夏文學的一部分。而張賢亮之后的寧夏作家,就不可避免地更多地顯現出本土意味和地域色彩。
在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寧夏作家中,我相對熟悉一點的是石舒清。石舒清是從“西海固”走出來的作家,“西海固”素來有“貧困甲天下”的稱號,在這樣的地方成長和生活,物質的匱乏是可想而知的。在石舒清的作品里,苦難敘事更多地表現為大自然的貧瘠帶來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生發出來的精神生活的豐富。就我的閱讀所及,他似乎很少涉及政治性的話語,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潔凈。《清水里的刀子》這個題目取得特別好,這個題目的意味幾乎能夠完美地闡釋石舒清的敘事美學:靜穆、清潔而又暗藏鋒芒。如果說張賢亮的苦難敘事是外在的、濃烈的,像烈酒一樣辛辣生猛,那么石舒清的苦難敘事則是隱忍的、沉靜的,正如“清水里的刀子”,那種尖銳的感覺只有在靜寂中才能體會。
同樣是從“西海固”走出來的,郭文斌對于貧困的大地有著另一種意味的書寫。他常常喜歡從童年記憶的角度,去挖掘艱難生存背后蘊含著的溫情和詩意。我們都知道,童年記憶往往會有效地過濾掉那些痛苦、煎熬的成分,而保留下美好、溫暖的部分。對于“西海固”這份眾多作家已經充分挖掘和抒寫的文學資源,郭文斌有著較為獨特的思考方式和觀照態度。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人們在艱苦的生活中保持的樂天知命的達觀態度,在饑餓、貧窮,甚至苦難中保持的樂觀、自信和滿足。這也是童年視角特有的敘事魅力和感染力。
至于更年輕一輩的寧夏作家,如我的魯院同學了一容等,對于這片大地上的苦難也有著深沉的書寫。礙于極其有限的閱讀范圍,我無法作更多的議論。以上是我對寧夏文學的一點粗淺認識,不當之處,請各位方家不吝指教。
楊劍敏,現任江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江西省文聯《星火》雜志副主編。文學創作一級。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西省作家協會常務理事。曾任滕王閣文學院特聘作家。出版有長篇小說《南方以南》、中短篇小說集《出使》《刀子的聲音》等。曾獲江西省第一、三、五屆谷雨文學獎,《廣州文藝》第三屆都市小說雙年展獎。短篇小說《突厥》登上2002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