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夏美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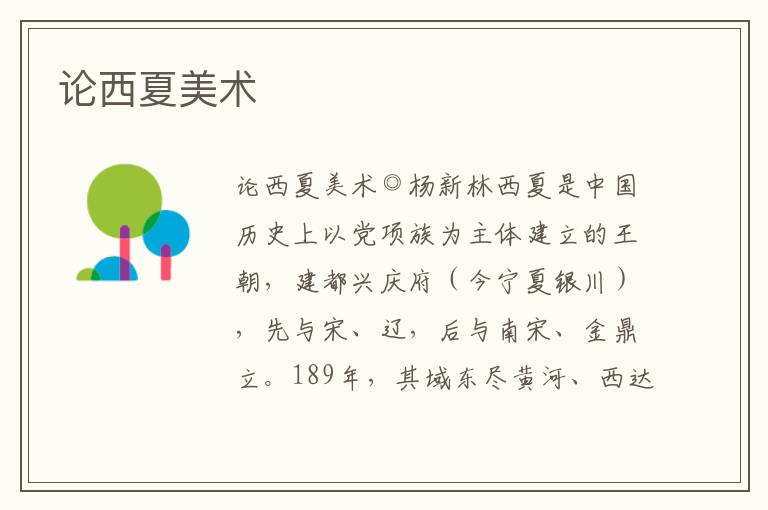
論西夏美術
◎楊新林
西夏是中國歷史上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先與宋、遼,后與南宋、金鼎立。189年,其域東盡黃河、西達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西夏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大興佛塔與佛寺,以承天寺塔最為有名。黨項族在謀求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強調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吸收了漢族、契丹、吐蕃、回鶻等民族的美術特點,取得突破性發展,逐步形成了獨特的西夏美術形式。在藝術方面致力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佛教壁畫,具有“綠壁畫”的特色。尤其是在版畫、雕刻、瓷器等美術方面的繼承與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國美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民族篇章。
一、雅致意趣:西夏壁畫
西夏繪畫根據歷史記載,可以說在西夏建國前就已經開始了。史記“李繼遷被宋軍戰敗逃到地斤澤時,拿出先祖拓跋思恭的畫像,以示黨項……”(陳兆復:《中國少數民族美術史》,福建美術出版社,1995年,第419頁)這是對西夏繪畫最早的記述。目前從西夏繪畫文獻資料來看,多以佛教繪畫為主,有壁畫、木板畫,還有在紙、絹上的繪畫作品,創造出西夏佛教美術光輝燦爛的局面。
(一)環境與淵源:西夏佛教畫的發展現狀
黨項族是羌族的一個分支,在唐朝時,生活在青藏高原,過著游牧生活,從松州(今四川松潘)遷徙到慶州(甘肅慶陽),再遷徙到銀州(今陜北)。此時黨項族開始接受儒家教育。從環境上看,黨項在開元年間,居住在青海東南和甘肅南部,佛教在公元1世紀在涼州刺史部逐漸興盛起來,黨項受到佛教的影響。佛教自兩漢之際從南北朝的發展至隋唐達到鼎盛時期,晚唐開始日漸衰微,到宋朝更是每況愈下,而在與宋、遼、金相鼎立的西夏國卻日漸興盛。西夏佛教藝術的形成,與西夏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有關。在當時,嵬名元昊提出了“以浮圖安疆”的主張,在德明、元昊、諒祚、秉常時代多次用馬匹與宋朝交換“大藏經”。元昊熟讀佛經,命令西夏國刻印書籍,以佛經為主。政府設有“刻字司”,作為官家的出版機構。西夏國在頻繁地向宋朝贖經的同時,為了能使之在廣大黨項和漢族人群中間流傳,又作了大量的翻印并用“番文”進行翻譯工作。這種類似漢字結構又有自己造字特點的出現,對于西夏文化藝術的繁榮和印刷業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上層統治者在這當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他們在本地區大力提倡佛教,吸收中原僧人及佛經學者流入西夏,積極扶持民族佛教文化人的成長,還專門設置刻印佛經的工作崗位,使佛教一度成為國教,滲透到西夏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當中,伴隨佛經的出現,西夏佛教畫也在此歷史條件下必然的產物。
(二)獨特與創新:“綠壁畫”式的藝術風格
西夏的生產關系進一步發展,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老百姓對現實生活產生困惑與懷疑,所以不同程度地對佛教產生依賴心理,以敦厚、善良、喜慶的造型形象,寄托自己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追求,這一點便成為西夏佛像獨創的特點。另外,歷代統治者利用佛教形象來滿足社會需要,通過佛像造型表達老百姓對佛、菩薩及凈土世界的審美認識。
西夏佛教繪畫,以石窟寺院壁畫為最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安西東千佛洞、早峽石窟、天梯山石窟、肅北五個廟、酒泉文殊山、永昌圣容寺等地都有豐富的西夏壁畫遺存。這里我們主要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安西東千佛洞等處的西夏壁畫,來探索西夏壁畫藝術的風格。西夏佛教壁畫可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時期。
西夏早期學習五代、北宋風格,最后形成嚴謹、寫實的藝術風格。采用鐵線描、蘭葉描為主,兼用折蘆描,大量使用石綠打底,使畫面呈現出冷色調“綠壁畫”的獨創風格。題材內容都是一些佛教故事,有千佛、說法圖、西方凈土變和藥師佛之外,還出現供養人、文殊變、普賢變、菩薩與水月觀音及洞窟裝飾圖案等,以《文殊變圖》《普賢變圖》《水月觀音圖》與《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圖》最為有名。而榆林窟第三窟的《文殊變》《普賢變》,卻以山水作為畫面整體的主構件,來反襯人物主體,畫面脈絡明晰,結構縝密。這種在石窟經變畫中將山水背景從畫面屬從陪襯、偏居一角的角色中走出來的藝術表現形式,明顯是學習繼承了兩宋及前代山水畫表現傳統的結果,而這種運用全景式的山水表現形式來營造畫面的磅礴氣勢與空靈氛圍更是前所未有的。西夏中期,經常與宋、遼發生戰爭,洞窟在數量和題材內容上明顯減少,但服飾上受到高昌回鶻的影響,出現“雍容華貴”的體態。如榆林窟第三窟《普賢變圖》,圖中普賢菩薩安詳沉靜,雍容華貴,白象四足蹬蓮花,背景林木蔥郁,氣勢雄渾。榆林窟第三窟《文殊變圖》,本圖雖以人物為主,但背景中山水占有一定比例,具有西夏藝術的風格。其中有一些造型,富含唐宋舞蹈與蒙古舞蹈的特點。如《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碑額兩側的線刻舞伎,舞姿對稱,裸身赤足,執巾佩瓔,于豪放中又顯出嫵媚。還有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壁畫中的《樂舞圖》,左右相對吸腿舞狀,姿態雄健。在藝術表現上主要以線描為主,設色簡約,間以少量青綠做暈染,著重突出了線描的造型作用。這種重墨輕彩的藝術表現手法在敦煌石窟群中極為少見,其簡約清新的藝術風格在中國石窟藝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西夏晚期,由于西藏地區佛教密宗藝術的傳入,使壁畫藝術有了一個新的變化: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優點,創造自己文化特征的民族,同時吸收了宋代筆墨構圖、遼金造型及紋飾、西藏的佛教題材、回鶻的服飾,使西夏佛教藝術進入了成熟時期。在《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內的《農耕圖》《踏碓圖》《釀酒圖》與《鍛鐵圖》中觀察到西夏社會生產和生活內容。在黑水城出土的佛像畫中,有《文殊圖》《普賢圖》《勝三世明王曼荼羅圖》等,畫面濃墨重彩,色調深沉。區別于前代的經變畫,榆林窟第三窟《文殊變》《普賢變》無論是藝術語言的表現還是藝術手法的綜合體現,都繼承了優秀的繪畫語言,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成熟階段,并發展成為一個純粹的藝術表現形式,為石窟壁畫增添了新的藝術風格——“綠壁畫”。
二、因緣而生:西夏版畫
西夏在藏傳佛教藝術向內地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由于從統治者到草根的熱心投入,使版畫隨著佛教在此地區生根、開花、結果,最終為了逐漸適應異地部族的審美需求,打上了地域烙印,成為西夏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譯經圖”是整個西夏版畫發展的最終反映和總結。它的現實主義成分,異地情趣,異地文化的集中體現,成為中國佛教版畫逐漸衰落過程中的回光返照,而且從此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勢頭。另外,西夏佛教版畫是中國佛教版畫中的分支,是緊緊依附于這棵參天大樹而生長的。它的努力是對中國佛教的繼承及地區性的演變,而且西夏在自己藝術的基礎上融漢傳和藏傳佛教藝術于一體,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形式。這一藝術形式對元代內地藏傳佛教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從今天所能見到的大量資料來看,西夏佛教活動無疑是中國佛教發展歷史上的一環,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用組成部分。隨著佛經的出現,作為佛經卷首扉頁的版畫,同樣也應擁有其在中國佛教版畫歷史中的位置。
(一)程式與趣味:西夏版畫形成的淵源
西夏版畫是伴隨著佛經雕版文化發展起來的一種藝術形式,佛經的卷首是以版畫形式出現的插圖。在中原地區佛教版畫的長期演變中形成了特有的裝飾程式和審美趣味。這種具有裝飾性的構圖,線條遒勁流暢,表情自然端莊,形象親切溫雅,體現佛教內涵的故事插圖,無疑受到西夏人們的喜愛。版畫的內容表現是佛教故事,用通俗易懂的畫面形式傳達給人們精神內涵,自然就被西夏佛經所采用。如果沒有佛經“插圖”樣式的版畫出現,也就不可能有西夏的版畫藝術。另外,版畫可以反復印刷,因而可以豐富書籍內容。
關于西夏版畫的起源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現存唐代有紀年的《金剛經卷首畫》來看,其刀法嫻熟,造型嚴謹、布局合理、線條流暢,儼然是一幅成熟的作品。西夏佛教版畫在印度佛教藝術的程式上進行創新,發展形成了一套富有黨項民族特色的形象和線條處理方法,成為佛教版畫形成的重要依據和特定程式。從版畫家到工匠都在尋求更適合于版畫表現的藝術語言,采用特殊的技術手段——雕版印刷工具,借助宗教繪畫造型的表現方法,服務于佛經的審美趣味。早期代表性的版畫作品還有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年)印制的《般若多心經》卷首版畫,這部佛經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夏刻印的漢文佛經。另外,還存在一種生氣勃勃、樸實無華甚至風格粗獷的大眾版畫,如在民間印刷作坊印刷的“為市甚盛”的民間風俗畫、木板年畫、節令畫等。這種通俗易懂的民間藝術,積極滲入到各種文化活動中,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的各個階層,使西夏佛教版畫進入濫觴期。總之,元昊時代開始使用西夏文字和漢文文字譯經,所以漢文佛經版畫與西夏文佛經版畫都經歷過初期的引入過程和后期的完善階段。西夏版畫的歷史也應該從這兩種文字的佛經出現算起,這其中盡管有相當數量的版畫都是贖入佛經中的版畫的翻版,但刻印畢竟還是西夏匠人完成的。早期刻板技術的形成也應視為西夏版畫開拓的功績。
(二)經典與樣式:《譯經圖》是西夏佛教版畫的典范
首先,《譯經圖》所表現的譯經環境展示了西夏民族文化的精神狀態,故而它成為西夏佛教版畫的經典樣式。西夏佛教版畫語言的生成是處在特定環境中的產物。《譯經圖》是一幅數量極少的以表現西夏譯經日常生活的作品。這種佛教活動場面為內容的題材,通過對日常生活的直接描寫,更好地詮釋版畫家對自然的直觀感受,更能集中展示版畫家的創造性思維和技巧功底。其次,《譯經圖》是了解西夏政治、宗教文化活動的重要史料。這幅畫真實地記錄了皇太后、皇帝親臨譯經現場的畫面,體現了皇室對佛教的支持和對譯經事業的關注。主譯人白智光以國師之尊位于畫面中央,處理為高大形象制約全局,猶如佛祖一般,反映了統治階級對佛教的崇敬和對高僧的重視。這幅版畫再現譯經場面的組織結構,主譯人、助譯人分工詳細。這種譯經場面基本上借鑒了漢文譯經場面的組織結構。另外,譯經工作由黨項、漢、藏等民族譯經學者參加,從這個意義上看,西夏文佛經是多民族協作的產物。最后,《譯經圖》的出現是奠定西夏民族版畫語言的基石。在畫面的組織安排上,版畫家再現了譯經場面和譯經工作人員的順序,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的譯經環境。構圖上注重對稱與均衡,體現出秩序上的安排。這幅畫的構圖在今天來看稍有些生硬呆板,但站在西夏特定歷史時期去審視西夏版畫的構圖,發現《譯經圖》在構圖上是經典的樣式。《譯經圖》對形象的塑造上,追求寫真效果。畫面大部分是西夏當時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并且都用西夏文將其名落款,將他們的形象較真實地再現于畫面。注重人物形象的寫真也是西夏版畫的重要特點之一。
三、民族特點: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是指西夏時期西北少數民族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的文化遺產。從目前已有的史料看,寧夏靈武窯是西夏時期重要的燒制窯口,在這里曾經燒制了大量的生活用具、娛樂用具、宗教用具、文房四寶、窯具、工具、建筑材料等瓷器,共2000余件。
(一)資源與需求:靈武窯產生的歷史原因
靈武窯就是西夏時期的一個重要瓷器生產基地,以日用器皿為主,樣式多且富于變化,造型優美,花樣清晰。其中刻釉、剔刻釉是靈武窯瓷器裝飾技法的一大特點。剔刻釉技法能在器物上形成胎釉之間的色差,色彩對比鮮明,有較強的紋飾裝飾的藝術效果。此外,西夏瓷器的釉色與西夏少數民族審美取向有直接的關系,最主要表現在剔刻化妝土技法的廣泛使用。受磁州窯系的影響,靈武窯瓷器多用白色化妝土,此技法的使用真實地反映出當時西夏王朝權貴推崇白色的審美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中原與西夏民族文化的交融。
隨著西夏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技術的提高,西夏中后期瓷器的生產也有了規模性的發展,結合本民族的生活習慣,創造出帶有濃郁民族特色和地區風格的瓷器工藝品。西夏文化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枝奇葩,西夏瓷器是中國少數民族幾千年文化的集中反映,瓷器品種涉及的范圍廣泛,在滿足生活日用之余,不乏高雅的藝術精品。西夏靈武窯瓷器的裝飾紋樣體現了當時西夏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族特點和審美取向等,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產力。西夏瓷器歷經元、明兩代,燒制技術日益精湛,產品更趨完美,影響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具有地域特點和獨特藝術風格的北方少數民族瓷窯系列。
(二)多樣與寓意:瓷器上的裝飾紋樣
西夏瓷器的紋飾與宋代中原北方諸窯瓷器上的紋樣大體相仿,有植物紋、動物紋、人物紋、幾何紋等,構圖飽滿,題材豐富,顏色古樸,造型別致,是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藝術形式,是倫理、吉祥等思想道德和情感意念的載體和傳播情感的媒介。
1.植物紋樣。植物紋在西夏瓷器裝飾中運用最為廣泛,往往裝飾在罐、瓶、盤、缽、壺、盆等器物的口、沿、頸、肩、腹等部位。植物紋樣大都采用象征、諧音等寓意手法,組成具有一定吉祥寓意的裝飾紋樣。
牡丹紋是西夏民族最喜愛的紋樣之一,也是我國各個民族共同喜愛的傳統紋樣之一。它是百花之王,有國色天香的美譽,它色澤鮮艷,花香濃郁,深得人們喜愛,在歷代瓷器裝飾中,不論官窯或民窯,以寓意和諧音來象征吉祥,使用得比較廣泛。牡丹紋按照不同的瓷器形狀的變化而變化,千姿百態。加之剔刻、模印技法的使用,使紋飾胎體和釉色產生強烈的對比,主次分明,疏密得當,給人以明快之感。在造型上,有一枝獨秀的單朵牡丹;也有常見的花朵兩兩相對牡丹,形態自然,花葉隨著牡丹造型的變化自由穿插;也有團花形式的牡丹紋樣,組成的紋樣蘊含吉祥團圓;還有受繪畫風格的影響,云頭形曲線的三朵牡丹,表現清秀靈活自然的形態。構圖方式有適合式、對稱式、均衡式等。碗內壁刻一枝牡丹,花朵盛開,枝葉繁茂,布滿全器,作適合式構圖。又有刻兩枝牡丹,花枝相交,花朵相對的對稱式構圖,瓶上的牡丹枝莖纏繞,花葉紛披,作均衡式構圖。總之,牡丹紋是西夏出土瓷器中最常見的紋飾,牡丹花雍容華貴,富麗堂皇,被視為繁榮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紋樣在西夏瓷器的裝飾中被稱為“富貴之花”。
黨項民族信奉佛教,荷花紋是最為典型的佛教紋樣之一,佛教中喜愛蓮花是因為它出淤泥而不染的含義。蓮花紋飾也是瓷器的重要裝飾之一。蓮花素淡優雅,潔身自好,恰好符合當時文人墨客所追求的愿望,以蓮花喻君子也是因為當時這種強烈的寓意。蓮花紋線條流暢,姿態優美,形象生動,紋路清晰,整體風格端莊秀美,蓮花紋在瓷器上多為纏繞紋,具有吉祥美好的含義和境界。西夏瓷器常有的題材鹿銜蓮花紋和剔刻串枝蓮花水波紋,盛開的蓮花莖蔓相連,婀娜俊俏,似在水中跳躍飄逸。
菊花紋是黨項族瓷器裝飾紋樣之一。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自古以來頗受人們的喜愛。菊花還被看作花群之中的“隱逸者”,被贊“風勁齋逾遠,霜寒色更鮮”。欣賞西夏菊花紋,不同角度,不同時節,不同生長程度,都各有千秋,而瓷器上的菊花紋形式多以纏枝和折枝為主,纏枝花紋的形式感平和自然,裝飾均勻嚴謹;折枝花紋樣具有趣味性,形態生動活潑,幾何形式的菊花紋,簡潔大方,體現了清新、典雅的藝術特色。百菊花紋邊,枝葉動態形式感較強,也是西夏人比較喜愛的紋樣之一。總之,菊花紋被大量廣泛應用在瓷器裝飾中,所涉及的窯包括磁窯堡、回民巷等窯,裝飾技法種類繁多。從此,瓷器菊花紋裝飾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階段。
2.動物紋。西夏瓷器紋樣種類豐富、形式新穎,在器形上刻動物紋,也是西夏瓷器中較多見的裝飾形式。其中鹿、魚、馬、兔等紋樣以其同音的美好寓意,長久以來占據著瓷器裝飾的重要位置。
鹿在西夏傳說中是一種祥瑞之獸,象征吉祥。鹿紋作為“祿”的替代形象常與蝠(福)、壽桃組合成“福祿壽”吉祥圖案出現在瓷器上。西夏瓷器中的鹿紋多是鹿銜牡丹花或是鹿銜蓮花。鹿紋以雄鹿為主要描繪對象,通過夸張、變形等藝術手法處理成為一種動物紋樣。在鹿紋圖案形式的處理上,有單獨紋樣和連續紋樣等多種構成形式,并能隨器物形狀的不同而相應地進行創作組合變化,達到器物與裝飾、實用與美觀的統一。鹿紋的組合形式主要有“對鹿紋”“三鹿紋”和“團鹿紋”等。“對鹿紋”具有均衡穩定感,“三鹿紋”具有節奏韻律感,“團鹿紋”具有吸引視線感。鹿和人類長期共同生存、相互依賴,鹿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在鹿身上寄托了豐富的想象和深厚的感情。磁窯堡瓷器面上所繪鹿紋動態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間漫步,或臥于灌木中驚望,或立于路途上踟躕,線條流暢寫意。回民巷窯瓷器白地黑花罐上描繪的是鹿銜草飛奔的圖畫,簡練生動。總之,鹿紋不僅僅是一個動物裝飾紋樣,它所體現的更多是古西夏先民的人文信仰和思想觀念,這一吉祥美好的紋樣值得我們繼續探索和研究。
魚紋是西夏傳統紋樣之一。魚字因與“余”同音,所以人們就喜歡“年年有魚”,魚紋要有蓮花或蓮藕,還要有魚,即“蓮連有魚”,代表生活富足,每年都有多余的財富及食糧,表達一種美好的愿望。表現魚的形態時,往往脊鰭與腹鰭各一個或兩個,魚紋常飾于盤內,反映器物裝飾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結合的。總之,魚紋,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它伴隨著瓷器工藝的發展而繁盛,進而成為極具民族特色的傳統瓷器。
綜上所述,西夏美術是在中原地區美術發展到相應完善的狀況下出現的,這種完善局面使西夏美術避免了猶如孩童學步那樣的初級階段,初次展示給人們的美術作品就呈現出一定的成熟態勢。但這種局面也帶來了某種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自唐代以后的各個時期對其完善規范的因循守舊。西夏美術是中國佛教美術中的分支,它緊緊依附于這棵參天大樹而生長的。它的努力是對中國佛教的繼承及地區性的演變,后來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洗劫了西夏,使西夏美術從良好的開端逐漸消失了。從這一特點來看,西夏美術也不可逃避地受到沖擊,這些美術作品就被當成一種手工藝技巧由作坊里的師傅傳給一代又一代,他們所極力傳授的也多是設計圖稿的規范定式及呆板過程中的技術問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們的創造力,限制了人們從情感出發對審美的追求,但西夏美術發展中,地域性、民族性因素的積淀使西夏美術愈加豐滿起來。
參考文獻:
[1]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3]段文杰.榆林窟黨項蒙古政權時期的壁畫藝術[J].敦煌研究.1989,4
[4]王靜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畫[J].文物,19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