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蕪了的花園》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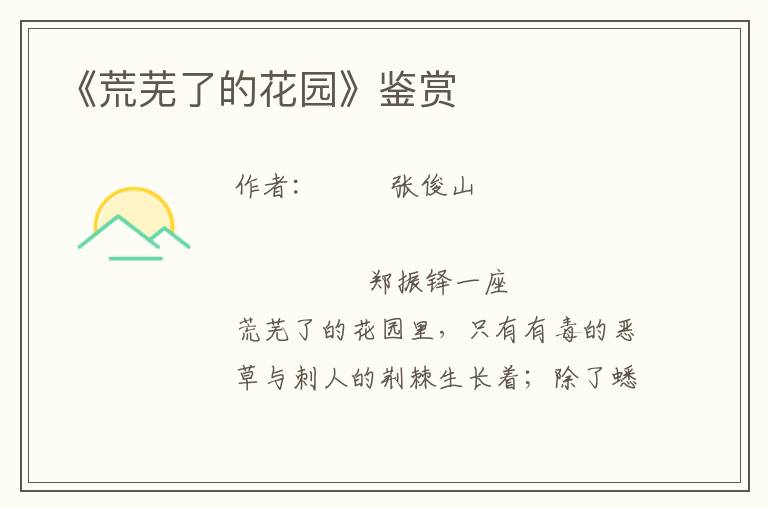
作者: 張俊山
鄭振鐸
一座荒蕪了的花園里,
只有有毒的惡草與刺人的荊棘生長著;
除了蟋蟀在草叢中悲鳴以外,聽不見別的聲響了。
美麗的池從前淙淙地流過石橋的,現在因為沒有人管理,漸漸地干了——干得見底了。
美麗的花木從前燦爛微笑地盛開著的,現在因為沒有人時時灌溉,也漸漸地萎枯盡了。
就是從前天天飛到園里唱夜之歌的夜鶯,也因為它的好朋友玫瑰死了,好久沒有再飛來了。
有一天忽然有好幾個人來到園里。
他們看見這座美麗的花園的凄涼情況,幾乎要痛哭了。
他們坐在快要坍倒的草亭破椅上、談起這座花園的以前的美景,個個人臉上都顯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一個人嘆氣道:“難道我們就任它長此荒蕪了么?”
其余的人都毅然站起身來答道:“不,決不,我們應該大家努力把它整理好。”
于是他們跑到池旁,坐在一塊假山上,細細地討論怎樣改造這座荒蕪的花園的方法。
青蛙帶著滿肚子的喜歡,由池岸下石罅中跳出來聽。
終夜悲鳴的蟋蟀也暫時停止了它的哭聲,由草叢中露出半個頭來,看他們討論。
他們悉心地討論,還用粉筆在石上畫了許多草圖,計劃著將來園中的種種布置。
他們由黎明討論到早餐過后,還沒有商議好一件事。因為他們的意見有許多不能相同。
青蛙暗想道:“為什么他們還不動手做工,只在那里滔滔不息地討論呢?”
后來他們舍了將來的詳細計劃,轉而討論改造這座廢園的入手的方法。
一人說:“應該先把惡草和荊棘斫除掉,然后才能把花木栽下。”
別一人說:“不然。應該先把花木運來,然后再去斫伐惡草和荊棘,因為——”
別一人說:“不然,我表同情于Y君的話。惡草和荊棘如果不先除去,佳木好花是決不能栽種的。因為——”
其余的人說:“不然。你的話錯了。我贊成B君的意見。因為——”
他們各舉了許多理由,互相辯論著,還引了許多例來證明他們的話。由早餐的時候一直辯論到正午,家家炊煙起了,還沒有停止。甚且因為意見不合,他們至于互相謾罵……而且扭打了。
青蛙等得不耐煩了,哭喪著臉,不高興地,一步一步慢騰騰地仍舊走進石罅中去。
蟋蟀的希望也漸漸地減少了;它不愿意看見他們的爭斗;終于把頭縮回草叢中,跑到墻角下,拖長它的音調,重復曼聲悲鳴起來。
荒蕪了的花園還是照舊荒蕪著。
這是一篇用象征手法創作的散文詩。詩篇的隱喻意向直指清談誤國的社會現象,它使人自然地聯想到五四運動到北伐戰爭前夕中國思想界的現狀,其象征意蘊是十分明顯的。
十九世紀法國象征主義詩人讓·莫拉說過:“象征主義的詩賦予觀念的感性的外衣。”這就是說,“象征”不是簡單的、甚至生硬的比附。作為一種藝術手法,它所建構的藝術世界應當是生動而“真實”的。只有這樣,象征才能“賦予觀念以感性的外衣”,因其富有生命的質感而令人信服。
在這篇散文詩中,“荒蕪了的花園”作為一個象征世界是活生生的藝術呈現。這里,“惡草”與“荊刺”叢生,園池干涸,花木枯萎,沒有夜鶯的歌唱,只有蟋蟀在悲鳴。在一片荒涼的氛圍里,那“幾個人”始而痛心疾首地“追慕惋惜”,繼而高談闊論重修花園的方案。他們主張不同,意見分歧,由爭論而“互相漫罵”。就在這些人爭論不休之際,花園的“居民”——青蛙和蟋蟀也都不無期待的走出來旁聽,可是看到他們只談不做,最后都失望地回復到原來的生活狀態。這些描寫,構成了一幅生活氣息濃郁的畫圖,自成一個意趣盎然的藝術天地,它本身是可信的。而就是在這個藝術世界里,景象、人物、動物等形象都一一占據著與現實社會的對應關系,從而都獲得特定的象征意味。這樣,作品的象征建構就具有強烈的諷喻性,它的批判矛頭所指,就是現實社會里那些雖有愛國之心,卻缺乏實干精神的空談家。詩人的“觀念”在這里穿起了“感性的外衣”,自然,貼切,無牽強生硬之感,有耐人尋味之致。這種蘊藉性與形象性的結合,為作品帶來一種情致幽宛的意境,也就是詩意表現了。
當然,這篇作品有一定的寓言色彩,因為故事的諷喻性正是“寓言”的基本特征。但是,它比一般的寓言有更多的細節描寫,詩篇的意境氛圍也是寓言很少具有的。從這種意義說,把它看作象征的散文詩,似乎應恰當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