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莊子·德充符(節選)》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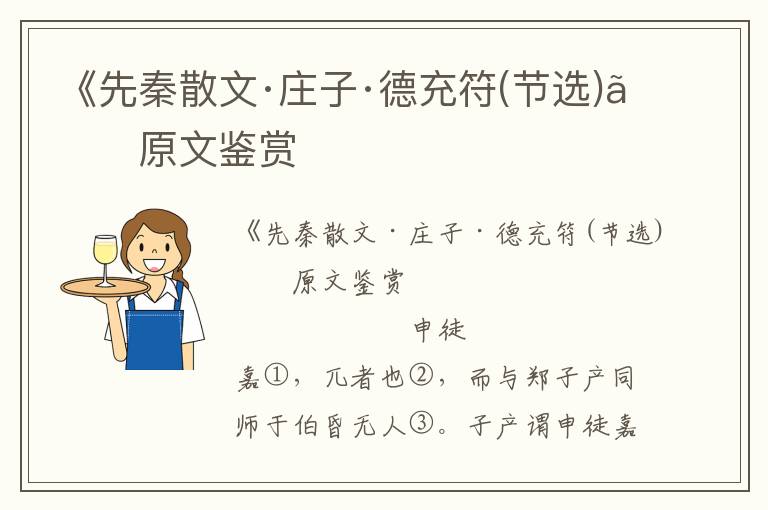
《先秦散文·莊子·德充符(節選)》原文鑒賞
申徒嘉①,兀者也②,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③。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④,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⑤。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⑥?且子見執政而不違⑦,子齊執政乎⑧?”申徒嘉曰:“先生之門⑨,固有執政焉如此哉⑩?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后人者也(11)?聞之曰:‘鑒明則塵垢不止(12),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13),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14),不足以自反邪(15)?”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16),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地彀中(17),中央者,中地也(18);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19),我怫然而怒(20);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21)。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22)?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23),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于形骸之內(24),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25),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26):“子無乃稱(27)!”
【注釋】 ①申徒嘉:復姓申徒,名嘉,鄭國人。 ②兀者:被斷去足的人。 ③鄭子產:鄭國大夫,姓公孫,名僑,字子產;伯昏無人,莊子寓言中虛構的人物,其含義如成玄英《南華真經注疏》所說:“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 ④止:留下,停留。 ⑤合堂:同在一室。 ⑥其:抑或。 ⑦執政:子產時為鄭國執政大臣,故其自稱“執政”;違,回避。 ⑧子:你;齊,同并。 ⑨先生:指伯昏無人;門,門下。 ⑩固:豈,難道。(11)而:乃;說,通悅;后人,瞧不起人;后,作動詞用,把別人放在后面。 (12)鑒:鏡子;明,光亮。這里以鏡子喻人的心靈。(1 4⑥取:求取;大者,指大道。 (14)計:衡量,這里意謂考慮。 (15)反:反省,覺悟。 (16)狀:陳述;過,過錯;亡,指亡足;不當亡,指不應當受刖刑。 (17)羿:傳說為上古時的神射手,每發必中;彀(gou音夠)中,弓箭的射程之內。 (18)中(zhong音眾):射中。 (19)全足:雙足齊全。 (20)怫(bo音勃)然:發怒的樣子;怫,通勃。 (21)廢:消除;反,同返,指返回常態。 (22)洗:清洗,這里指教育、開導。 (23)夫子:老師,指伯昏無人;游,交游。 (24)形骸之內:指精神,這里指德。 (25)索:求;形骸之外,指形體,這里指斷足。 (26)蹴(cu音醋)然:慚愧的樣子;改容改貌,變了臉色。 (27)乃:如此;稱,稱述。
【今譯】 申徒嘉是一個被斷去了足的人,和鄭子產同做伯昏無人的弟子。子產對申徒嘉說:“我先出去,你就暫時先停一下;你先出去,我就暫時先停一下。”到了第二日,申徒嘉又和子產同在一間屋子里同席而坐。子產對申徒嘉說:“我先出去,你就暫時先停一下;你先出去,我就暫時先停一下。現在我要出去,你可以暫時先停—下嗎?還是不能呢?你看見我這位執政大臣而不回避,你把自己看作是和我一樣的執政大臣嗎?”申徒嘉說:“先生的門下,難道有這樣的執政大臣嗎?你炫耀自己的執政之位而看不起別人嗎?我聽說過這樣的話:‘鏡子光亮,塵垢就不會停留在上面;塵垢停留在上面,鏡子就不會光亮。常常和賢人在一起相處就沒有過失。’現在你到這里來求德學道,尊崇先生,還說出這樣的話來,不是太過份了嗎?”
子產說:“你已經受過刖刑了,還要和堯爭善,你考慮一下自己的德性,還不足以使你自我反省嗎?”申徒嘉說:“一個人為自己辯說過錯,認為不應當形殘的人是很多的;已經形殘,不加辯說而認為自己應該形殘的人是很少的。知道事情無可奈何而安于自己的處境,就象安于自己的命運一樣,這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走入了羿的射程之內,那正中間的地方,正是必然被射中之地。然而有時能不被射中,那只是命運的安排罷了。別人因為兩腳齊全而嘲笑我足不全的很多,我聽了十分憤怒;等到了先生門下,就消除了怒氣,恢復了常態。我還不知道這是先生用善教育了我呢。我在先生門下已十九年了,可他從來沒有感覺到我是個斷了腳的人。現在你和我游于‘形骸之內’,以德相交,但你卻在‘形骸之外’,以外貌來嫌惡我,這不是太過份了嗎?”子產覺得很是慚愧,改變了自己的容貌說:“你不要再說了。”
【集評】 清·林云銘《莊子因》:“全段謂德為良貴,勢為形戮,皆不能與,許多曲折,隨筆寫出,無不入妙。”
又:“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雋,味永機新,雪藕冰桃,不許人間朵頤。”
清·宣穎《南華經解》:“又是一個兀者,卻又是一個出色人。”
又:“彀中一喻,妙!妙!言汝之未兀者,或反是當兀者耳,絕妙撲法。”
清·劉鳳苞《南華雪心編》:“第二段,借兀者申徒嘉發出高論,極和平,卻極冷峭。子產從形骸起見,不肖與之周旋,意中未能忘情執政。形諸口吻,乃覺卑無高論。申徒嘉趁勢提出先生之門,推倒他‘執政’二字,以矛攻盾,絕妙文心。措辭含蓄蘊藉,機趣環生。意中以為既有執政之見存,則不宜游于先生之門,既游于先生之門,則宜取大先生,而不得悅子之執政,妙語解頤,消去胸中多少鄙吝,隨將‘鑒明’二語,陪出與賢人久處,微微規諷,味美于回。取大先生,要言不煩。正大處,使人可欽;峭厲處,使人可畏。子產之對,以形之虧而疑其德之未至,借此開下文一段妙論,得未曾有。‘自狀其過’四語,暗駁他‘子既若是’句;‘知不可奈何’二語,暗駁他‘與堯爭善’句。……游于羿之彀中,且在中央之地,顯蹈危機,人亦何能保其不中,然其間亦有幸免者,不能不歸之于命矣。比擬最精,轉令不兀者無處著腳。下文乃明駁他‘子既若是’四語。……前后文法,遙遙相應,筋節極靈。末寫子產改容更貌,逼肖神情。 ‘子無乃稱’四字,作蹇澀不全語,詰屈聱牙,尤傳神之極筆也。”
【總案】 德充符,意謂內心之德充足,外物就會自來相符。充,充足;符,符合。《德充符》的主旨在于論述修德得道,而修德得道的關鍵,則在于泯滅是非,順應自然,忘形忘情。在這則寓言中,莊子主要說明修德得道重在內在精神,而不是外在形骸,只有忘卻形骸,才能最后修德得道。莊子把社會比作獵場,把統治者比作神射手羿,把人民比作羿的射程之內的獵物,深刻地揭示了處在這個社會中,人死于統治者之手是必然的,而不死卻是偶然的事實。這是對當時社會極為深刻有力的批判,是春秋戰國時期其他諸子所難以企及的。
這一節,莊子借申徒嘉與子產的對話,描繪出一幅維妙維肖的畫像,申徒嘉的冷峭、機警,子產的狂妄、自以為是以及最后的無地自容的窘態,都躍然紙上,寫出了他們各自的精神境界,各自的面貌、各自的性格和特點。莊子這種描寫人物的手法,很注意為人物傳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