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人間詞話·少游境凄婉》經典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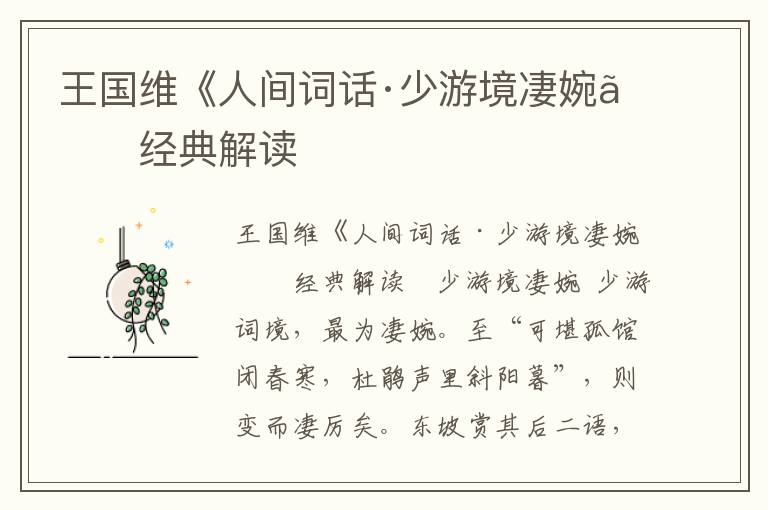
王國維《人間詞話·少游境凄婉》經典解讀
少游境凄婉
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東坡賞其后二語,猶為皮相。
上一節王國維說秦觀的詞:“淡語有味,淺語有致。”
是因為秦觀的詞深厚細致,境界卻又是舒遠的。
一樣是婉約派的代表,閑適里,我喜歡讀晏幾道,晏幾道辭藻華麗,讀起來內心輕松。相比起秦觀,我害怕讀秦觀,在大學中文系學習古典詩詞的時候,就害怕讀秦觀的《踏莎行》。
同是離別的憂傷,晏幾道的傷,會叫你微笑,猶如戀愛之中的女子玩的嬌嗔小把戲,讀過之后,笑笑他的假清高、笑笑他的小心眼,卻還裝得如此正兒八經。
而讀秦觀是不一樣的,在讀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揪著心、攥著書,有種生怕把某一個東西碰碎的緊張。
秦觀、李煜、柳永等都是婉約派的詞人。
讀李煜,他的悲傷是氣勢磅礴蘊含無盡之哲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讀柳永,他的悲傷是情意綿綿包含無盡之男女歡愛,“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讀秦觀的詞,他的悲傷僅僅是凄婉還不夠,傷心流血,似乎這個人從來沒有快樂過,內心總是有無限的愁情,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秦觀的詞表現出來的痛苦已到極致,這樣的痛苦,和李清照的痛苦又是不一樣的,李清照的痛苦,全在生活之愁苦、生活之辛苦、生活之艱苦、知己消逝、落魄凄清……
而秦觀的痛苦,恰恰是在痛里。覺得他的心早已經千瘡百孔,發出這一聲聲凄厲的卻又不能痛快而出的隱忍的哀號。
我們先看王國維指明的秦觀的代表作:
踏莎行
秦觀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上闋寫景,樓臺已被濃霧所迷,那么月亮也漸漸的模糊不清,望斷桃源無處尋。孤館里不能忍受這春寒,杜鵑凄啼殘陽時暮。
其中“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一句是王國維津津樂道的凄厲之語。他的理由是“孤館”“春寒”“杜鵑之聲”“斜陽之暮”都已經營造了悲苦之境了。而“孤館”又是“關閉”,“春寒”才更寒。本已經是斜陽暮下,杜鵑又泣血啼叫。真是悲不勝悲,凄厲得叫人心惶惶。
或許王國維欣賞此句的理由,還因為王國維由于受到叔本華哲學的影響,本身就是一個有著濃重悲觀情緒的人。
下闋以記事為主。驛站有梅花送來,魚雁有托書信。這些被牽掛牽扯起來的愁恨重重疊疊無法細數。郴江悠然自得地繞著郴山,又為了誰流下瀟湘去呢?
“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是蘇軾頗為欣賞的句子。而蘇軾欣賞的句子卻被王國維譏笑,認為蘇軾不過只是懂得皮相。
對蘇軾欣賞此句的態度,我并不贊成王國維的觀點。秦觀的這句,表面上似乎流露出了對自己被貶謫的不滿,似乎這句話又隱含著人生的無常,人生中總是充滿變數。郴江本是愿意繞著郴山流淌的,可是怎么又改變了初衷,為什么要流下瀟湘去呢?這樣的追問,或許自己的內心是知道答案的,但是又似乎明知如此,卻又不愿意面對,表面上看隱含著淺淡的不甘心,但是讀起來又是明白的,期望自己應有面對人生的豁達之感慨。是悲苦,也是一種期許,期許解脫。
不少人認為蘇軾喜歡這句,大概是因為同秦觀一樣,遭受了貶謫之苦。蘇軾的經歷和他樂觀曠達的心境,使他更懂得秦觀最后一句的意味深長的暗示。
【注】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東坡絕愛“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自書于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皮相,從表面看,語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