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揉碎的時(shí)光里撿拾記憶——《朔方·固原專號(hào)》小說淺評(pí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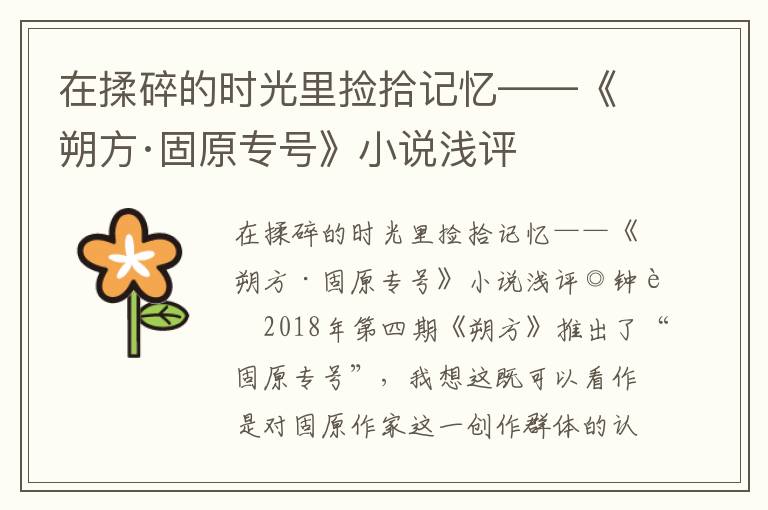
在揉碎的時(shí)光里撿拾記憶——《朔方·固原專號(hào)》小說淺評(píng)
◎鐘莎
2018年第四期《朔方》推出了“固原專號(hào)”,我想這既可以看作是對(duì)固原作家這一創(chuàng)作群體的認(rèn)同,也昭示著固原作為寧夏一個(gè)特定區(qū)域,其創(chuàng)作的日益繁榮。作家們以各自的人生體驗(yàn),構(gòu)筑起自己獨(dú)特的文學(xué)世界,小說、詩(shī)歌、散文和評(píng)論精彩紛呈。我選擇小說作為對(duì)此專號(hào)進(jìn)行評(píng)論的切入點(diǎn),是因?yàn)椋≌f對(duì)人生繁復(fù)性的書寫遠(yuǎn)遠(yuǎn)高于其他文學(xué)樣式,而它所標(biāo)榜的虛構(gòu)性質(zhì),也使作家情感的抒發(fā)更恣肆和真實(shí)。
《朔方·固原專號(hào)》,共收入了六部短篇和一部中篇,這七部小說不約而同地展示出了對(duì)記憶的迷戀。《底色》中的“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在記憶的時(shí)空穿梭,串聯(lián)起母親張桂香辛酸的一生;《周吳小學(xué)的春天》,吳學(xué)謙在生源流失的嘆惋中,將記憶觸及初為校長(zhǎng)時(shí)學(xué)校有過的輝煌;而《王居士》和《獵手》,視線抵達(dá)了歷史的縱深處,對(duì)人性扭曲和價(jià)值失范作了沉痛的反思;《順英的新年》和《飛蛾》,在漠漠茫茫的悲哀與貧窮里,順英和龐四奶奶都選擇向回憶汲取溫暖、填補(bǔ)哀傷;《手》這篇小說,在時(shí)過境遷以后,曾經(jīng)迷戀的雙手,以靈魂叩問的方式,一次次侵?jǐn)_著麻熹之夢(mèng),更顯示了記憶的綿長(zhǎng)與堅(jiān)固。
文學(xué)是對(duì)生命的一種陳述和記錄,生命本身的駁雜性,注定了文學(xué)的多樣風(fēng)采,通過此次小說創(chuàng)作,我們得以瞥見不同的人生形態(tài)和生存面貌。無(wú)論是城市和鄉(xiāng)村的互為對(duì)照,還是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縱深思考,在小說的世界里,人性永遠(yuǎn)是投注的焦點(diǎn),無(wú)處遁形。李繼林《周吳小學(xué)的春天》以一種溫軟的筆調(diào),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里一直以來(lái)被作家喻為尋夢(mèng)之源和靈魂安放之地的鄉(xiāng)土世界,作了一次最深情的禮贊。周吳小學(xué)被描寫成一處桃源般的所在,美得讓人心醉。素樸的人情之美點(diǎn)綴其間:吳校長(zhǎng)為貧困學(xué)生貼補(bǔ)學(xué)費(fèi),對(duì)王老師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對(duì)弟媳和侄女的關(guān)心;蔬菜店女老板不立契約的誠(chéng)信;吳校長(zhǎng)老婆無(wú)私送雞蛋的行為;弟媳對(duì)吳校長(zhǎng)的堅(jiān)守的支持……使其有了如同沈從文筆下《邊城》世界的透明和純凈,成為一幅絕美的鄉(xiāng)村風(fēng)情圖。然而,周吳小學(xué)畢竟受著城鎮(zhèn)教育的襲擊和侵?jǐn)_,時(shí)時(shí)面臨倒閉的危險(xiǎn),生源的流失,辦學(xué)的艱苦,這是烙在吳校長(zhǎng)心中的隱痛,因此,小說又流淌著一種詩(shī)意的哀傷;情感的節(jié)制,又使其區(qū)別于劉醒龍《鳳凰琴》的悲壯和凄愴。作為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最后一位守望者,吳校長(zhǎng)以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維持著教育應(yīng)有的體面:在喊著“上課”“下課”這樣一種充滿儀式的呼聲中,維系著鄉(xiāng)村教學(xué)的最后一絲榮光。六個(gè)學(xué)生,兩位老師,一位做飯師父,一口破鐘,一株老槐,殘破的生存環(huán)境,卻并不凄楚,因?yàn)檫@片鄉(xiāng)村土地上,有吳校長(zhǎng)這樣的人物,他們以對(duì)教育的敬畏孕育出了教師的尊嚴(yán),以此扛住了時(shí)代的重量,彰顯著高貴。
如果說鄉(xiāng)村是詩(shī)意的所在,與之相反,城市給予人的印象仿佛永遠(yuǎn)是冰冷和無(wú)情的,世態(tài)的冷漠制造出了四處蔓延的孤獨(dú)與抑郁。馬曉雁的《飛蛾》以一種蒙太奇的手法,將各色人物和生活場(chǎng)景進(jìn)行自如地轉(zhuǎn)換,類似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用最快利的鏡頭攫來(lái)人生的一個(gè)個(gè)片段,片中人各自的心理和生活軌跡,就構(gòu)成了人生百態(tài)。第一個(gè)片段中,以龐四奶奶的視角,牽連出了因工失去胳膊的長(zhǎng)生,與狗爭(zhēng)食的乞丐,匆忙行走的女教師,從事性工作的胖女子,以及她不爭(zhēng)氣的兒子和日漸疏遠(yuǎn)的女兒;而第二個(gè)片段中,鏡頭切近到長(zhǎng)生,做最精微的觀察,他不幸的經(jīng)歷呈現(xiàn)出來(lái);第三個(gè)片段,又切換成女教師肖芬的視角:在小巷子里生活的人們成為一個(gè)個(gè)剪影,龐四奶奶的女兒橫遭車禍,大搞形式主義的肖芬的學(xué)校,胖女子的工作經(jīng)歷。在這一個(gè)個(gè)片段里,城市人情感的疏離、淡漠,讓整座城市籠罩在一層陰冷恐怖的迷霧中:親情被仇恨和仇殺所代替;挖煤工人的生命被踐踏,無(wú)處申訴。城市彌漫著的近乎獸性的咬嗜和掠奪,是作者對(duì)城市所作的最為精微的呈現(xiàn),也引發(fā)著人們對(duì)城市文明病的思考。
與《周吳小學(xué)的春天》對(duì)鄉(xiāng)村所作的最深情的禮贊不同,《飛蛾》對(duì)城市進(jìn)行了無(wú)情的鞭撻,火霞《順英的新年》,卻選擇以最秉正的姿態(tài),肯定了鬼魅神秘的城市所具有的最大吸附力:在城鄉(xiāng)發(fā)展嚴(yán)重失衡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我們無(wú)法否認(rèn)城市生活的便捷及其所提供的發(fā)展機(jī)遇。于是,順英作為進(jìn)城的鄉(xiāng)下人,帶著一種“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倔強(qiáng),出租房里陰冷的住宿環(huán)境、工作中被城里人防御的難堪,都無(wú)法阻止她想在城市尋求一席之地的決心,頗有一種李進(jìn)祥《屠戶》中馬萬(wàn)山破釜沉舟的氣概。而《屠戶》以兒子的慘死為結(jié)尾,使其成為一則現(xiàn)代城市的寓言。《順英的新年》以溫和的敘述姿態(tài),描述了鄉(xiāng)下人這一群體之間的互相守望:無(wú)論是順英送油餅、油果子給孤寂的大叔大嬸,大叔大嬸回以心疼的感激,還是順英將病室里遺留的物資分發(fā)給同樣貧困的同城姐妹,這種鄉(xiāng)村人之間的默契與體諒,使他們暫時(shí)從城市的殘酷本性中得以抽離,也是文中存留的一處明麗的色彩。在文本的最后,當(dāng)順英的貧窮被其他小孩子進(jìn)行赤裸裸的嘲笑之時(shí),短暫的沉默與怨恨之后,她說出的一句“全家人一個(gè)不落,去洗澡,都給我洗得干干凈凈、利利索索的……”,也可以看作鄉(xiāng)村人骨子里的韌性與倔強(qiáng)的生命力,可以幫助這樣的群體,抵抗城市的壓力,贏得一個(gè)美好的未來(lái)。
與立足對(duì)當(dāng)代的鄉(xiāng)村、城市作一次全方位的展示不同,《王居士》《獵手》和《手》,卻選擇在歷史的縱深處尋找人性異化、人生變形的根源。
《王居士》是李繼林創(chuàng)作的一部頗帶反思性質(zhì)的小說,王紅兵作為一個(gè)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將一切求神拜佛、占卜算卦都看作封建迷信,這樣一個(gè)人,在奇癢難治的病痛的折磨之下,在一切救治宣告失敗之后,終于皈依了佛門,法號(hào)“思賢”,與運(yùn)動(dòng)之前自己的本名不謀而合,使文本彌漫著一種神秘主義的色彩。皈依之后,王紅兵帶著一種反省的姿態(tài)審視過去的所作所為,對(duì)寺廟的破壞、對(duì)神像的不恭,一個(gè)扭曲的時(shí)代旋即浮出水面,同時(shí),也糾引出王紅兵心中的隱痛——對(duì)老東家劉成德的迫害,導(dǎo)致其慘死。東家兒子劉拴狗的出現(xiàn),使其在恐懼的心理動(dòng)機(jī)驅(qū)使下,希望憑借對(duì)劉拴狗的金錢救助,來(lái)進(jìn)行靈魂的救贖。當(dāng)王紅兵突然倒在地上,文本多了一種強(qiáng)烈的因果報(bào)應(yīng)的暗示,當(dāng)年劉成德就是頭直接著地,折斷脖頸而死。《王居士》王紅兵對(duì)自我所作的沉痛反省和救贖,王紅兵看似是一個(gè)迫害者,其實(shí)在無(wú)形中也是時(shí)代的犧牲品。
與《王居士》在歷史的反思中側(cè)重自我救贖不同,王玉璽的《獵手》將筆觸深入到顛亂的時(shí)代,勾畫出價(jià)值失范后普通人的不幸命運(yùn)及與命運(yùn)抗?fàn)幍臍v史。小說從兒童視角出發(fā),以“我”的敘述勾連起了爺爺?shù)牟恍颐\(yùn)。一個(gè)在抗美援朝戰(zhàn)場(chǎng)上戰(zhàn)斗的英雄,面對(duì)時(shí)代的擠壓,只能做最深沉的嘆惋和最深切的隱忍,他的步步退讓希望求得一世平安,由于是以孩子的眼光進(jìn)行囊括,爺爺?shù)谋Р棚@得真實(shí)而有分量。只是爺爺所以為的社會(huì)會(huì)越來(lái)越好的夢(mèng)想最終沒有實(shí)現(xiàn),他的悲哀離世也并未宣告殘酷時(shí)代的結(jié)束。命運(yùn)的沉疴移動(dòng)到二叔的肩上,二叔作為父親心中真正的獵手,在二媽被隊(duì)長(zhǎng)孫兆龍調(diào)戲后的哭聲中,終于仰天長(zhǎng)嘆,走向了最輝煌的戰(zhàn)場(chǎng),射殺了孫兆龍,完成了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獵殺。二叔是一位孤膽英雄,以一己之力對(duì)不合理的時(shí)代進(jìn)行了最激烈的對(duì)抗,即使是以生命作為代價(jià)。
與上述兩篇不同,柯萬(wàn)昌的《手》,歷史背景極其模糊,作者有意淡化時(shí)代的幕布,而將目光集中在對(duì)人性的挖掘。史鐵生說:“文學(xué)和藝術(shù),從來(lái)都是向更深處的尋覓,當(dāng)然是人的心靈深處”,在《病隙碎筆》中,“手”作為一種極美事物的象征,激起了麻熹極強(qiáng)的占有欲,在一種近乎變態(tài)的迷戀中,他將那雙手砍下,埋在窯洞里一處隱秘的坑中,不時(shí)輕輕撫摸。王玉璽抵達(dá)了人性的幽微之處,人對(duì)美麗的占有、人性的貪婪,是無(wú)法擺脫的根性,只是麻熹在十幾年后依然被噩夢(mèng)驚擾,是否也隱含示著作者對(duì)世人所作的一次警醒:占有不屬于你的,原本就是一次心靈的冒險(xiǎn)。
作為七篇中唯一的一部中篇,馬金蓮的《底色》,在時(shí)間的暢想中,三代女性的命運(yùn)躍然紙上。當(dāng)“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思緒在不同的時(shí)空中自由切換,于是,母親張桂香的坎坷命運(yùn),“我”的成長(zhǎng)隱痛,外奶奶的沉默離世,所牽連出的人和事奏響了一首生命的哀歌。張愛玲說:“長(zhǎng)的是苦難,短的是人生”,也許是對(duì)這篇小說所表達(dá)內(nèi)容的最準(zhǔn)確寫照。這是一篇有關(guān)回憶的小說,即使沒有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纖細(xì)與宏大,但它終究表達(dá)出了作者對(duì)于時(shí)間的感受。母親和小姨娘因?yàn)橥粋€(gè)男人,分道揚(yáng)鑣,互相仇恨,但是在各自的不幸后,又言歸于好,放下所有的怨恨;“我”成長(zhǎng)的艱辛,承受著母親嫁接在我身上的對(duì)父親的仇恨,最終在“我”成為母親后,達(dá)到了對(duì)上一代人的諒解;“我”潛藏在心的對(duì)完整家庭的祈愿,也最終隨著父親馬忠長(zhǎng)的逝世而煙消云散,所以時(shí)間才是小說的主人公。它將一切雄偉堅(jiān)硬的東西消解、風(fēng)化,淹沒了一切的仇恨與不堪。《底色》揭示出了生存的某些本相,在親情的面紗下,我們也可一窺其中的嫉妒、計(jì)較和瑣細(xì)。馬金蓮有著驚人的透視生命和生存本質(zhì)的能力,在綿延的回憶里,也揭示了女性生存的不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
以上七篇小說,鄉(xiāng)村與城市作為兩個(gè)不同的眺望窗口,當(dāng)下與歷史成為書寫的兩層解剖面,為我們展現(xiàn)出了固原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無(wú)限豐富性與可能性。文學(xué)作為一種靈魂的救贖圣地,也是欲望年代的守護(hù)神,作家們的書寫,熔鑄著他們各自對(duì)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形成于文,成為一個(gè)個(gè)跳動(dòng)的音符,在疲憊沮喪的光陰里,為讀者帶來(lái)一次次靈魂的放空與洗浴。借用馬金蓮《底色》的結(jié)尾作為此次評(píng)論的結(jié)束:“深藍(lán)的底色上,是無(wú)邊無(wú)際的遼闊”,生命是遼闊的,它的底色是什么,作家們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對(duì)底色的不同理解,卻可以呈現(xiàn)生命最駁雜的狀態(tài)。那些涂抹于底布上的色彩,就是人生的每一個(gè)側(cè)面,讓我們做一次記憶的回顧,在揉碎的時(shí)光中,拼湊出屬于你我不同的記憶,作一次生命最為真切的禮贊。
鐘莎,寧夏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專業(yè)2017級(jí)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