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志清《折斷的翅膀》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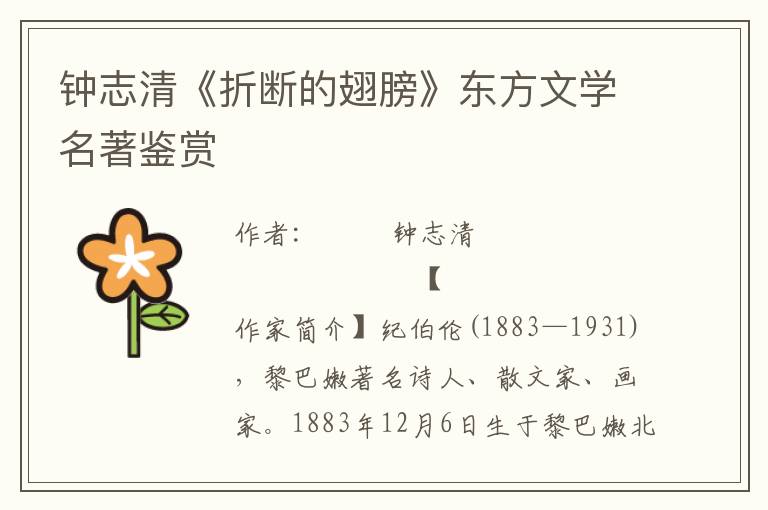
作者: 鐘志清
【作家簡介】紀伯倫(1883—1931),黎巴嫩著名詩人、散文家、畫家。1883年12月6日生于黎巴嫩北部山鄉卜舍里一農民家庭,幼時家境貧寒,父親嗜酒貪杯。12歲時隨母到美波士頓僑居,15歲時返回巴黎,進入貝魯特希克瑪睿智學院,學習阿拉伯文、法文和繪畫。1902年創辦《真理》雜志,抨擊時弊,揭露封建禮教和陳規陋習。1908年發表小說《叛逆的靈魂》觸怒當局,被驅逐出境,再度赴美。后去法國巴黎學習繪畫和雕塑,曾蒙藝術大師羅丹獎掖。學習期間,他不僅飽覽法國的藝術瑰寶,還游覽過羅馬、布魯塞爾、倫敦等名城,遍訪西歐各國的歷史文化名勝。1911年,紀伯倫學成返美,先居波士頓,后移居紐約,與一些旅美阿拉伯作家組織和領導了“筆會”,從事文學藝術創作活動,1931年4月10日病逝。
紀伯倫很早即開始創作生涯。前期以寫小說為主,幾乎都用阿拉伯文寫成,作有短篇小說集《草原新娘》(1905)、《叛逆的靈魂》(1908),中篇小說《折斷的翅膀》(1911)。定居美國后,他逐漸轉向寫散文和散文詩。他用阿拉伯語創作了散文詩集《淚與笑》(1913)、《暴風雨》(1920)、《行列圣歌》(1918)、《珍趣篇》(1923)等,用英語創作了散文集《瘋人》(1918)、散文詩集《先驅者》(1920)、《先知》(1923)、《沙與沫》(1926)、《人之子耶穌》(1928)、《先知園》(1931)以及詩劇《大地諸神》(1931)等。其中《折斷的翅膀》是他最著名最富感傷情調的中篇小說,《先知》是他全部創作中的代表作。
紀伯倫是阿拉伯近代小說和散文詩的主要奠基者,阿拉伯近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重要文學流派“敘美派”的代表之一。他既受到了阿拉伯傳統文化的熏陶,又受到現代西方文化的影響,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他的作品多以“愛”和“美”為主題,把抒情、想象、象征、哲理有機地融在一起。在哲學上,他受尼采影響較大,頑強地表現自我,張揚個性,在阿拉伯近代文學史上具有獨創意義。
《折斷的翅膀》,郭黎譯,見《紀伯倫作品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內容提要】當愛情用它神奇的光芒照亮我的雙眼,用它火熱的手指第一次輕撫我的心扉時,我才18歲。那是陽春4月的一天,身在貝魯特城的我前去拜訪父親的摯友法里斯·克拉瑪,與克拉瑪的獨生女兒薩勒瑪相識。薩勒瑪是一位十分美麗的女性,一見到她,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動。從那兒以后,我常去法里斯·克拉瑪家,與薩勒瑪見面。我和她坐在花園里,我端詳著她的姿容,欣賞她的才華,領略她淡淡的憂愁。我感到冥冥之中有許多無形的手在把我拉到她的身邊。
薩勒瑪的美不在于她形體的完美,而在于她那高尚的精神猶如一簇白熾的火苗,在大地與無垠的天空間飄動、燃燒。她好深思、寡言談。伴隨著她的稟性和氣質的,是深切而劇烈的憂愁。憂愁是她佩帶的一條精神綬帶,給她楚楚動人的體態增添了幾分凝重和異彩。這憂愁織就了一條使我和薩勒瑪精神相通的紐帶,使我們相知、相戀。
城中大主教保羅、加利卜垂涎于克拉瑪的家產,故選薩勒瑪作為侄子曼蘇爾貝克的配偶,因為薩勒瑪是克拉瑪的唯一繼承人,她的萬貫家財能保障曼蘇爾貝克的前程,她廣泛的社會關系將幫他在達官顯貴中間贏得高人一等的地位。當大主教向薩勒瑪的父親提議聯姻時,老人的回答只能是深沉的沉默和兩行老淚,老人被迫屈從大主教的意志,答應了他的請求。就在我們曾經傾吐愛意的那一座花園里,哀怨、絕望的薩勒瑪痛苦地把消息告訴我。我們木然地坐在那里,像被地震埋進土里的一對大理石柱。當我們分手時,我握住薩勒瑪的手,把它放在我的唇邊,為自己祈福。她靠近我,在我頭發的分縫處吻了一下,然后,往后退去,身子倒在一張椅子上。閉上眼睛,緩緩地低聲說;“主啊,憐憫吧,讓所有被折斷的翅膀變得堅強吧。”
我離開了薩勒瑪。世上的一切,生活的全部意義,心靈的所有奧秘,都變得丑陋、可怕、嚇人。我像一只被獵人擊中的鳥兒,墜落在柵欄中間,心口還插著箭。我的理智在可怕的清醒和擾人的睡意之間掙扎,我的靈魂只是重復著薩勒瑪的話:“主啊,憐憫吧,讓所有被折斷的翅膀變得堅強吧!”
薩勒瑪和主教侄兒結了婚。春去秋來,我對薩勒瑪的愛,漸漸地從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對一個窈窕淑女的懷戀,變成一種孤兒對他長眠在九泉之下的母親英靈的無聲崇拜。相思的呻吟,變成了深情的祈禱。我的靈魂在靜穆之中祈求上蒼讓薩勒瑪幸福,讓她的丈夫愉快,讓她的父親安康。但是,我的同情、我的祝愿和我的祈禱卻沒有用。曼蘇爾貝克很像他的叔父。大主教以他的紫色的袍服為遮掩,達到他的目的;以懸掛在胸前的金十字架為掩護,滿足他的貪欲。而他的侄兒,則是公開地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大主教清晨去教堂,白天的其余時間,用來從孤兒寡婦和黎民百姓身上榨取血汗;而曼蘇爾貝克,則終日在陰暗的、骯臟的小巷里尋花問柳。他剛剛把薩勒瑪娶到手,攫取了她的巨額財產,便對岳父棄之不理,盼他壽終正寢,好把他其余的財產一并吞噬。孤獨中的法里斯·克拉瑪患病去世。曼蘇爾貝克霸占了他的財產。而他的女兒,卻仍然是苦難的俘虜。在她的眼里,生活是一出由恐怖擔任主演的大悲劇。
在貝魯特城的園林和山嶺之間,有一座年代久遠的神殿,小小的神殿內,只有一片令人心往神馳的深沉靜寂和一種神幻莫測的肅穆氣氛,默默地泄露著神靈的隱秘,述說著時代的滄桑變遷。在這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我和薩勒瑪每月相會一次。我們坐在門前,背抵著墻,反復吟味往昔的回聲,探究今日的處境,擔心未來的歷程。我們向對方敞開心扉,訴說苦悶、焦灼、不安和惆悵;我們互勸對方忍耐,充滿希望地羅列種種令人欣喜的幻景和甜蜜的夢想;我們相互擁抱,兩心繾綣,情投意合;我們探討都讀過的書籍,評價其優劣以及書中包含的幻景和社會原理。那神圣的幾小時使人名副其實,使生活成為永恒之謎。但不幸的是,大主教窺探到薩勒瑪與我幽會這一舉動,便派耳目盯梢。薩勒瑪怕我受連累,忍痛斬斷情思,不再與我交往。
薩勒瑪婚后5年,一直未曾生育。她一直在苦苦地祈禱,懇求上蒼賜給她一個孩子,用孩子的小手拭干淚水,用孩子的目光驅散心頭死亡的陰影。她的真誠感動了蒼穹,薩勒瑪懷了孕,但孩子生下后立即死去。薩勒瑪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她在極度的悲痛中死去。而他的丈夫卻沒流一滴眼淚。
我夾在送殯者的行列中行走,人們不認識我,也不了解我此時的心情。薩勒瑪丈夫臉上并無悲傷的表情。人們議論說,明天,他的大主教叔叔會替他另娶一個更有錢、更健壯的妻子。
送葬的人們走后,我再也忍耐不住,撲倒在薩勒瑪的墳上,為她哭泣,為她哀傷。
【作品鑒賞】《折斷的翅膀》堪稱紀伯倫最出色的中篇小說,小說取材于作者的初戀經歷。青年時代的紀伯倫曾與故鄉的一位富家女相愛,常相會在山川叢林之間,互訴衷腸。然而由于雙方貧富懸殊,難免遭到強大的社會習俗和傳統勢力的干預,他的初戀失敗了。他深切地體會到社會的不平等,開始把個人的遭遇與社會的不幸聯系起來。《折斷的翅膀》以“我”與薩勒瑪的愛情故事為描寫中心,他們本是一對熱戀中的情人,但是由于城中大主教覬覦薩勒瑪家中的萬貫資財,想讓她嫁給自己的侄子,于是親自出馬干預這樁婚姻,女主人公被迫另嫁他人,在痛苦與不幸的生活中過早地結束了生命。
依照結構主義理論家格雷馬斯的觀點,我們可把該作品看作一個“離合型”的結構模式。主人公“我”是人物關系中的主角,薩勒瑪是主人公的戀人,是人物關系中的對象。大主教是這樁婚姻的直接破壞者,居對頭之位;薩勒瑪之父雖從內心深處支持女兒與“我”的自由戀愛,但卻屈從于主教的意志,不得已把女兒嫁給她不愛的人。各種角色模式確定以后即可深入分析潛在的深層蘊涵。因為角色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所代表的是人物的特定關系,它既可指人,也可指非人類的因素如歷史、世界、物質力量等。這樣一來,大主教和薩勒瑪之父則在本質上有著趨同性。主教是宗教勢力的化身,薩勒瑪的父親是父權制的象征。在東方,特別是中東地區,封建勢力極為嚴重,而封建社會的最大支柱就是宗教制度,作為宗教制度化身的大主教的意志可以支配一切。人們必須無償地屈從于他的意旨。薩勒瑪,一位脈脈含愁的普普通通的東方女性無力與之抗爭,無法贏得自己心馳神往的愛情,只能聽任命運的擺布,犧牲了愛情與幸福。她的悲劇在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內頗具典型性。本世紀初,黎巴嫩的青年剛剛覺醒,他們熱烈地追求愛情與理想,但卻不具有為之抗爭的勇氣和力量。小說的主人公被動地接受封建制、父權制強加給他們的命運。一雙追求理想與愛情的翅膀被折斷了,恰似籠中的囚鳥,只能一味地悲傷與哀嘆,他們的人生悲劇實際上就是一幕時代悲劇。
《折斷的翅膀》典型地體現了紀伯倫風格:風格柔婉,情節清淡,人物性格單一,浪漫而感傷。小說不以敘述故事為重要目的,而以宣泄情感為主旨。整部作品彌漫著深深的感傷色彩,堪稱詩化的小說。
小說的動人之處不僅僅在于愛情故事本身,紀伯倫在作品中對人生、愛情、理想、自由、物質與精神、靈與肉、愛與美、傳統與現代文明、生與死等主題進行了多方探討,發表獨特的見解。如文中所述:“薩勒瑪姣好的面容并不符合人們制定的審美標準,但是,她的美奇異得像夢、像幻景,像圣潔的思想,它無與倫比,不可名狀,不能用畫家的畫筆去玷污,也不能通過雕塑家的大理石來體現。薩勒瑪的美不在于她的金發,而在于她頭上套著圣潔的光環;不在于她那雙大眼睛,而在于眼睛里閃爍著的光芒;不在于那玫瑰色的嘴唇,而在于唇間流出的蜜汁般的話語;不在于她那象牙般的脖子,而在于脖子微微前傾的樣子。薩勒瑪的美不在于她形體的完美,而在于她那高尚的精神猶如一簇白熾的火苗,在大地與無垠的太空間飄動、燃燒。薩勒瑪的美是一種詩的意境,我們能從典雅的詩篇、不朽的繪畫和樂曲中捕捉到它的影子。作家所崇尚的美是以“美在精神”為標志的,他筆下的女主人公盡管軟弱、柔順,但卻有思想,有卓見。她可就人類社會中婦女的地位問題發表見解,可窺見現代婚姻關系中的重重弊端,感受到女性徘徊在愛與愁、憐憫與獻身、坐在王座上的阿什塔露特與站在十字架前的圣母瑪利亞中間產生的難以名狀的心情。正如作家所說:“昨天,她們像瞎子一樣在大白天行走;今天,她是明眼人,卻在黑夜中邁步。”一針見血,指出婦女在傳統與現代文明間猶疑不定、舉步維艱的二難境界。而且,作家從討論女性問題上升到對整個國家命運的思考,把弱女子看成是“受凌辱的民族的象征”,把那個苦苦追求愛情、身體卻被牢牢禁錮住的女子,視為“受盡統治者和祭司們折磨的民族”,使愛情主題升華到對民族命運的探索。但是,這種探索并非空洞的抽象說教,而是用詩的語言述出,整部作品呈現出詩的意境美與音韻美。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折斷的翅膀》中,紀伯倫把自己的人生哲學作了一番詩意化的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