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裴啟《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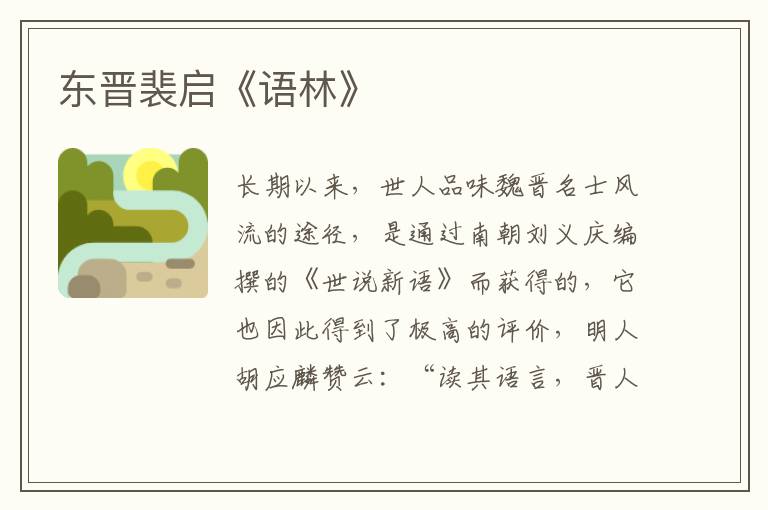
長期以來,世人品味魏晉名士風流的途徑,是通過南朝劉義慶編撰的《世說新語》而獲得的,它也因此得到了極高的評價,明人胡應麟贊云:“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少室山房筆叢》)魯迅稱之為“名士底教科書”(《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事實上,早于《世說新語》成書六七十年的東晉裴啟編撰的《語林》,才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名士教科書,它在記錄魏晉名士風度方面起到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作用,對《世說新語》的成書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由于《語林》在隋唐之際便亡佚了,以致人們忽略了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一、 裴啟與《語林》的盛行
《語林》的作者——裴啟,在史書中沒有關于他的傳記,僅有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以及南朝宋代檀道鸞《續晉陽秋》提供了零星的記載,我們也只是對其生平略知一二。《世說新語·文學》第90則云: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
在《世說新語》中只是說《語林》的作者是“裴郎”,沒有明確指出是裴啟。《世說新語》問世后大約六十余年,劉孝標(462—521)為《世說新語》作注,引裴啟《語林》中的故事,表明了《語林》的作者是裴啟。《世說新語·任誕》第43則劉孝標注云:
裴啟《語林》曰:“張湛好于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劉孝標又引檀道鸞《續晉陽秋》指出《語林》的作者是裴啟。《世說新語·輕詆》第24則劉孝標注云: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
通過以上材料我們可以看出,《語林》是一部描寫魏晉名士言談舉止、嘉言懿行的志人小說,此書在東晉時曾大為流行,名重一時。
關于《語林》的作者似乎還存在一些疑問,劉孝標也沒有完全確定,《世說新語·文學》第90則劉孝標注云:
《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啟作《語林》,榮儻別名啟乎?
《裴氏家傳》認為裴榮撰寫了《語林》,從其性格來說,“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似乎也適合撰寫《語林》,這里的裴榮與裴啟是否為一人,不能確定。兩人的共同之處,除了姓氏以外,籍貫也是相同的,都是“河東人”,劉孝標說:“榮儻別名啟乎?”他姑且提出了疑問。不過,后世文獻(《隋書·經籍志》《說郛》《玉函山房輯佚書》《古小說鉤沉》等)都是把裴啟作為《語林》的作者。
關于裴啟的社會身份,《隋書·經籍志》云:“《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亡。”《隋書》說他是一名“處士”,何謂“處士”?顏師古《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一》曰:“處士,謂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李賢注《后漢書·劉寬傳》曰:“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處士是有一定才華,但是未仕或不仕的人。裴啟是一名處士,這也是史書沒有裴啟傳記的原因之一。
簡言之,《語林》是東晉隆和年間(362—363)處士裴啟撰寫的一部描寫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說,曾一度很受歡迎,并且比劉義慶(403—444)的《世說新語》早六七十年,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名士教科書。
二、 《語林》與魏晉風度
何謂名士,各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解讀。“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后漢書·方術傳論》)。魏晉時期的名士沿襲了東漢名士的特點,并發揚光大。魏晉之際,名士特立獨行、清峻灑脫,表現出的是一種與眾不同、舉止不凡的風度,他們言詞高妙、曠達不羈、精神超俗、不拘小節、鄙視世俗,為后世所景仰,因此被后世稱為魏晉風度。最早有意識地把這種魏晉風度記錄下來的,不是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而是東晉裴啟的《語林》。
魏晉名士喜愛飲酒,他們也并不是單純飲酒,而是將飲酒與人生體驗聯系起來,并進一步發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感慨。例如《語林》云:
王大嘆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酒自引人入勝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
王仲祖酒酣起舞,劉真長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北堂書鈔》卷一百七)
劉伶,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酲,復飲五斗,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莫可聽。”(《藝文類聚》卷七十二)
一些名士飲酒時不注意禮節,只是一味追求一時的快樂或麻醉,劉伶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典型。當然,名士們熱衷于飲酒,甚至于沉湎,并不完全是為了喜好,有時也是為了逃避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而借酒澆愁,表面上他們放縱、灑脫,內心卻又常常十分苦悶。宋人評價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于醉,可以粗遠事故。”(葉夢德《石林詩話》卷下)飲酒是一種放縱,也是一種解脫,他們通過酒來麻醉自己,以逃避這個無力改變的社會現實。
名士的行為方式也往往異乎尋常,例如《語林》云:
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世說新語·傷逝》第3則劉孝標注)
再如《語林》云: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樂其母。(《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
“作驢鳴”,對于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而言,是有所顧忌的,但是魏晉名士并不受此拘束,表現了他們的標新立異與特立獨行。
魏晉名士注重瀟灑的儀表、優雅的氣質,社會上也十分傾慕。《語林》云: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丑,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世說新語·仇隙》第7則劉孝標注)
王右軍目杜弘冶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九)
有的名士注重語言的表達藝術,有時令人忍俊不忍,有時使人思緒萬千,例如《語林》云: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虱,夷然不動。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復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顧擇虱不輟,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量地。”(《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顧和在丞相府門前抓虱子,安然自若,周顗指著顧和的胸脯問道:這里面裝著些什么?顧和依然捉虱不輟,從容不迫地答道:這里面是最難捉摸的地方。這一問一答,似有所指,又耐人尋味,令人回味無窮。魏晉名士沒有矯揉造作和嘩眾取寵,卻表現了他們的恬淡、從容與幽默。
通過《語林》的佚文,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名士的風度,使我們似乎又回到了魏晉時代。《語林》本來可以與《世說新語》相媲美,但是由于它后來亡佚了,淡出人們的視野,因此,魏晉風度確實是有賴于《世說新語》而得以傳承。
三、 謝安與《語林》
東晉裴啟在撰寫《語林》時,描寫了許多當時名士們的嘉行軼事。記載當時的人或事,有可能得到當事人的褒獎,也有可能開罪于當事人,《語林》在流行時,其內容得罪了大名士謝安,遭到了致命一擊。《世說新語·輕詆》第24則云: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其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于此《語林》遂廢。
《世說新語·輕詆》第24則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云:
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于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
《語林》中記載了一些謝安的言語,當事人謝安予以了否認,他之所以否定《語林》,一般認為是“記謝安語不實,為安所詆,書遂廢”(《中國小說史略》)。事實上,《語林》關于謝安的記載并沒有不實之處,謝安否定《語林》是因為裴啟贊揚了與謝安反目成仇的王珣。不過,畢竟謝安是大名士,講究自己的身份,他沒有用簡單粗暴的手段壓制《語林》,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這顯然指《語林》記載的內容不實,而這在那個時代是不受社會認可的。因此,其負面效應很快顯示出來,《語林》受到社會的鄙視。對于這件事的真相當時人無從查證,但從社會影響力來看,人們更傾向相信謝安,而不是裴啟。《語林》很快由被社會推崇轉向被社會排斥,并在隋朝時便散佚了。
四、 《語林》與《世說新語》
《語林》與《世說新語》頗有淵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題材相同,敘事方式相似,它們都是以名士為描寫對象,都是通過簡短的語言描寫名士們的言談舉止。二是《世說新語》吸收了許多《語林》中的內容,清人馬國翰在輯佚《語林》時云:“劉義慶作《世說新語》,取之甚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
我們通過與周楞伽輯佚《裴啟語林》作對比,《語林》有82則故事與《世說新語》中的故事相同或相似,占現存《語林》185則的44%,也就是說,《語林》中接近一半的故事被《世說新語》所吸收或借鑒。毫無疑問,《語林》是《世說新語》成書的最重要的故事來源。例如《語林》云:
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之:“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后為尚書,助魏,不忠于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敕,以致今日。”母無戚容,謂曰:“汝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何負哉!”(《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一)
《世說新語·賢媛》第10則云: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于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戚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語林》與《世說新語》關于王經及其母親的故事的記載一致,僅有個別字的差異,而且未見其他書籍記載,這則故事當為《世說新語》摘錄于《語林》。所以,在閱讀《語林》中的故事時,給我們的印象是許多都是似曾相識,這是因為《世說新語》摘錄了許多《語林》中的故事。
《語林》更多的是裴啟的原創,更接近第一手資料,而《世說新語》基本上屬于“纂緝舊文,非由自造”(《中國小說史略》)。《世說新語》因而更能凸顯《語林》的價值。作為最早的一部魏晉名士教科書,《語林》也是研究魏晉時期政治、社會、文化、風俗等的重要資料,這是不應被忽視的。
五、 《語林》與唐宋類書
類書是采輯若干古代典籍中相關事物的記載,將其依類或按韻編排,以備檢索文章辭藻、掌故事實等,兼具“百科全書”和“資料匯編”雙重性質,它對于保存中國古代的散佚之書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存《語林》中佚文的唐宋類書主要有《初學記》《藝文類聚》《白氏六帖事類集》《六帖新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續談助》等,其中以《太平御覽》為最多,共165條。還有一些故事是《語林》獨有的,也就是《郭子》《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均未記載,因此文學價值頗高,例如《語林》:
王右軍少嘗患癲,一二年輒發動。后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讀竟,乃嘆曰:“癲,何預盛德事耶?”(《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
再如《語林》:
桓宣武性儉,著故褲,上馬不調。褲敗,五形遂露。(《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
雖然通過唐宋時期的類書,《語林》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的恢復,但是也存在許多問題。例如《語林》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同一則故事,唐宋類書之間的記載也不盡相同,甚至差異較大,“鄧艾口吃”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1 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為云‘艾艾’,終是幾艾?”答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
2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太平廣記》卷二)
《太平御覽》與《太平廣記》成書于同一時期,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即使如此,它們記載了同樣來源于《語林》的故事也有差異。關于“鄧艾口吃”的故事,戲言“‘艾艾’,終是幾艾”的是宣王司馬懿,還是文王司馬昭,兩書記載是不同的。而陳壽《三國志·鄧艾傳》中,并未記載究竟是宣王還是文王,究竟孰是孰非,并不能確定。
同一部類書,在引用同一故事時,也有一定的差異,例如:
1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中捋,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太平御覽》卷二十一)
2 《語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駙馬都尉。美姿儀,帝每疑其傅粉,后夏月賜以湯餅,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
3 《語林》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
4 《語林》曰:何平叔,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日喚與熱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時帝始信之。(《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
另外,《語林》中的故事,很多被稍晚于它的《世說新語》吸收,相比較而言,《語林》原創的成分更多一些,而《世說新語》多為“纂緝舊文,非由自造”。這也正是《語林》的珍貴之處。
六、 《語林》的亡佚與輯佚
唐初《隋書·經籍志》首次著錄《語林》,但宣稱這部書已經亡佚,此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書目再無著錄,因此,在修撰《隋書·經籍志》的唐代初年就已散佚。
不過,后人又通過輯佚的方法,《語林》得到了部分恢復,雖屬吉光片羽,但彌足珍貴,從中我們依稀可以見到魏晉小說的面貌以及魏晉風度。元末明初陶宗儀在《說郛》中輯得《裴啟語林》一卷,共21則。清人馬國翰從《初學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唐宋類書中輯得152則,收入其《玉翰山房輯佚書》。魯迅在1909年秋至1911年底利用業余時間,搜集散佚了的魏晉六朝小說,輯錄共36種,近8萬字,命名《古小說鉤沉》,其中裴啟《語林》共180則;今人周楞伽在前人的基礎上,共輯得佚文185則,此書命名《裴啟語林》,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為目前最完備的《語林》輯本。
對于《語林》的輯佚已經有了一定的成績,這些佚文,對于窺探東晉志人小說有重要意義。但是,輯佚很難做到涸澤而漁,即使能做到涸澤而漁也很難做到準確無誤,散布在各種類書中的條目也大都經過了增刪,甚至有的面目全非,因此,對待《語林》的佚文需要有一個審慎的態度。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