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來明月如夢夢——看電影《海角七號》的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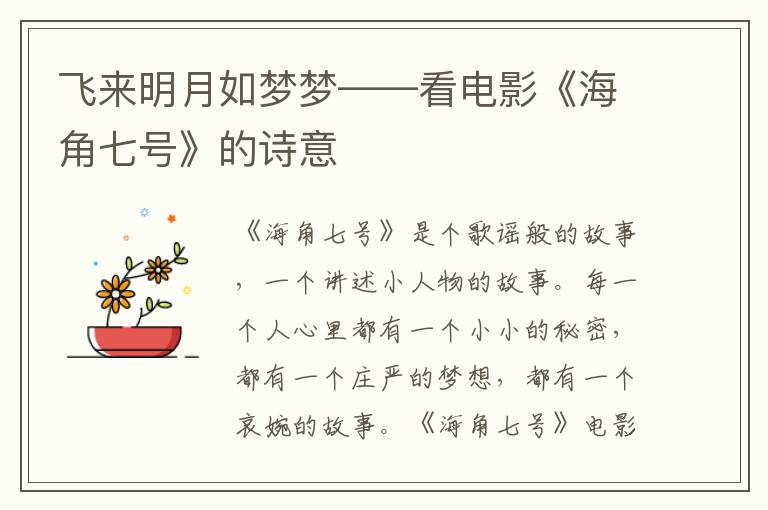
《海角七號》是個歌謠般的故事,一個講述小人物的故事。每一個人心里都有一個小小的秘密,都有一個莊嚴的夢想,都有一個哀婉的故事。
《海角七號》電影海報
小城故事多
《海角七號》開場似乎有點兒亂,頭緒很多。同時有兩個游子還鄉:戰敗國日本青年男教師被遣返還鄉,臺北青年歌手阿嘉落魄還鄉。女主角又接踵而至,一個“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年輕日本女郎——很分神的。
分神還有一個原因,這是部沒有主次角之分的影片。每一個人物觀眾都能認同,每一個人物觀眾都能同情。編導是個速描高手,寥寥幾筆,便勾畫出了眾生百態。見誰都點頭哈腰的米酒推銷員“馬拉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如果真有勤勞、勇敢、智慧的中國人,首推賣酒青年“馬拉桑”。女主角是想當模特卻流落在臺灣小鎮打雜的日本女郎。被人拋棄的怨婦有個聰明淘氣的琴童女兒。橫沖直撞的村代表主席人老心不老,黃昏戀有理論基礎,說是女方的房子大、床大,空了可惜。鬼頭鬼腦的“水蛙”很努力地勾引已經生過三胞胎的良家婦女,而且他也有理論基礎,說是見過母青蛙背上有兩三只公青蛙,而且是和平共處的公青蛙。
小城故事多。每個人都有煩惱的一面,憂傷的一面,和可愛的一面。人人都有不順心的事,每一個人都有理由和這個世界過不去。主角阿嘉不順心的事最大。在臺北當歌手不成,回到小鎮當了個郵差。陰差陽錯地與“破銅爛鐵”的鎮民排練演出。阿嘉的臺詞很少,最精彩的一句在片首:離開臺北時一邊使勁兒砸自己那把吉他,一邊罵“我×!我×你媽的臺北!”罵得真好!出來到大都市闖世界的誰不想罵?我×你媽的紐約!我×你媽的倫敦!我×你媽的東京!什么是天才?能以藝術的方式道出我們心聲的人就是天才。
好的故事大多有幾個層面,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意思。《海角七號》是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但不是好幾個層面,而是有好多個平行的故事。《海角七號》出場了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矛盾,而且看上去幾代人都無法化解的矛盾居然化解了。影片過半,人物之間的矛盾都得到了化解。居然還有好幾對戀愛成功的老少男女,而且都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電影里沒有壞人,也就是經理借著酒力,對日本來的女外賓動手動腳,有點兒性騷擾之嫌。觀眾對配角的認同不亞于對主角的認同。電影里的俊男靚女很酷自不必說,但到處添亂的老阿公也很酷。每一個小人物都有尊嚴:一樹一菩提,一花一世界。
一部詩一樣的電影
《海角七號》是一部詩一樣的電影。中國文學最輝煌的是詩歌,唐詩宋詞輝煌的巔峰無人可以超越。《海角七號》是以畫面來表現詩意。
影片畫面清麗干凈。小城很漂亮,海天一碧,暮云凝色。但歸根結底,景因有人而美——美首先是一種感知。夢心月,淚里圓。海邊獨坐,目送天邊遠去的晚霞,那是“立盡黃昏淚幾行”的詩意。當男女主角相知相識,“憐憫便融化為愛情”(“For pity melts the mind to love.”John Dryden)。阿嘉坐懷不亂,女生低眉垂眼,輕輕牽住他的手:“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沙揚娜拉》,徐志摩)詩意是痛楚的。英雄路短,命運無常。勞馬當過臺北的特警,妻子出走,自己負傷后回家當了一個小交警。酒醉后他拿著前妻的玉照到處示人,撞見一對早戀的小朋友,又掏出前妻的照片介紹。懂事的小女孩看懂了勞馬的悲傷,無限憫意地在勞馬的前額輕輕吻了一下。硬漢勞馬頓時酒醒,淚水奪眶而出,俯身痛哭。
詩意更是含蓄的。花底風來,蘭人慧草,芳心深意低訴。用阿嘉的臺詞說就是“我以前唱歌太用力了”。據說《海角七號》在臺灣的票房好于李安的《色·戒》。應該的,《色·戒》“唱得太用力了”——李安選擇了艱難歲月的難解人物,而且床上床下都太用力,太用力后還是讓人不得要領。含蓄就是點到為止。當遲到的情書最后終于投遞到海角七號的時候,只有收信人阿婆的側影,阿嘉恰恰放下信之后,便輕輕退出。電影《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也有這樣的鏡頭,兩鬢蒼白的男主角找到舊日情人的住處,獨坐樓下,眺望窗戶良久,然后起身離去。有情人終成眷屬,可能是更多的失望。
那艘海上的輪船
抒情和表達真情是件難事。兩個人之間交流都很難,通過電影向世人展覽就更難。馮小剛的《非誠勿擾》到故事結尾時,男女主角說話還是半真半假,只能靠插科打諢來交流。《海角七號》的抒情很自然,靠的是那艘在海上開來開去的輪船,還有那位埋頭寫情書的日本男青年,用日語念出那一封又一封沒有發出的情書,如泣如訴。“情隨芳草連天去,夢逐輕鷗拍水回”——那一封又一封的情書是不停的駐足和回首,分明是李白的詩意:“千里一回首,萬里一長歌。”
交通工具中,火車和輪船是浪漫的道具。海輪緩緩移動,色彩朦朧,像童話里的船,宛如仙子駕鶴彩云間。反復出現的海輪和到處亂跑的摩托車,從時空上把過去和現在對接起來,也把那對跨世紀的中日戀人和80后那對中日戀人的愛情故事連在了一起。古詩“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下古今愁”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海角七號》的抒情也借優美的歌曲和歌詞。“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我會試著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著說完。”演出會上阿嘉給觀眾獻歌,更是把歌獻給了友子:“請原諒,我的愛訴說得太緩慢。”
片尾是臺灣女生趕到港口與情人私奔,背景音樂是《男孩看見野玫瑰》的歌聲,先是中文,然后是日文。汽笛一聲,輪船緩緩起航,女生腳隨船移,不斷往船上翹首張望,尋找自己的愛人。岸上站滿了前來送行的中國人,船上是回國的日本人,船上、船下的人都是滿面戚容,欲哭無淚,不停地揮手道別。此時響起了童聲合唱的《男孩看見野玫瑰》,歌聲中輪船漸行漸遠。場面很是悲蒼,生離死別,蕩氣回腸。大陸的觀眾看了需要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臺灣的國民黨軍政要人的后代看了,大概也需要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
一部給中國人看的電影
《海角七號》似乎有日本情節。連米酒的名字“馬拉桑”聽上去也有點兒像日文。編導把最美的畫面給了說日文的角色,最優美的臺詞是用日文念出來(不懂日文看中文字幕)的。日本情郎念信念得如泣如訴,聽了之后會產生錯覺,懷疑其他語言是否也能有如此優美的旁白。我說是錯覺,因為讀信的情郎是一個日本人,他的愛情故事用日文來講述當然最好。看了《海角七號》,有一種沖動,很想學日語、說日語和寫日語。
《海角七號》中老阿公說一口流利的日文,是小時候學的。這個年紀的大陸老者小時候上學的時候也被迫學過日文,抗戰結束后國民黨又把淪陷區的大、中、小學的學生稱為“偽學生”。《海角七號》在大陸公演時,剪去了老阿公整段說日文的臺詞。老阿公小時候受的是日本教育,上了年紀之后還說日文、唱日文。老阿公騎車送信,一路還不停地用日文哼著小調——聽上去像淫穢黃色小調。有點兒“隔江猶唱后庭花”的意思。不過,有愛情就可以跨越時空,可以超越國界。就像詩人說的那樣,“在選擇背叛國家和朋友之間,我希望自己有勇氣不背叛我的朋友”。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看了《海角七號》都會覺得很親切。兩岸的中國人真是太像了:酒席上的“敬酒”、交警的刁難和動粗,就像北京發生的一樣。米酒“馬拉桑”的廣告用語與大陸的也是一脈相承:“千年傳統,全新感受。一家人的制服。”還有個亂搞開發的鎮長。臺灣那個地方也是到處搞拆遷,到處都是BOT。BOT是英文“Build,Operate and Transfer”的縮寫,是一種項目建設。臺灣到處都是BOT,到處搞開發。臺灣的中國人也是工作居家不易。
飛來明月如夢夢
我們不得不承認,臺灣的電影走在了我們的前面。從塵事、小事、俗事中能看到雅意便是天才。《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有什么《梅蘭芳》,都是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導演要么居高臨下,要么故作深沉——非常惡心。
《非誠勿擾》和《瘋狂的賽車》都是2008年不錯的電影。可惜,《非誠勿擾》也不是常人的故事,奢云艷雨,酒心花態。男女主角都是衣食不愁的有錢人,巧笑不斷,艷歌無閑。總之,《非誠勿擾》仍然停留在溫飽思淫欲的階段。《瘋狂的賽車》和《瘋狂的石頭》是噩夢,很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學習重壓之下的女生對父母哀嘆:“來世再也不做人,寧愿做條狗。”而多數父母照樣放鞭炮,有事沒事照樣開著國產的外國汽車在長安街上亂跑。這樣的地方只能出張藝謀和陳凱歌,出不了李安和魏德圣這樣的導演。張藝謀只能像中小學老師強迫學生死記硬背那樣編排大型團體操,追求軍事化的動作整齊劃一,缺少想象力。這樣的地方只會出《百家講壇》和《梅蘭芳》,拍不出《臥虎藏龍》,更拍不出《海角七號》。
夜靜閑潭春花落,飛來明月如夢夢。《海角七號》有明月,但更奪目的是彩虹。海上那位孜孜不倦寫情書的情郎,飲茶的慵懶麗人,還有送信途中、摩托車上的祖孫兩代人,幾個人都驀然回首,不約而同地說:“啊,彩虹!”這就是詩意,是“飛來明月如夢夢”的詩意。“啊,彩虹!”《海角七號》是觀眾期待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