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事見義與《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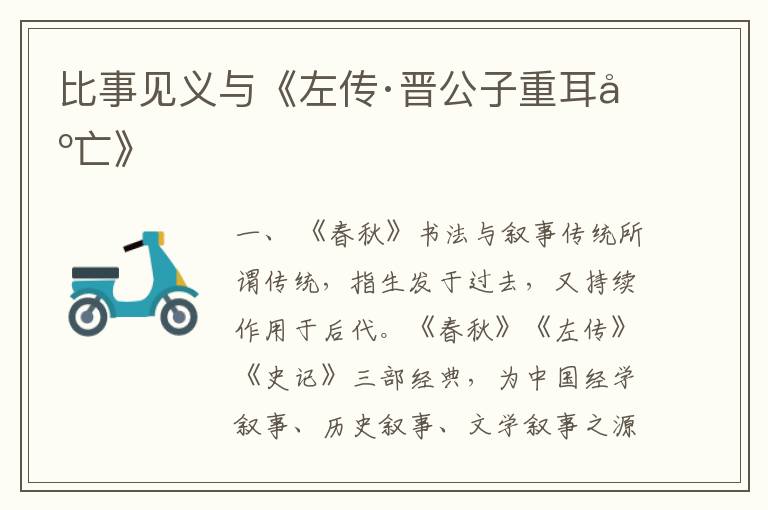
一、 《春秋》書法與敘事傳統(tǒng)
所謂傳統(tǒng),指生發(fā)于過去,又持續(xù)作用于后代。《春秋》《左傳》《史記》三部經(jīng)典,為中國經(jīng)學(xué)敘事、歷史敘事、文學(xué)敘事之源頭。對于后世之作用與影響,既深且遠(yuǎn):史傳、樂府、小說、戲曲之?dāng)⑹拢嗍芷湔锤龋弧洞呵铩窌ā⒐盼牧x法,亦皆為敘事之旁支與流裔。
敘事,或作序事,語出《周禮》,原指典禮進(jìn)行之秩序,或音樂演奏之次第。據(jù)《說文解字》,其本字當(dāng)作“敘”;后世作“序”者,同音通假。就語源學(xué)觀之,中國傳統(tǒng)敘事特重“敘”法,尤其關(guān)注前后、位次、措置、語序之經(jīng)營。西方敘事學(xué),淵源于小說,較注目“事”件、故“事”、情節(jié)。東西方敘事學(xué),自源頭而言,已殊途異轍,后來發(fā)展自然各有千秋。
孔子筆削魯史,而作成《春秋》:據(jù)其史事,憑其史文,以體現(xiàn)褒譏、抑損、忌諱之微辭隱義,《春秋》敘事學(xué)由此形成,歷史敘事、文學(xué)敘事亦自此衍化。左丘明著成《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孔子之《春秋》經(jīng)。晉杜預(yù)《春秋經(jīng)傳集解·序》稱《左傳》:“或先經(jīng)以始事,或后經(jīng)以終義,或依經(jīng)以辯理,或錯(cuò)經(jīng)以合異。”所謂先之、后之、依之、錯(cuò)之,皆是以《經(jīng)》為指歸,而致力于先后、位次之經(jīng)營。清劉熙載《藝概·文概》稱《左傳》釋經(jīng)有此四法,其實(shí)《左傳》敘事亦處處體現(xiàn)此義。
《孟子·離婁下》稱其事、其文、其義,為孔子作《春秋》之三大元素。《禮記·經(jīng)解》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漢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論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統(tǒng)合《孟子》《禮記》《史記》三家之說,約其辭文,為屬辭之能;去其煩重,筆削史事,為比事之功。排比史事,連屬辭文,皆“如何書”之法。清方苞倡導(dǎo)古文義法,《書〈貨殖傳〉后》提示“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強(qiáng)調(diào)法以義起,法隨義變。換言之,排比哪些史事,連屬哪些辭文?皆緣“義”而發(fā),亦隨“義”作轉(zhuǎn)變。世所謂意(義)在筆先,未下筆先有意(義),差堪仿佛。知曉其事、其文,與其義之交互關(guān)系,就可以明白《左傳》如何因比事以明義,如何借屬辭以顯義。了解比事明義,屬辭顯義,有助于敘事傳統(tǒng)之闡揚(yáng),見證《春秋》書法之發(fā)用。
二、 《晉公子重耳出亡》與《左傳》紀(jì)事本末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號(hào)稱“春秋三傳”,各以所得,解釋孔子《春秋》經(jīng)。《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jīng),關(guān)注《春秋》“如何書”之“法”,《公羊傳》《穀梁傳》偏重解讀《春秋》“何以書”之“義”。就《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jīng)而言,所謂“敘事”,其一,指史事如何安排措置,此即“比事”之斟酌。其二,指辭文如何連綴修飾,此“屬辭”之權(quán)衡。其三,古春秋記事成法,為“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劉師培《古春秋紀(jì)事成法考》),于是吾人解讀詮釋史義,亦當(dāng)運(yùn)用系統(tǒng)思維,探究始終。
《春秋》《左傳》,皆編年敘事,相關(guān)史事橫隔而不連貫。其缺失,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云:“或一事而隔越數(shù)卷,首尾難稽。”至宋袁樞編纂《通鑒紀(jì)事本末》,“每事各詳起訖”,“各編自為首尾”。清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書教上》稱揚(yáng)紀(jì)事本末體之優(yōu)長:“文省于紀(jì)傳,事豁于編年。”于是既有是體以后,踵事相因者多,如宋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明唐順之《左傳始末》、清馬骕《左傳事緯》、高士奇《左傳紀(jì)事本末》、吳闿生《左傳微》,皆其流亞也。由此觀之,《左傳》之為體,不只是編年敘事而已!細(xì)考《左傳》敘事,如《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聲子說楚》(襄公二十六年)三篇,堪稱紀(jì)事本末體之濫觴。為篇幅所限,今僅就《晉公子重耳出亡》一篇,論述其紀(jì)事本末,且闡發(fā)其比事見義之書法。
紀(jì)事本末體,顧名思義,自然以敘事為主。就《左傳》解釋《春秋》經(jīng)之面向而言,即先經(jīng)、后經(jīng)、依經(jīng)、錯(cuò)經(jīng)之倫,為比事見義之書法。就歷史編纂學(xué)而言,方苞說義法,所謂“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真可作傳統(tǒng)敘事學(xué)詮釋解讀之指南。義,為著述之旨趣,一篇之主腦。意(義)在筆先,未下筆先有意(義);猶宋蘇軾述文同畫竹,“畫竹,必先有成竹在胸中”。義意,猶將帥,一軍之進(jìn)退離合隨之;又如定位器,左右環(huán)繞,前后映帶,要皆不離其宗。《春秋》,是一部諸侯爭霸史;楚晉兩大國之此消彼長,構(gòu)成紛紛擾擾之《春秋》史。所謂春秋五霸,實(shí)主導(dǎo)其中之浮沉消長。晉文公重耳,在齊桓公小白之后,壓勝荊楚,奠定中原霸業(yè)。重耳,本一公子哥兒,遭遇驪姬誣陷,不得不亡命天涯。《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以紀(jì)事本末體,敘述公子重耳流亡之歷史:奔狄、過衛(wèi)、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及秦,前后十九年。其后得秦穆公資助,終于返國為晉君。晉文公三年文教,于城濮之戰(zhàn),大敗楚軍。周天子三次召見,榮封為霸主。代行天子事,可以討伐無禮。踐土之會(huì),以臣召君,號(hào)令天下諸侯。晉國之霸業(yè)自此奠定,一直持續(xù)到春秋中期始衰。
公子重耳何德何能,居然開創(chuàng)晉國之霸業(yè)?險(xiǎn)阻艱難備嘗,如何塑造一位理想之霸主?《左傳》敘記公子重耳流亡期間,心智之成長,人情之練達(dá),處事之圓融,采行紀(jì)事本末之體。十九年事跡,運(yùn)以筆削、重輕、詳略之?dāng)⑹聲āU\如劉知幾《史通·載言》所云:“言事相兼,煩省合理。”令人讀之,娓娓不倦,覽諷忘疲。《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敘公子重耳出亡,正為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zhàn)、溫之會(huì)、踐土之盟作張本,所謂“先經(jīng)以始事”,皆排比史事,以見史觀、史義之方法。以下,將以《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以下稱本文)為探討文本,敘說“比事見義”“屬辭顯義”之情形。紀(jì)事本末體“爰始要終,本末悉昭”之書法,亦略加闡說論述。
三、 詳略重輕,筆削示義
公子重耳遭驪姬之禍,流亡在外十九年,最終返晉得國,進(jìn)而勝楚稱霸。其中關(guān)鍵,在于“得人”。《左傳》經(jīng)由擬言、代言,一篇之中,曾三致其意焉。“得人”二字,乃一篇之主腦,左丘明纂敘此篇之指義:蒲城遭伐,重耳自言,保命享祿,“于是乎得人”拈出“得人”二字,作為一篇文眼,于是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輕或重,多緣此而發(fā);史事如何編比,辭文如何損益連綴,亦多脈注綺交于“得人”之旨義中。
“奔狄”一章,《左傳》所列“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等流亡團(tuán)隊(duì)成員,固然個(gè)個(gè)是人才;《史記·晉世家》尚有先軫、賈佗,與狐偃、趙衰、魏武子,號(hào)稱“賢士五人”。及曹一章,僖負(fù)羈妻之言“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云云,所謂“得人”,曾獲僖負(fù)羈妻之認(rèn)證。“及鄭”章,叔詹之諫稱:“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公子重耳之得人,再經(jīng)叔詹確認(rèn)。“及楚”章,楚子曰:“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公子之得人,又三經(jīng)楚成王印可。其他,如子犯稽首受塊而載之,公子安齊,從者以為不可;姜氏醉遣公子,與子犯謀;秦穆享重耳,趙衰曰重耳拜賜、重耳敢不拜云云,由此觀之,《左傳》敘事之視角,全在從者,而不在公子。蓋公子重耳之得土有國,必先“得人”!善哉,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何況十?dāng)?shù)人?此《左傳》之人才觀,作為歷史資鑒,治國經(jīng)世,有足多者焉,故左氏書重辭復(fù)如此。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祭義》:“書之重,辭之復(fù),其中必有大美惡焉,不可不察也!”吾于《左傳》四稱“得人”,亦云。
本文一篇之旨義既在“得人”,可見晉文成就霸業(yè),主要在因人成事,《易》所謂“三人同心,其利斷金”。一篇旨趣既在“得人”,于是筆削取舍、重輕詳略,多據(jù)此表述。中國傳統(tǒng)敘事學(xué)之著眼點(diǎn),在主賓、重輕、詳略。換言之,在經(jīng)由或筆或削以見義,篇幅之長短,字?jǐn)?shù)之多寡,多準(zhǔn)此以作斟酌:主意歸趣所在,多詳說、重言;至于賓位,則多輕言、略敘。至于歲月之久暫,幾乎未曾考量。如重耳流亡,“處狄十二年而行”;《左傳》止敘二事: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將適齊,與季隗對話。敘十二年事跡,全文凡152字。其余七年,安章措詞,卻用712言,每年均分102字左右。由此觀之,《左傳》敘事傳人之詳略重輕,多以斯篇指歸為主要考量,不以歲時(shí)之短長久暫為商榷。舉凡有助于塑造公子重耳“得人”創(chuàng)霸之史實(shí)者,則詳載、重言;反之,則輕描淡寫、簡言略敘。如過衛(wèi),只敘“衛(wèi)文公不禮焉”;及宋,止敘“襄公贈(zèng)之以馬二十乘”;其他一概不及,以無補(bǔ)于主意大義故。
公子重耳落難出亡,順道造訪諸國,廣結(jié)善緣,雖險(xiǎn)阻艱難備嘗,而民之情偽亦盡知之,誠有助于政治之應(yīng)變,人情之練達(dá)。此一理想領(lǐng)袖之培訓(xùn)歷程,自是本文之主體與重點(diǎn),故《左傳》于“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及秦”五章,詳哉言之,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清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稱:“《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必有詳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輕,異人之所同,而忽人之所謹(jǐn)。”而孔子于此中“獨(dú)斷于一心”,富于別裁心識(sh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左傳》于此,類敘相關(guān)事跡,運(yùn)用烘云托月之?dāng)⑹路ǎ酝癸@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長與轉(zhuǎn)化。采用紀(jì)事本末體之?dāng)⑹路ǎP之于僖公二十三年,為同年《春秋》經(jīng)“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作為張本。杜預(yù)《春秋序》所謂“先經(jīng)以始事”;傳統(tǒng)敘事學(xué)所謂“預(yù)敘”。更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春,秦伯納公子重耳,即位為晉君,作“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情節(jié)交代。
四、 類敘事跡,表述心智之成長——比事觀義之一
公子重耳性情之轉(zhuǎn)換與成熟,當(dāng)是本文之主腦與大義,猶斯巴達(dá)勇士對哲學(xué)家皇帝之訓(xùn)練。所不同者,公子重耳出于自我調(diào)適,與斯巴達(dá)之訓(xùn)練注重“由外鑠我”,顯然有別。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固是《左傳》行文之特色;然就本文而言,《左傳》純粹敘事處并不多;而借言記事,透過人物對話,以凸顯人物性情、個(gè)性者,反而所在多有。此種“借乙口敘甲事”之手法,《史通·敘事》說敘事方法,其三有“因言語而可知”者,于此篇最多,最具特色。借歷史情境中之人物,述說眼前之人與事,不但親切,備感真實(shí),同時(shí)借言記事,“因言語而可知”,旁觀側(cè)寫,絕妙烘托,情韻神韻多可于此中見之。
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長轉(zhuǎn)化,《左傳》往往借“因言語而可知”之記言敘述之。其敘事方式有二:其一,類比見義,意在言中。《左傳》筆削史乘,選取處狄,季隗之言;及曹,僖負(fù)羈妻之言;及鄭,叔詹之言;及楚,楚子之言;之秦,懷嬴之言等。比事而觀照之,其性情之轉(zhuǎn)化,氣質(zhì)之提升,已呼之欲出。由季隗之言,重耳之缺乏同理心,罔顧他人感受,自私自利之公子哥兒心態(tài),可以想見。過衛(wèi),乞食于五鹿,野人與之塊,公子怒而欲鞭之;由肢體語言,知行有不得,動(dòng)輒怨怒,公子哥兒之性情仍未調(diào)整。及齊,公子安于現(xiàn)狀,未有遠(yuǎn)圖。從者將行,姜氏勉以志在四方,公子不以為然。由姜氏曉以“懷與安,實(shí)敗名”,知重耳猶然懷思美眷,安于逸樂,公子之息氣依然故我。以上三節(jié)載記,《左傳》采用“言事相兼”之?dāng)⑹滤囆g(shù),除記言之外,又參以敘事,以終其義。如處狄篇,接敘季隗“請待子”之言,自私無情正與癡心有情相襯映。過衛(wèi)篇,野人與之塊后,接敘子犯“天賜”之言,稽首受而載之。土塊之賤,頓成得土有國之天賜。將去齊,醉遣公子;及醒,“以戈逐子犯”。由醉遣、戈逐,知公子之桀驁不馴、妄自尊大。唯經(jīng)一事,長一智,自有助于人情之練達(dá)。故于“及曹”一章,曹共公觀其裸;而僖負(fù)羈之妻,饋盤餐、置璧玉,于是“公子受餐反璧”。公子溫文儒雅形象,與前三章幾乎判若兩人。公子重耳之氣度胸襟,從此定位,漸有領(lǐng)袖之氣質(zhì)。心智之自我成長,亦與時(shí)俱進(jìn),逐漸完成了類似“哲學(xué)家皇帝”之訓(xùn)練。
《左傳》敘晉公子重耳領(lǐng)袖人格之完成,多采借賓形主、烘云托月之陪敘法。如“及曹”章,借僖負(fù)羈妻之言,倡言“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已預(yù)敘重耳將返晉國,晉文公將稱霸諸侯,此自僖負(fù)羈眼中看出,從口中道出。“及鄭”章,借叔詹諫言,斷定晉公子重耳返國為君,乃“天之所啟,人弗及也”。“及楚”之章,再借楚成王之觀察“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重耳形象已自魯莽任性,提升為穩(wěn)重、內(nèi)斂、豁達(dá)、斯文!且謂姬姓諸侯,將由晉公子振衰起弊:“天將興之,誰能發(fā)之?”重耳王位,為天命所歸,此叔詹、楚成之共識(shí)。錢鍾書《管錐編》稱《左傳》長于擬言代言,謂是院本小說之椎輪草創(chuàng)。歷史人物之對話,而出于擬言、代言,一則借言記事,再則推動(dòng)情節(jié),三則凸顯個(gè)性身份,《史通·敘事》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傳統(tǒng)敘事學(xué)謂之言敘、語敘。
《左傳》之言敘、語敘,有夫子自道,即自表個(gè)性襟抱者,如“及楚”一章,楚子餐重耳,直言:“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bào)不谷?”楚成王公然政治勒索,公子重耳將如何應(yīng)對?言為心聲,出辭自述,往往可以體現(xiàn)說者心態(tài)。此時(shí)之重耳,不過是位流亡之公子,尚未返晉,尚未得土,尚未有國。然面對強(qiáng)權(quán)如楚成王之勒索,舉凡損及晉國現(xiàn)有利益者,一絲一毫要皆不肯退讓。所謂:“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余也,其何以報(bào)君?”其言外之意,分明耍賴,不愿意絲毫割愛。雖流亡公子,自見得土友國之君王氣象,自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可比。楚成王聞言,哪肯放過?又贊一言:“雖然,何以報(bào)我?”既然強(qiáng)人所難,逼人太甚,于是公子重耳亦強(qiáng)勢回應(yīng),所謂“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退避三舍,雖亦軍事冒險(xiǎn),若兵謀進(jìn)退無虞,亦可以無害,故公子許諾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敘晉楚城濮之戰(zhàn),晉師退避三舍。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對楚成王之言,堪稱“先傳以始事”。原始要終,張本繼末,自是古春秋記事之成法,劉師培《左盫集》之說,《左傳》敘事可作印證。
總之,《左氏》選取史料,針對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間,足以凸顯其心智之成長、性情之圓融、襟抱之開通,裁斷之明快者,類聚而群分之。排比前后之記言,或敘事之事跡,作本末始終之勾勒串?dāng)ⅲ淮酝鯐x文公人格風(fēng)格之形成,乃不疑而具。
五、 女德壸范,對敘顯義——比事觀義之二
自古以來,婦德為“四德”之一,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左傳》敘《晉公子重耳出亡》,敘次四位奇女子:于狄,為季隗;于齊,為姜氏;于曹,為僖負(fù)羈之妻;于秦,為懷嬴。公子重耳于流亡生涯中,先后巧遇四位婦德完備之奇女子,或安定其心,或鼓舞其行,或雪中送炭,或勸善規(guī)過,要皆流亡之奇緣,生命中之貴人。《左傳》敘寫流亡公子,饒富霸主氣象;卻又圖寫四位奇女子之深明大義、高瞻遠(yuǎn)矚、觀察入微、義正辭嚴(yán),諸般形象,與晉公子重耳之言談舉止相較,彼此對比襯托,形成反差之效果,自然見于言語之外。《禮記·經(jīng)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比事之書法,有類比見義之法者,已詳論于前節(jié)。又有對比顯義之方,四位奇女子之言行,對敘公子重耳之德行言語,亦《春秋》書法比事觀義之?dāng)⑹滤囆g(shù)之一。
《左傳》敘寫四位奇女子,處處多與公子重耳之言語德行相對比。如將適齊,季隗應(yīng)對重耳“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后嫁”之言,謂待二十五年,年已五十,無所謂嫁或不嫁,答得干脆大方;且謂“請待子”。深明大義如此!癡心期待如是!相較之下,公子重耳之自私孟浪,便覺自慚形穢。及齊,公子安之。從者謀行,將去齊他往,公子不可。姜氏勉以“四方之志”,戒以“懷與安,實(shí)敗名”。姜氏之高瞻遠(yuǎn)矚,警戒宴安鴆毒,胸襟氣度如是高尚,真非常人所及。重耳既不肯行,姜氏乃與子犯謀,醉遣公子。姜氏能割恩斷愛,公子卻一心迷戀溫柔鄉(xiāng)、安樂窩。姜氏女德足為壸范,對照公子重耳之“不可”“無之”,以戈逐子犯諸負(fù)面作為,于敘事手法,是謂對敘顯義;于文學(xué)技巧,謂之對比成諷。“及曹”章,敘僖負(fù)羈妻之觀人術(shù),直言斷定“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據(jù)此推論“夫子必反齊國”“必得志于諸侯”;若“誅無禮,曹其首也”云云,為僖公二十四年春,公子返回晉國,即位為君王。以及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zhàn)攻曹,預(yù)作張本。但看僖負(fù)羈妻盤餐置璧,公子重耳“受餐反璧”,即可見于取予授受之道,已頗有講究,謙恭辭讓君子之德操,躍然紙上。第四位奇女子,為懷嬴。懷嬴,先婚配予懷公,再重婚予公子重耳,可能因此引發(fā)重耳不悅。不滿之情緒,引發(fā)沃盟時(shí)“既而揮之”。懷嬴義正辭嚴(yán),爭取平等權(quán)利:“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反詰有力,石破天驚。公子知懼能改,降服而囚。大丈夫能屈能伸,知所進(jìn)退,重耳于人情世故,已多所體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曾言:“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xiǎn)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從上述奔狄、及齊、及曹、及秦之對比敘事,可以相互發(fā)明。
屬辭比事之教,歷史編纂之學(xué),人物形象塑造之法,以及傳統(tǒng)敘事之方,理一分殊,彼此之間多有相通相融之處。編比史料,排比史事,其法有二:或以類比,或以對比。就對比敘事而言,或得失功過相絜,或善惡賢否相較,多可收映襯、烘托之效。《左傳》敘公子重耳出亡,主意指趣在“得人”,所謂“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因此,敘事脈絡(luò)不在公子重耳,而在從者;敘事者不在公子重耳,而是季隗、姜氏、僖負(fù)羈妻、懷嬴;以及子犯、叔詹、楚子。就人物形象而言,女性為對比敘事,男性為類比敘事。對比、類比相輔相成,可以相得益彰。
六、 原始要終,本末悉昭——紀(jì)事本末體之濫觴
中國史書有三大體例:編年體,以歲時(shí)月日為敘事經(jīng)緯,《春秋》《左傳》可為代表。紀(jì)傳體,以人物傳記為敘事焦點(diǎn),《史記》《漢書》諸正史可作典范。紀(jì)事本末體,以事件發(fā)展之來龍去脈為敘事基點(diǎn),遲至南宋袁樞《通鑒紀(jì)事本末》,方有成書。編年、紀(jì)傳,各有優(yōu)劣得失:《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稱:“紀(jì)傳之法,或一事而復(fù)見數(shù)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shù)卷,首尾難稽。”于是袁樞因司馬光《資治通鑒》而重編之,以事件為主,每事自為首尾。“經(jīng)緯明晰,節(jié)目詳具,前后始末,一覽了然”。清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書教上》稱揚(yáng)其優(yōu)長,以為“文省于紀(jì)傳,事豁于編年”,因事命篇,體圓用神,謂深得《尚書》“疏通知遠(yuǎn)”之教。清韓菼《左傳紀(jì)事本末·序》稱《左傳》:“傳一人之事與言,必引其后事牽連以終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其實(shí),《左傳》敘事,切合紀(jì)事本末體格式者亦有之。
《左傳》祖始《春秋》之編年,年月井井,人物事件系于相關(guān)歲時(shí)之下,堪稱編年體成熟之作。然細(xì)勘《左傳》之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卻發(fā)現(xiàn)有《重耳出亡》《呂相絕秦》《聲子說楚》三篇,皆攸關(guān)晉國爭霸、稱霸、奠霸之來龍去脈。敘事事件橫越數(shù)年,卻同置于一篇之中,終始本末,首尾一貫,堪作紀(jì)事本末體濫觴于《左傳》歷史敘事之明證。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其事跡之終始本末,同時(shí)載記于《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一年之內(nèi),并未散敘于相關(guān)歲時(shí)之篇章中。一事自具首尾,前后始末了然,確有“疏通知遠(yuǎn)”《書》教之特色。公子重耳遭驪姬誣陷,倉皇出逃,時(shí)當(dāng)周惠王二十一年,魯僖公四年(前656)。首先,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其后七年之間,過衛(wèi)、適齊、之曹、及宋、及鄭、訪楚、至秦,直到周襄王十年,魯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始自秦返晉,即位為晉君。重耳流亡之始末,《左傳》同載于一篇之中,傳承“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記事成法,堪稱后世紀(jì)事本末體之濫觴。而《春秋》比事以見義之書法,雖經(jīng)轉(zhuǎn)化,亦得以考見。
晉杜預(yù)《春秋經(jīng)傳集解序》論《左傳》之解釋《春秋》,有先經(jīng)、后經(jīng)、依經(jīng)、錯(cuò)經(jīng)之倫。《左傳》所敘紀(jì)事本末三篇,要皆攸關(guān)晉國爭霸、稱霸、奠霸之事件。考其作用,或先經(jīng)以始事,如《晉公子重耳出亡》,為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zhàn),晉文公一戰(zhàn)而霸,預(yù)作張本。《呂相絕秦》,為秦晉外交折沖史,作一系統(tǒng)敘事;且為麻隧之戰(zhàn)晉勝秦?cái)∽饕粴v史解釋,可作攻心用謀之資鑒。《聲子說楚》,則細(xì)數(shù)楚材晉用之歷史,亦綜合敘說晉楚爭霸中,人才之依違,戰(zhàn)役之成敗,兵謀之高下,以及楚晉勢力之此消彼長。要皆睹一篇,而可窺數(shù)十年諸事之本末。《尚書》因事命篇,疏通知遠(yuǎn)之效應(yīng),此中有之。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xué)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