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禪”一體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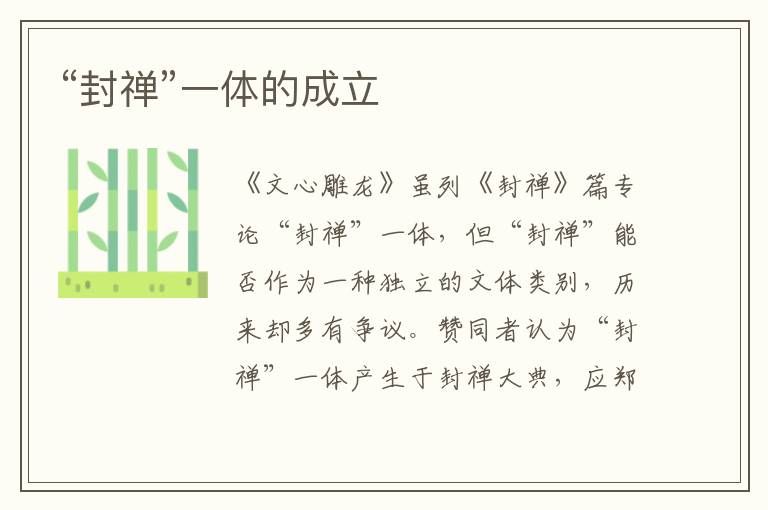
《文心雕龍》雖列《封禪》篇專論“封禪”一體,但“封禪”能否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類別,歷來卻多有爭議。贊同者認為“封禪”一體產生于封禪大典,應鄭重之;反對者認為其旨在頌揚,歸于頌體即可。本文擬在辨析反對者所持理由的基礎上,論證“封禪”作為一種文體的成立。
一、 “封禪”獨立于“頌”體的特征
不同意“封禪”為一體者,往往認為封禪文主體內容是歌頌帝王功德,歸入頌體即可,如詹锳在《文心雕龍義證》中言:“劉勰雖然對它(按:指封禪體)的規格要求非常嚴格,其實封禪不能算作一種獨立的文體。把封禪文歸入頌贊一類,還是比較合適的。”章學誠、蔣伯潛等持論大抵相同。實則,“封禪”與頌體有別,有自己獨立的文體特征。首先表現在,封禪文的主題非常明確,即為勸請帝王封禪。由這一主題出發,言符命、請封禪成為封禪文的獨特內容。
符命,又稱祥瑞、符瑞、瑞應、征祥等,其出現是進行封禪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無符命則不能言封禪。管仲阻齊桓公封禪以符瑞不現,秦始皇借秦文公獲黑龍事強行封禪之禮,漢武帝得寶鼎之后,公卿才議封禪之事。封禪大禮自其出現之日起,就與“符命”緊密聯系在一起。《文心雕龍·封禪》篇論述“封禪”一體,以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為代表作品,《文選》收此三文而立體稱“符命”,正乃同體異稱。封禪文以勸請帝王封禪為目的,文章中都包括對于當朝所現符命的細致描述與強調,如揚雄《劇秦美新》言:“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班固《典引》言:“是以來儀集羽族于觀魏,肉角馴毛宗于外囿。……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這種言符命的內容,在一般的以“美盛德”為目的的頌體文中是絕少見到的。
請封禪是封禪文寫作的目的所在,主旨所歸,一般這類內容出現在頌揚帝王功德、夸耀符瑞臻至之后,如司馬相如《封禪文》言:“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愿陛下全之。”班固《典引》言:“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心。瞻前顧后,豈蔑清廟憚敕天命也?”封禪之事雖更多出自帝王侈心,但封禪典禮所表達出來的君主憂勤國事、國家太平昌盛,無疑于加強老百姓對皇權的依附有一定作用。封禪文作者請封禪的表達雖有獻諛之嫌,但這種請求中未嘗不包含著,作者期望通過封禪這種方式,來提高對老百姓的駕馭能力,所謂“以浸黎元”(司馬相如《封禪文》);來加強國家對異族的威懾力,所謂“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揚雄《劇秦美新》)。
封禪文雖以頌揚帝德、請求封禪為目的,但在頌美中一般又都表達著對受勸帝王的諷諭,這種表達或隱或顯,頌中含諷也成為封禪文區別于一般頌體文的一個特征。如司馬相如《封禪文》在文末直言:“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于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雖然司馬相如此文前文皆在頌揚,諷諭之筆廖廖止此,大有“諷一勸百”之嫌,且亦由此多受古人死而獻諛不止之譏,但文末諷諭還是寄托著作者一片深心。必要一辨的是揚雄的《劇秦美新》,因為這篇文章,揚雄飽受譏議,但看出其深旨者未嘗沒有,劉勰即稱此文“詭言遁辭”,逃遁在表面文字之后的應該就是作者對新朝的諷諫。雖然他通過“劇秦”來“美新”,把自己生存幾十年的漢朝暫時擱置一旁,但對漢政還是進行了贊美,如云“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這種贊揚未嘗不是希望王莽亦能做到如此。今人殷孟倫云:“子云此文,后世以為病,朱子《綱目》至書之為莽大夫,細繹文旨,劇秦而不劇漢,微意甚明。”(《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深得此文諷諭之旨。
不止于上述,已有學者指出,封禪文的開篇亦呈現出獨特之處:“從開天辟地起論,契合讀者身份。這樣的開篇為符命文所特有,成為區別于其他文體的標志之一。”(李乃龍《符命的文體淵源與〈文選〉“符命”模式》)
另外,“封禪”和頌體的不同,還表現在語言形式、風格上。在《文心雕龍》中,《頌贊》篇和《詮賦》《祝盟》《銘箴》等篇先后排列,屬“有韻之文”,《封禪》篇和《詔策》《檄移》《章表》等先后排列,屬“無韻之筆”。表現在具體作品中,司馬相如的《封禪文》由正文和頌文兩部分構成,頌文簡短,屬四言韻語。然而,雖然揚雄、班固皆稱學習了司馬相如的《封禪文》,但全都沒有繼承其正文加四言韻語頌文的結構,《劇秦美新》和《典引》都只有序文和正文兩部分。正文雖都不乏韻語,但總體而言皆屬散體單行之列。顯而易見,用韻并不是封禪文之必須,在此體越來越向前發展時,韻語反而為諸多作家所拋棄。
關于封禪文的理想風格,《文心雕龍·封禪》云:“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于訓典之區,選言于宏富之路,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于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不外乎兩點,一則須“訓典”,即學習經典,形成典雅的文風;二則文辭宜剛健有力。這和《頌贊》篇言頌體文可以“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大為不同。
不論主旨內容,還是體式風格,“封禪”與頌體都是有明顯區別的,應單獨立體。
二、 “封禪”一體成于封禪大典
封禪文產生于封禪大典。《白虎通·封禪》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封禪在古代是異常隆重的祀禮,上封泰山,下禪梁父,向神明報告功德,是帝王藉以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國家大典。圍繞著這場大典,封禪文產生了,如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等均對封禪典禮稱揚備至、充滿期待。
封禪一體催生于封建禮制,這與當時諸多文體的成體方式相同。儒家禮制名目繁多、等級森嚴,是我國諸多文體產生的源頭。劉勰《文心雕龍·宗經》言:“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言:“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這些大體是事實,如誄體產生于“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周禮》)之禮;祭文的產生與祭禮關系密切,《禮記·祭統》開篇便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銘文的產生,源于祭器銘功之禮,《禮記·祭統》言:“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實則,劉、顏二人所列之外,如頌、贊、祝、盟等體與吉禮,章、表、奏、啟與人臣之禮,誓詞、檄文與軍禮等的關系都非常密切。
《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論述具體文體,多強調它們與封建禮制的關系,并以此為基礎,來描述諸體理想的風格特征。易言之,劉勰認為諸多文體的產生源于禮制,其風格的形成又受禮制的制約。如頌體,《頌贊》篇言:“雅容告神謂之頌。……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頌文的創作源于向上天報告功德之禮,出于對神明的尊重,含意一定要純正美好。誄文,《誄碑》篇言:“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凄然如可傷。此其旨也。”誄文產生于定謚之禮,故要總結其人一生的德行,還要表達對死者的哀傷之情,具有感染人的力量。吊文,《哀吊》篇言:“吊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吊文產生于慰問死者家屬之禮,故要對死者作出客觀的評價,文辭雖然悲哀但不可失其純正。他如《祝盟》《章表》《奏啟》《檄移》等等,無不在溯源眾體時將它們與古代禮制相聯系,并在所源禮制的基礎上描述諸體各自鮮明的風格特征。可以說,《文心雕龍》論述文體,追溯它們與古禮的淵源關系,并在禮制的基礎上總結文體的風格特征及寫作要求,已成一種模式,而《封禪》篇也遵從這種模式。《封禪》篇追述“封禪”體的起源云:“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跡者哉!……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正因為封禪是國家的祭祀大典,在祭祀眾典中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由此決定它在風格特征上的一些必然:“茲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于訓典之區,選言于宏富之路,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于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文心雕龍·封禪》)而或正由于此體所源典禮在諸種禮制中地位猶高,《文心雕龍》甚至用了一篇的篇幅專論,突出它比諸多與禮制相關的文體更重要的地位。
劉勰重視封建禮制,亦重視由這些禮制產生的文體,故在《文心雕龍》中列專篇討論“封禪”體。后世贊同“封禪”一體成立者,也多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如紀昀言:“自唐以前,不知封禪之非,故封禪為大典禮,而封禪文為大著作,特出一門,蓋鄭重之。”(見黃霖編著《文心雕龍匯評》)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亦言:“然大典之施,必有隆重之文,應備一格也。”從因禮立體的角度講,“封禪”一體的成立是有依據的。
三、 “封禪”成體的文人、環境因素
當然,“封禪”能夠發展成為一種文體,還有一些客觀因素,主要表現在從漢代開始,封禪典禮已深入儒者文士之心,到了魏晉南北朝,符瑞文化又大大發展,形成了利于“封禪”立體的環境。
封禪典禮是象征國家太平、昌盛統一的國家大典,它神化、強化皇權。在封建社會,皇權是國家的代表,是社會安定的基礎,是國運興衰所在。易言之,希望封禪典禮舉行的不僅有皇帝,以讀書求晉身之階的儒生文士亦迫切追求天下統一太平的秩序,盼望昭示這一秩序形成的“封禪”典禮的踐行。從這一角度就不難理解,何以司馬談因不得與封禪而發泣血之言并終因之亡;亦不難解釋,“封禪書”何以與“禮書”“樂書”等并列,成為《史記》“八書”之一。而司馬相如的《封禪文》亦不是死后“獻諛”之作,“封禪”本是他心向往之之盛典,多有念及,即如《難巴蜀父老文》亦言:“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不獨司馬氏父子與司馬相如,實則如《史記·封禪書》所云:“(建元)元年,漢興已六十余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封禪在秦漢時“成了社會上公同的信仰與要求”,是“人們所共同要求的大事”(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以未能參與封禪大典為憾,亦在文人的創作中有所表達,如班彪《冀州賦》云:“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于伯姬。建封禪于岱宗,瘞玄玉于此丘。遍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不及此事,陪后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獨足娛。且休精于敝邑,聊卒歲以須臾。”文人對封禪典禮的接受與重視,顯然為“封禪”的成體打下了良好的作家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替頻繁,歷朝統治者都面臨著為自己的政權尋找合法依據的問題。雖然這一時期沒有進行過一次嚴格意義上的封禪,但至少如吳主孫皓、魏明帝、晉武帝、前秦苻堅、宋太祖、梁武帝等都曾意圖封禪。與此相關,封禪文化在這一時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宋書》設《符瑞志》,這是正史設符瑞類志的開始,繼之而后,《南齊書》設《祥瑞志》,《魏書》設《靈征志》,此外如東晉王隱《晉書》設有《石瑞記》《瑞異記》,南朝宋何法盛《晉中興書》設《征祥說》,齊臧榮緒《晉書》設《瑞志》等,更有《瑞應圖》之類的作品層出不窮。這些為符命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拓展了空間、擴大了影響。
魏晉南北朝歷代皇帝亦皆以符命粉飾政權,至齊梁更甚。如梁武帝,先是神化其出生,“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梁書·武帝紀》)。而在其統治期間,《梁書·武帝紀》給人深刻而震驚的印象是,關于老人星頻繁出現的記載,只在此篇中就達四十次之多。何以如此呢?《春秋緯》曰:“老人星見則治平主壽。”《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承天,則老人星臨其國。”皆言老人星是國家承平、國主享祚長久的象征,梁武帝本身就是南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而他的貪戀權位也使老人星這種符瑞的出現成為一種“必然”。
可見,事實上,從漢代開始,封禪之禮就是深入儒者文士之心的,歷代皇帝更是利用符命神化、粉飾政權,所有這些都是利于“封禪”立體的環境。而知名作家的相沿而作,使這種文體最終確立。即如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序文所言,《劇秦美新》的創作是受司馬相如《封禪文》的感召,《典引》的創作是承繼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而來。這樣有影響力的知名作家的前后相沿而作,成就了“封禪”一體的三篇代表作品。知名作品的出現成為這一文體立體的有力支撐,而《封禪文》的首發作用,又加上司馬相如個人的巨大影響,對這一文體的成立更是居功甚偉。這與“七”體的形成何其相似!枚乘《七發》,是“獨拔而偉麗”的典范性作品,“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文心雕龍·雜文》),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曹植《七啟》、王粲《七釋》等等,紛至沓來,最終形成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文學體裁——“七”體。而這種體裁,在寫作內容與風格上,后世作者也充分繼承了創始者的特征:“及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云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龍·雜文》)形成了以敷陳夸張的手法言七事以服人的創作傳統,“七”體便蔚為大觀了。自然,由于應用場合的限制,沿司馬相如《封禪文》而成就的“封禪”一體,所涵括的作品數量還無法與“七體”相比,但因為有知名作家的參與與張揚,有前后相承的創作傳統,這一文體形成了區別于其他文體的獨特特征,為文學批評家和選錄總集者所注意,確立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
封禪文無論主旨內容,還是體式風格,都與頌文存在差異,所以不宜竟歸入頌體;“封禪”一體源于封禪大典,催生于封建禮制,這與諸多文體的產生方式相同;文人的重視,利于封禪、符命思想發展的環境,知名作家的參與,典范作品的出現,都對封禪體的最終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體而言,“封禪”作為一種文體是無疑問的,至于其在后代能否發揚光大,則與封禪大典在后代的興衰與否關系密切,不應作為此體不能成立的理由。
[本文為2014年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立項編號:2014CWX032)]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