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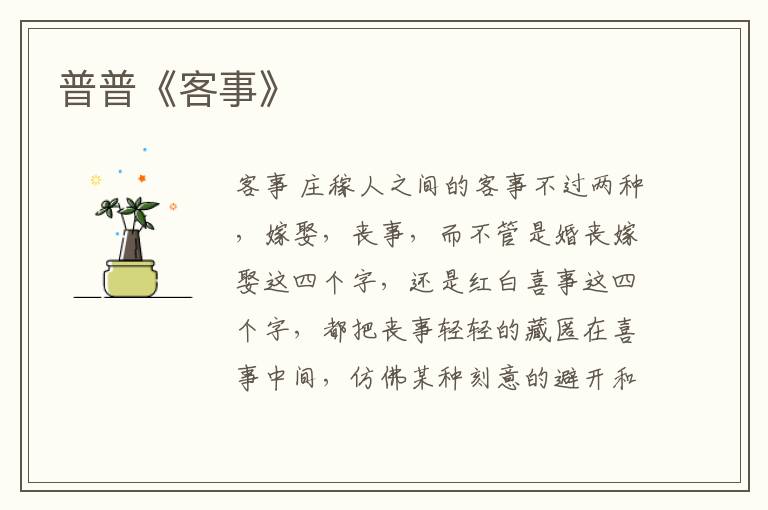
莊稼人之間的客事不過兩種,嫁娶,喪事,而不管是婚喪嫁娶這四個字,還是紅白喜事這四個字,都把喪事輕輕的藏匿在喜事中間,仿佛某種刻意的避開和不想表達,可是它又確確實實是客事當中很大的一件事,除過這兩件,莊稼人也就沒有那種大聚集,大集合的客事了。
頭發花白的老阿媽坐在大路邊的石頭上,與那從河頭上來阿奶輕輕說著話,旁邊的大人們背著籃子路過,點頭招呼一句接著往上去了,孩子們在旁邊跑著,尖銳、鮮活的聲音隨著跑動的腳步不停的移動著。
“……廿四…………十六……”這是兩位老人家用彝話交談當中穿插著的孩子們唯一能聽懂的兩個數字,孩子們完全不會聽和說彝話。
廿四、十六是三姐出嫁日子的待選項,在還未完全定下來的時候,老阿媽坐在路邊與河頭阿奶的對話就好像是相互之間某種親密的告知,又好像是某種內心深處積壓的心事的釋放和表達,說的人和聽的人都用著相互能聽懂的話語來進行相互聽取和表達。上了年紀之后,這樣的交談已經不在乎對方是否是自己最親近的人,是否是完全可以告知的人,那種相近年齡、有相似的情感積累以及互通的語言達成了內心深處的某種默契,你只管說,我只管聽,到后來,聽的也會跟著問幾句,都準備好了吧?姑爺哪里人?家中幾口人……說的人接著把那些過門禮以及嫁妝之間糾纏的往來也一傾而出,不管是怨、還是不滿統統毫無掩飾的直接表達和傾訴。
日頭偏西了,說的如釋重負,聽的似乎也對于那種被需要感到很滿足,這種滿足里有對方對自己的信任和過去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感同身受,然后雙雙挪步往家去了。
有那么兩三年間,母親是喜事上有重任的一人,她們經常三人一組,負責喜事上米飯烹煮,總管根據主人家的客人數估算所需的米飯量,提前通知煮飯人做準備,這個時候蒸子從不同的人家借過來,清洗、配套擺放、泡米、燒水、水開下米、漲開,撇干米湯,倒入蒸子,加柴,上汽后,每一顆米飯都熟透了就出鍋。期間管事的來查看米飯烹煮情況,順手拿起瓷碗舀了半碗米湯趁熱喝下去,然后才又根據時間進度,該提醒的提醒,該叮囑的叮囑。
“她三叔,三姐下月廿四出嫁,到時候來家里喝口喜酒。”
莊稼人之間的喜事就是這樣一家一家到堂屋里告訴主人家的,然后孩子們就都依著主人家通知的時間相互傳遞著。
“三姐廿四要出嫁了。”
“三姐爸也來我家說了。”
“三姐嫁的就是上面那個村的,不遠。”
婚嫁的日子通常都是提前定下來的,主人家再根據時間提前通知到每一位親戚,所以對于那些親戚較遠的主人家,單是請客就得花上十天半個月,在交通還沒那么便利,車輛往來沒有那么頻繁的日子里,趕早出門,順著山路走上一個上午才能到達,當然也有那種到不了的親戚家,往集市上一走,托同方向來的帶個口信過去也是常有的事。
臨近日子了,親戚朋友也請好了,大概來多少人,遠房親戚住下的有多少,數字一出來,就是準備的環節,當然這里的準備也不僅僅是喜事上要用到的鍋碗瓢盆,要吃的蔬菜瓜果,還有那些遠方親戚住下所需要的鋪蓋行李。
一般的莊稼人家里不會有太多閑置的鋪蓋行李,特別是精打細算的女主人手下,凡事有備二三,但少有備好七八九十的,在她們看來備好的七八九十多半都是浪費的,所以籌備環節當中又增加了一個項目,就是從鄰居家借取閑置的毛毯、被褥、枕頭,事情結束后又統一進行清洗干凈,逐一歸還到各位鄰居家中。慢慢的,不論誰家的喜事上,各種鍋碗瓢盆、桌椅板凳似乎都是完整的一套,只不過是在沒事的時候隱藏在不同的人家家里罷了。
去做客得送禮,提籮底部裝上米,上方置上瓶裝白酒、飲料、甘蔗葉子包裹的圓形紅糖,至于數量,是雙數就行,這是平常鄰里之間送的禮。這些東西通常由大人早早送去主人家記賬,孩子們只管換好干凈衣服,等到吃飯的鞭炮聲一響,直接上桌吃飯就可,在那種歡喜的氛圍當中,在孩子的世界里從來沒有這樣的客事對于做客人來講有沒有為難之處,也從來不會覺得那位背著軍綠色裝滿白酒的小水壺,縮身在后,始終沒去記賬處的半大孩子有什么為難,更不知道手持一瓶啤酒坐在院角,看著一眾客人笑聲一片,聽著嗩吶吹奏,獨自抬起酒瓶對嘴大口喝酒的三姐爸有什么憂愁。
孩子的世界里,拼盤很好看,上面的櫻桃被小二吃了,糖很甜,新娘子兩鬢下垂的彎曲卷發絲好漂亮……
散客的時候,那些送禮的提籮被悉數拿出擺在院里,里邊裝著雙數的喜糖、煙、糕點,是做禮尚往來。
三姐嫁的并不遠,莊稼地邊遇到了,孩子們還是依著原來的稱呼,遠遠的,大聲的,干凈利落的叫著:三姐。一旁的三姐夫不等孩子們叫他,到直接接過話頭問道:要去哪啊?孩子們接著回答,之后又回到三姐身上,三姐去哪呀?三姐去不去趕集……三姐則接著回說:小妹長高了,大妹越來越能干了,阿東叔頭發該剪了……同樣的平輩,倒是在三姐的一陣招呼中仿佛是兩個輩分中的人,而這些稱呼,一旁的三姐夫就接不上話了。
喜事,是有準備的客事,年頭年尾都安排較多,而喪事就不一樣了,那種突發以及來不及準備常常讓人們措手不及。
喪事的發生似乎不是一家人的簡單客事,而是一村人的事,所有人參與進來,有人去找老先生看出殯日子,有人受主人家委托,到山那邊的村莊通知一位親戚這里發生的事,接著敲木魚的、吹嗩吶的都請過來,附近來不及通知的人家,主人家的鞭炮聲一響,也能從來往莊稼人身上到聽到這里發生的事情,所以平日里互幫往來的人們,匆匆歇下碗筷就到尋著鞭炮聲到主人家來了。
通常喪事場上就沒什么孩子了,一喜一喪,兩個極端,喜事場上有多歡騰,喪事場上就有多收斂,所以那些被規規矩矩安排在家中的孩子,除了聽到一天到晚不停歇的嗩吶聲,夜里響起的木魚聲,以及遠房親戚到時燃放的鞭炮聲,并不清楚那個院落里究竟安排著怎樣的儀式,院中人如何悲傷流淚,他們唯一看到的也不過是喪事場上幫忙出來的人們頭上纏著的白布條,聽到的也不過是來送行的人們的樣子。
“阿珍姐來了,背來了一籃子大青菜,說是她的一點心意。”
這是阿珍姐對于那位去世的阿爺的一種送行方式,對阿爺的身后事盡的微薄之力。
立春剛過,氣溫沒有一絲一毫的溫柔的意思,阿珍姐穿著靛藍色洗了發白的褲子,膝蓋處向外突著,拼補上的一塊長方形布料也顯得舊跡斑斑,褲腳邊磨破后,線絲往下掉成了一小撮,腳上的布鞋濕噠噠,腳拇指向外凸露著。
阿珍姐進到堂屋點了三炷香,三跪三拜,起身背起籃子往外走,依然比劃著,咿呀著說:“一點心意,我的一點心意。”
主人家一路挽著追到了門外。
她的牙齒落光了,話說不清析了,頭發早已不見灰跡,主人留不住,目送著她離開。
阿珍姐,像是一個名字一樣,代表著阿珍姐自己,若是按輩分嚴格說起來,得叫大嫂,又或者大嬸,但是孩子們還是叫她阿珍姐,就像不愿意將三姐叫成嫂嫂一樣。
她叫阿珍姐。
“阿珍姐不吃肉的,她只吃雞蛋。”
“阿珍姐生阿三的時候就吃了三個雞蛋,沒吃的。”
“阿珍姐割田埂上的草,一鐮刀下去,把蜷縮在中間的菜花蛇割成了兩段,一點沒有害怕。”
“我媽媽請阿珍嫂來家里幫忙,提前打聽清楚她吃什么,不吃什么,最后做出來她也沒吃多少,最后給她準備了答謝禮她也沒收,她說那頓飯菜的謝意就夠了。”
阿珍姐家里的房屋建了很多年,柱子支撐著頂部橫梁、椽子、瓦片,除了能遮擋陽光雨水,似乎在御風抵寒上面沒有什么作用,站在院里忙碌的她同院外路過的熟人咿呀著打招呼,說著話。
喜事場、喪事場,一樣的人來而聚,人去而散。
午后的暖陽之下,老阿媽、阿奶靠在墻腳,用著她們之間相互能聽懂的彝話說著什么,依偎在一旁的孩子靜靜的聽著,兩人時而說的帶著些仇恨,時而帶著些不滿,有時又點頭表示某種贊許和欣慰,偶爾說到激烈處,淚花刷的流下來,隱忍中鼻涕也跟著流下來,徒手一擤,揩在路邊的石頭墩上,旁邊的孩子抬頭看,阿奶則立馬正身正氣的呵斥孩子:“不要用手扣泥巴,不聽話要打。”
孩子起身跑了。
兩人轉頭切換到那些聽得懂的語言當中繼續說著。
大人們路過了,她們就抬頭自我解釋道,我跟阿奶坐一會兒,坐一會兒。
……阿珍……阿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