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衛國《許衛國:井 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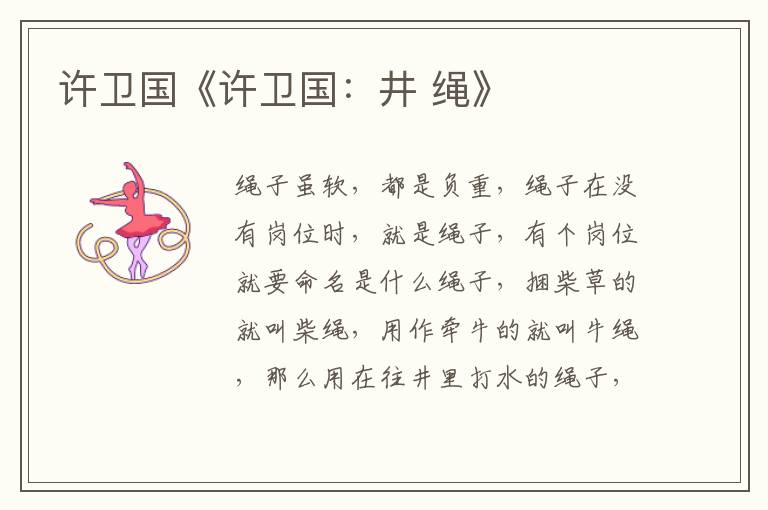
繩子雖軟,都是負重,繩子在沒有崗位時,就是繩子,有個崗位就要命名是什么繩子,捆柴草的就叫柴繩,用作牽牛的就叫牛繩,那么用在往井里打水的繩子,就得叫井繩。那年月,不是每家都有井繩,若是淺井還好,一般人家可以做得起,要是深井,就得好幾斤的苘或蔴,要不少錢呢。沒井繩就向關系好的人家借。借東西沒什么,鄉里鄉親,誰用不著誰啊。有東西不借,是不擱人緣,是狗都不親嘴的人家。這些人家往往被人瞧不起,孤立無助呢。
好了,來講井繩。井繩在井上,難免受潮水漬,這就要求選料要好,做工要好,選料好是耐用,做工好是質量保證,如果手藝不精,即便好料子你沒有搓好,繩子松松垮垮的,也不耐用,說不準哪天水桶提到一半,繩斷了,水桶擊落水面,水桶也變成幾塊木板了,雞飛蛋打,那真是煩心死了。
井繩還講究把澀,雖然水淋淋的,握在手里卻不打滑,提高一寸就是一寸,絕不會反復倒退,捋手。有條件的加點棉繩子在里面就有這種把澀的效果。不過越是好用的繩子,用的人就多,就容易損壞得快,這是因為和“好人不長壽”是一個道理。其實好人是長壽的,有法律保護,有道義擁戴,只因為好人總是刻苦勞動,總是廢寢忘食工作,總是見義勇為奉獻,危險就多了一些。
打水的時候,把井繩拴在水桶系子上,那種栓法要技術,扣不死就會桶繩分離,那結果也不亞于竹籃打水一場空。扣死又不易解開。當水桶到達水面,水桶是木頭的,天性決定它不會主動下沉,這就靠掌握井繩的手那不可言傳的巧妙一抖,水桶就會一頭栽進水里,一口喝滿,即使鐵皮桶,由于有空間,就有船的特性,也不會輕易灌滿水,往往也要這么一抖。如果那些人是外行,抖來抖去,抖得自己就差點下去直接灌水,還是水桶漂浮。水打滿了,要往上提,切記不能太靠井口邊緣,腿必須前后分開,不能并齊,否則只利于失足,一頭栽進去。兩手必須在半秒之間交換前后,提上來的井繩,多余的要不斷地往身后撂,這樣不礙事,效率高。
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上塘鎮,那里是丘陵地帶,嚴重缺水,有時真是貴至如油,油可以不吃,但水不能不喝。所幸那里有一口井,世代尊稱為龍井,看那井深似無底,若無神助,非人力難成。傳說是當年劉伯溫在此率官兵所挖,也說是他一根棍子戳下去所成,不管怎么說,井是存在的,而且很深,深到挑水的人,即使是大勞力,也只能擔一桶水,另一頭就是井繩。那井三十多米,把一桶水拎上來,讓物理學家一算是要不少力氣的,那繩子重量也就是那一桶水的重量。當時,那里嚴重缺水,有這口龍井,也真是龍恩浩蕩,謝祖龍恩了。
那一年夏天,大旱,龍井見底,任你怎么會抖井繩,水桶也吃不進水,就得有人下去,用水瓢一瓢一瓢舀。派大人下去,過于沉重,幾個人拉著井繩還說“快支持不住了”,大人下去也是大材小用。人們見我穿來穿去,甚為活躍,就說,叫這家伙下去,你看他猴子一樣呢。那時我剛好九歲。體重也就不過一桶水重。說著就把井繩系在我的腰上,我并不害怕,倒想下去看個究竟。井繩不斷往下放,我不斷地下沉,到了底下,再抬頭,只見井口宛若一輪明月,只有碗口大小了。我低頭看到井底那里有去年的山芋還新鮮如剛出土,有一副眼鏡,有兩支鋼筆,有幾個手指粗的黑洞向外涌水,還有幾條泥鰍,不知是人丟下了,還是它飛進來的。不一會,舀滿了三桶水,覺得寒冷胸悶,我就大叫要上去,他們知道小孩子的承受能力,就拉緊井繩把我趕緊往上升。
我把戰利品拿上來,消息不脛而走,這些在當時都屬于貴重的東西。頓時就來了失主,眼睛是小學朱老師的,他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趁火打劫,還帶來老婆作證,說某天某日去楊李圩子岳父家,路過,在井邊喝水,不小心掉下去的,那時戴眼鏡極少,誰也不會隨便敢說那是他的。朱老師作證解釋都是多余的,那眼毛毛的就是證明。知識分子那時誠實,但總是難免有點迂腐。鋼筆是上塘中學初二的揚大嘴的,他講得一點沒錯,上海永生的。筆尖是小嘴的那一種。另一支是大隊劉會計的。他們只顧失而復得的高興,卻把我遺忘了。
俗話說,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這個怕井繩的人,根本就沒見過井繩,它和蛇差別大著呢。要么可能是被咬傻了。
作者簡介:
許衛國, 江蘇泗洪人。編輯記者 文藝編導、 文旅策劃、文化管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鳳凰智庫專家組成員、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特約作家。作品散見《中國作家》《文藝報》《中國報告文學》《清明》《莽原》等報刊;出版《上帝原來是個近視眼》《遠去的鄉村符號》(一、二版)《許衛國文集》(五卷)《汴河四重奏》(四卷)《小高莊》《父親的革命》《春到上塘》等著作多部,遠銷海內外,多次參加國際、國內書展,曾獲中國作家協會、團中央、中國散文學會及省等大獎,部分作品再版或轉載文摘類報刊、入選權威文集;發表、上演大戲五部。《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當代作家研究》《光明日報》《中國新聞出版報》《中華讀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文匯報》《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等有評介,江蘇衛視有專題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