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姑娘不會游泳》李慧慧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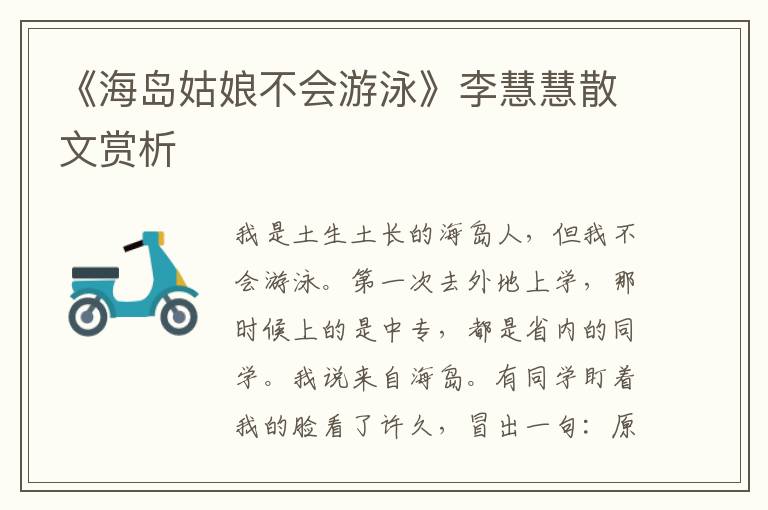
我是土生土長的海島人,但我不會游泳。
第一次去外地上學,那時候上的是中專,都是省內的同學。我說來自海島。有同學盯著我的臉看了許久,冒出一句:原來海島人皮膚這么白啊。由于在兩個月的暑假里沒有學業壓力,不用做暑假作業,天天在家里呆著,像只豬一樣被母親養得白白胖胖的,還穿了一身黑衣服,顯得特別白,平時雖然不是特別白,但我肯定自己與同學想象的黝黑黝黑還差著一些距離。我呵呵笑笑。同學可能覺得我是海島人里少數幾個白的,于是又問,是不是你家不住海邊?我帶著幾分抱歉,我家不住海邊,但我騎自行車十幾分鐘也能到海邊,而且我認識的女孩子皮膚黝黑的真的不多見。同學更納悶了。
那你家里有船嗎?
沒有。
你們家的煤氣灶會不會進水,飯燒著燒著是不是海水一來就滅了?說這話的時候,同學還一臉擔心。
是不是像威尼斯小城一樣出門要劃船的?
你父親要出海嗎?
我父親不用出海,我們家三代都不是漁民,都是農民,而且漁民未必有船呀,有船的叫船老大,漁民都是打工的。
同學們眼里都帶著好奇,帶著迷茫。連班主任老師都問道,那你們家每個人可以分到多少土地?我說,不多,一個人三分吧。班主任點點頭,嗯,這還是有點區別的。
什么區別?我不解。
底下的同學笑道,我們家每個人一畝。
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心里的慶幸,一畝啊,那得多辛苦,幸好我們每個人才三分田。那是我第一次離開生活的海島,第一次坐長途汽車。同學們那一臉好奇的神情,班主任老師聽到答案時的樣子,到現在我依然記得,他們是覺得困惑,是覺得奇怪,而我不知道,那時候有多少同學在心里停留著這樣那樣的困惑。
那天,杭州的同學來我們島上,我請她在島城一個小飯店里吃飯,點了幾個菜,其中有一個菜是帶魚,紅燒帶魚。放在盆里的帶魚很鮮活,賊亮賊亮的,像晚上的月光,但是同學小心地夾了一口,皺著眉頭說,太腥了,你們平時都這么吃的嗎?是啊,我們平時都這么吃的。同學吃了點別的,再也沒有碰帶魚一口。結束的時候,同學說,你以前說學校里帶魚不好吃,原來你家鄉的味道是這樣啊。同學所說的學校里的帶魚,是指我們學校食堂的帶魚。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帶魚的另一種味道,沒有海的味道,淡淡的,只有青椒的咸味,沒有海的鮮味,沒有屬于大海的味道,缺少海鮮特有的肉質感。雖然學校的帶魚不好吃,但是同學們喜歡吃,唯有我這個來自海島的人,只點了一次,再也不想吃。母親或許知道我在學校吃不慣沒有海鮮的伙食,那時候不像現在快遞公司那么多,實在想吃網上也可以買,那時候,母親在老家做好風干的帶魚,油炸一下,托長途汽車的師傅帶到車站,我自己去取,有時候寄一點曬干的魚干,彌補我吃不到海鮮的遺憾。當然,這樣的幸福,這樣的滿足,一個學期里也只有一兩次,郵寄太貴而且周期長怕爛掉,多數都是學期開學的時候,從家里帶個大包小包的,然后回到學校慢慢吃,當然也會分給寢室里的同學吃點。第一次分的時候,有一位來自山區的同學,或許沒有吃過螃蟹,拿著一只蟹爪問我,慧,這個螃蟹怎么吃啊,先吃里面還是外面?噢,原來還有不會吃螃蟹的人啊。告訴她怎么吃以后,她咬了一口說,不好吃,還是剛才那個熏魚好吃。我心里想,原來還有人不喜歡吃螃蟹的呀。再一想,有啥啊,海邊生長的父親吃螃蟹還要過敏呢。當然現在這位同學走南闖北的,吃多了螃蟹,也喜歡上了吃螃蟹。杭州來的同學,在我們家住了一晚,我盡地主之宜,帶著她四處看了看,海邊當然要去。去了以后,她有些許失望,你們家鄉的這片海水怎么這么渾濁呢?是不是太渾濁了,所以你才不愿意在這里學游泳啊?原來,真實的小島也有電影院,也有大型商場,跟我們城市差不多啊。
是啊,差不多啊,有什么區別呢。除了面對海鮮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你覺得很腥,好像作為土生土長的海島姑娘,我與你們這些城市姑娘并沒有太大的差別啊。
還有什么呢,噢,小時候,我織過漁網,織一頂,賺幾毛錢,算是勤工儉學,當然每一頂最后的收尾工作都是母親完成的,我只會簡單的粗線條地織。到底織了幾個暑假,賺了幾塊錢,我忘記了,現在幾乎看不到織網的女人了,只有偶爾在碼頭看到有人在補網。或許是因為技術先進了,不用人工織網了,或許是因為現在的漁船都轉產轉業了,或許因為捕魚種類的原因而不用那樣的漁網了。漁叟中拿著梭在碼頭補網的場面,這些年基本看不到了。倒是我們的孩子,都學會游泳了,當然,是在游泳池里。
還有什么呢?我得再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