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蘭秘境》張祚臣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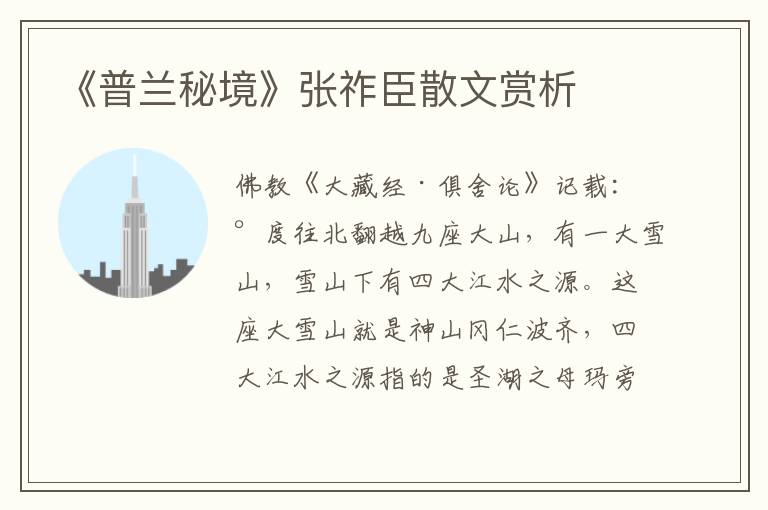
佛教《大藏經·俱舍論》記載:印度往北翻越九座大山,有一大雪山,雪山下有四大江水之源。這座大雪山就是神山岡仁波齊,四大江水之源指的是圣湖之母瑪旁雍措。古代藏族人認為,瑪旁雍措是廣財龍神居住的地方,東為馬泉河,南為孔雀河,西為象泉河,北為獅泉河。
在孔雀河谷、岡底斯山脈和喜馬拉雅山之間有一片谷地綠洲,它就是阿里地區的普蘭縣城。普蘭縣雖與尼泊爾和印度接壤,但是相隔十萬大山,并無公路相通。千百年來,尼泊爾和印度的香客商賈翻越喜馬拉雅山脈,走的都是險峻的山口,肩扛背負,人力為之。眾多的古商道似孔雀開屏,伸向大山深處。
孔雀河將普蘭縣城一劈兩半,分為舊城和新城。西北達拉喀山上裸露的巖石和斷層,仿佛歲月老人的褶皺,遠處隱約可見的殘垣斷壁是古象雄國遺落的王宮遺址嗎?舉目四望,雪山爭鳴,喜馬拉雅山脈綿亙不絕的峰頂像一條白色的練帛纏繞在普蘭的頭頂,所以普蘭乃名副其實的“雪山圍繞之地”。
從拉薩縱橫馳騁1400多公里,朝覲無數宗教圣地,夜宿偏寂無人的小鎮,一直在海拔4500米以上行走,歷經停電、高原缺氧、食物不適,這片海拔3600米的普蘭谷地,正是難得的休憩之地。
這片綠洲不愧是豐澤之地,清冽的泉水從我們入住的普蘭賓館門前流過,一家藏族同胞在溪水邊宰羊沖洗,似乎要迎接一個盛大的節日。幼兒園的孩子們剛剛放學,像一群沖出牢籠的小鳥,嘰嘰喳喳地奔向他們的父母。
一夜休息,第二天一早便奔向吉烏寺。
《楞嚴經》說:“世為遷流,界為方位。”形形色色的世界原本就是一個個時空交匯的產物,我們處在此生此世,而不是彼生彼世,都是機緣巧合的結果。
從時間上說,吉烏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藏傳佛教前弘期的蓮花生時代,據說當年蓮花生大師一路除魔降妖而來,曾在山上逗留七日,至今山體的西南面還有蓮花生大師修行的山洞,因而這座淡紅色的小山被稱為“桑朵白日”,漢語意為“銅色山”。這正是傳說中蓮花生大師所居凈土的名字。
然而,現在成規模的吉烏寺卻是由山南地區扎囊縣頂布欽寺的喇嘛“頓珠圖美”興建的,頂布欽寺是一座噶舉派寺廟,確切地說,是噶舉派的一個分支——“淖浦噶舉”的寺廟。吉烏寺的歷任活佛,都是由頂布欽寺委派。頂布欽寺建于公元1567年,所以吉烏寺的建設不會早于1567年。
或許由于噶舉派的分支過于龐雜,差別也沒有字面上理解的那么大,這座由”頓珠圖美”創立的噶舉派寺廟后來信奉的卻是“竹巴噶舉”——“竹巴噶舉”也是不丹人信奉的主要宗教。
從空間上看,吉烏寺處在圣湖和神山之間,東臨靈湖,西鄰鬼湖,西北是神山岡仁波齊,東南乃雪山納木那尼。從1907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繪制的一張地圖上看,如果以吉烏寺所處的中心位置畫一條線,將圣湖和神山串聯起來,恰如佛經中的“卍”字,是為吉祥海云,吉祥喜旋。
在佛教中,岡仁波齊被視為世界的中心——須彌山;在西藏原始苯教中,岡仁波齊是“九重山”,乃祖師降落之處;在耆那教中,岡仁波齊被稱作“阿什塔婆達”,即最高之山,是耆那教創始人瑞斯哈巴那剎獲得解脫的地方;而在印度教看來,岡仁波齊是“濕婆的天堂”。所以岡仁波齊是佛教、苯教、耆那教、印度教共有的神山,每年印度、尼泊爾、西藏以及中國內地的香客紛至沓來,朝拜他們心目中的神山。
圣湖瑪旁雍措在斯文·赫定的游記中被稱為“靈湖”,斯文·赫定沿用了印度的名稱“馬那沙羅發爾”,并說:“凡是身體觸到馬那沙羅發爾的土地或在它的浪潮中沐浴過的人,將走進勃拉馬的天堂,誰是飲過它的水的,則將升上西瓦的天宮,并解脫百次輪回的罪孽。”
早期苯教徒稱它為“瑪垂措”,而藏語瑪旁雍措含有“永恒不敗”的意思,名稱的改變隱含著宗教激烈爭斗的歷史,傳說十一世紀在瑪旁雍措湖畔曾經發生過藏傳佛教與外道黑教的斗爭,最后以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勝利而告終。
早晨,星星似乎剛剛隱去,白云黑云交替翻滾,有時候突顯一道耀眼的光芒,很快又被烏云遮住,天空中云詭波譎,氣象萬千。
經過鬼湖拉昂措,湖面呈現深不可測的深灰色,四周是深褐色的山體,仿佛回到宇宙洪荒,北方神山岡仁波齊那鉆石般的基座覆傾在岡底斯山脈的電光石火之中,但是頭頂仿佛削去了一塊,始終不見真容。
岸邊堆起的瑪尼堆磊石其上,纏繞著白色的哈達,朔風勁吹,發出嗚嗚的悲鳴。看來拉昂措鬼湖的名稱名副其實。拉昂措是一座咸水湖,寸草不生,鳥禽不飛,宇宙末日一般的死寂。
經過一片月牙形的淺灘,這里大概就是斯文·赫定著作中描述的鬼湖和靈湖的交匯之處,鬼湖和靈湖原來相通,后來由于地質和水文的變化,只留下這片淺淺的沼澤了。
然而到達靈湖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湖面波瀾不驚,深藍見底,斑頭雁和黑頸鶴喧嚷著飛過水面,納木那尼雪山的峰頂在白云之間時隱時現,雪山映照的光芒,仿佛那山就在眼前,伸手便能碰到。
佛教徒認為,瑪旁雍措是最圣潔的湖,是勝樂大尊賜予人間的甘露,圣水可以清洗人心靈中的煩惱和孽障。她是這個宇宙中真正的天堂,是眾神的香格里拉,萬物之極樂世界。
當年斯文·赫定對瑪旁雍措進行了科學考察,發現靈湖呈蛋圓形,南狹北闊,測得直徑二十四公里,水面面積四六零四公尺,水深八十一公尺八寸。
轉過兩座山坡中間的狹長地帶,看見左邊一座淡紅色小山,山頂的建筑白墻紅頂,頗似縮小了的布達拉宮。山腰間似有小路曲曲彎彎,一群朝拜的信眾正在轉山,山頂建筑和殘墻斷垣之間拉滿了長長的經幡。
這座小山就是“桑朵白日”,山頂之上建筑就是吉烏寺。
把車開到后面的山坡上,沿著一條小路向上攀登。愈是接近山體,愈明白“銅色山”之稱的妙處,山體的前半部分是陡峭的褐色巖石,瘦削獨立,山上山下,飄滿了五顏六色的經幡。
低頭經過彩色的經幡,山勢愈加陡峭,在山體的岬角上可以望見碧波萬頃的瑪旁雍措,高原湖泊,濃密的白云就浮在水面上,天地之間仿佛被壓縮在一起,假如上帝在宇宙之上觀看銀河系,也會看到同樣的景象,扁平而悠長。
攀過覆著貝瑪草的白色院墻,穿過黑黢黢的大門,我們在一片殘垣斷壁的迷宮里穿行,一只巨大的轉經筒露出了木質的軸心,在一間間殘破的小屋里,堆滿了家什器物,甚至在一堵倒坍的院墻下壓著一只銹蝕的鐵鍋。我懷疑這才是原來的吉烏寺所在。
這座由頂布欽寺的喇嘛“頓珠圖美”建立的噶舉派寺廟,有著至少四百年的歷史,然而卻在文革中毀于一旦,只剩一堆瓦礫。
1907年,當斯文·赫定來到吉烏寺的時候,也許就是在這些殘垣斷壁中的某一個房間里安營扎寨,把這里當做他們的總營,盤踞數日。期間還認識了一個十二歲的蔡林·童都彼喇嘛,童都彼喇嘛過膩了單調的生活,請求斯文·赫定帶他遠行。然而,當斯文·赫定真正出發的時候,他又猶豫了,也許沒有勇氣面對未知的世界。
沿著轉經路繞到后山,后山較為平坦,山坡上長滿了高原灌木,山頂就是現在的吉烏寺,現在的吉烏寺重建于1985年,院墻均勻地涂抹著白紅兩色,寺院簡陋,大經堂似一座不起眼的堂屋,但是經堂之上卻法輪常轉,鹿野呦鳴。
經堂左邊是僧人的生活區,一架天線高高矗立,寺院現在的編制為僧侶6人,可是經堂的大門緊鎖,見不到一個僧人。只有一只藏獒慵懶地伏于經堂門口,見我們走近,睜眼看了一下,又繼續睡覺了。
一會兒,一位喇嘛急急地走來,手中握著一本經書,身穿黃色布褂,頭頂咒師辮,幫我們開了鎖,繼續念他的經書去了。
據記載,原來的經堂中有一座精雕細刻的檀香木蓮花生大師神像,后來毀于文革,現在所供乃蓮花生大師的藥泥塑像。塑像置于玻璃柜中,左手執人骨手杖,怒目圓睜,蓮花生大師就是一副驅魔大士的形象。
像前供奉酥油花,兩盞酥油燈長明。涂成鮮紅色的酥油代表著鮮血和動物內臟,置于鮮紅的案桌上。在一堆花花綠綠的紙幣中,有美元、歐元、尼泊爾幣等,吉烏寺雖小,卻是各國游客和香客的朝拜之所。
吉烏寺是一座竹巴噶舉派寺廟。元朝末期,薩迦派由于元帝國的崩潰喪失了保護主,帕木竹巴噶舉派結束了薩迦派的統治,但是噶舉派卻吸收了薩迦派某些教義,比如對“道果”教義的尊崇。
噶舉派強調心之光明。放棄所有妄想、所有與生死輪回的狀態或與有寂有關的思想,叫做“涅槃”。但這仍是心之空的一種想象,因為大家所能了解的一切、能肯定的能否定的一切、能追求的能拒絕的一切都僅僅是出自心的幻覺,事實就是空。
修行的目的就是從幻覺世界中解脫出來,為此目的,就必須使用智慧、靜修、倫理和認識的冥想以及修習實踐的雙“道”。
走到后山的尾部,見一排銅色的轉經筒,與其他寺院不同的是,轉經筒上面安上了風輪,隨著風輪的轉動,轉經筒也吱吱呀呀地響著,讓這神山圣湖之風,默默誦念佛教的經文。轉經筒下面擺滿了白色光滑的石頭,每一塊石頭都是一個祝福。
在后山平緩的坡地上,有一排排白色的靈塔,吉烏寺的歷代喇嘛和活佛圓寂于此,在這神山和圣湖之間永生。靈塔周圍堆滿了大大小小的瑪尼石,一眼望不到盡頭,在西藏這是我見過的最大的瑪尼堆,在堆起的石塊上,有數不清的藏牦牛的頭骨,雄健的牛角指向深藍色的天空,神秘肅穆,代表偉大的靈魂和他們所傳承的藏傳佛教永世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