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竟陵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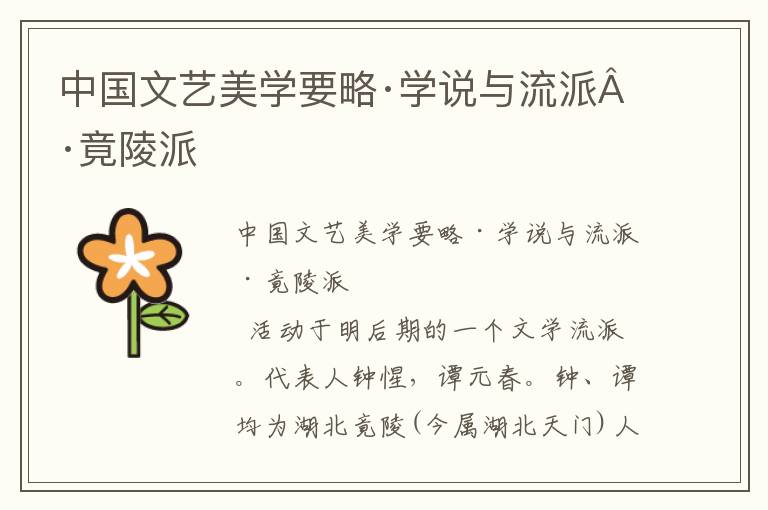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竟陵派
活動于明后期的一個文學流派。代表人鐘惺,譚元春。鐘、譚均為湖北竟陵(今屬湖北天門)人,流派因此得名。有明代,前后七子“第以剽略相高”之風綿延百年,影響深遠。明后期文人不滿于此,紛紛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矯正李王之弊,繼公安三袁獨標“性靈”、力排李、 王諸子之后,鐘惺、譚元春一方面以立僻說為事,欲排李、王并取代袁氏一派;一方面欲矯公安派破律壞度,俳諧空疎,失之“俚” “陋”之流弊,以幽深孤峭為宗,怪字險韻為文。竟陵派一系列理論主張,皆由此而發。
首先,針對復古派擬古文風,繼承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審美理論,在文學創作上提倡以“性靈” “靈心”創造的“真詩”:“精神者……其變無窮也”故表現變化萬端,各極其致的精神情致之作即是“真詩”。鑒于公安未流的淺率浮滑,在審美理想上追求“義理集乎中”的“奇趣”、“別理”,力主“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的趣韻。即到遠離“喧雜”的現實生活的“虛無飄渺間”,探悟古人的審美情趣以及“極無煙火”的文字“機鋒”,以創制“雄博高逸,迂迴峭拔”的奇險之作。因此,如果說公安末流險入空疎俚俗無以自拔,是由于時代造成的認識局限所致,那么既繼承公安派的審美理論,又肩負著雙重使命的竟陵派,同樣也無法找到出路,達到更高層次的審美理論與審美理想的統一,他們選擇的道路,只是流戀于傳統審美理想,并試圖在新與舊中尋求一種統一調和。而因此產生的作品,只能是抒寫幽情單緒,追求險僻文字刁鉆古怪, 佶屈聱牙的“鬼趣”之作。這對明末文壇產生了極消極的影響。也正因此,竟陵派被正統文人斥之為“少有一知半見”的“詩妖”。
實際上,他們的幽情單緒,還是與個性自由解放思潮一脈相承的,代表的是失意的下層文人,以比較迂迴的方式表達了不滿現實的市民意識。沒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也沒有赤裸的嘻笑怒罵,他們只是沉潛到適合自己“性靈”的古人藝術境界中尋找慰安,悵望千秋。在強調學古人“真詩”的前提下,反對摹擬,提倡獨創性,根本目的即希望以兀然自立獲得個性的自由解放,但事實這是矛盾而無法調合的,竟陵派這種心緒是當時文人的普遍心理,唯其如此,竟陵文人以“鬼氣”、 “兵氣” “征兆國家之盛衰”的作品,才能“浸淫三十余年” “滔滔不返”,至明亡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