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羅望子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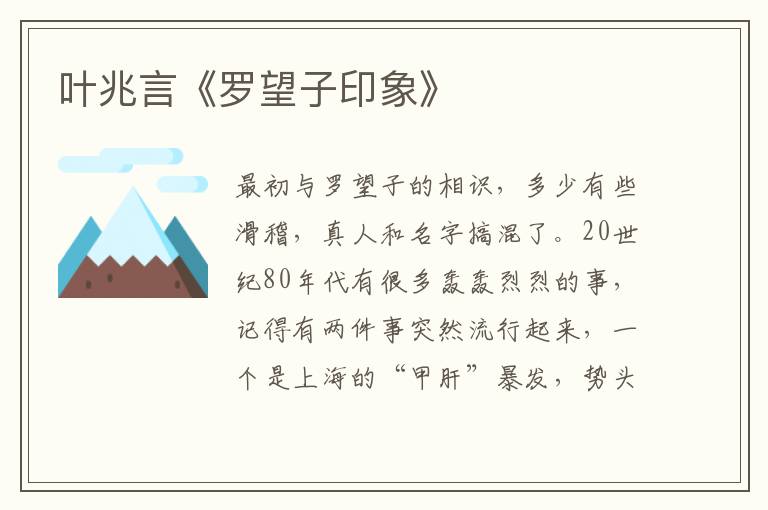
最初與羅望子的相識(shí),多少有些滑稽,真人和名字搞混了。20世紀(jì)80年代有很多轟轟烈烈的事,記得有兩件事突然流行起來,一個(gè)是上海的“甲肝”暴發(fā),勢頭兇猛,傳得有鼻子有眼,非常嚇唬人,一桌上吃飯,聽見上海口音就擔(dān)心。還有一個(gè)是新冒出一撥批評(píng)家,都是青年才俊,都是雙打選手,吳亮、程德培、張陵、李潔非、王干、費(fèi)振鐘、汪政、曉華,批評(píng)文章如雨后春筍,到處都是這幫家伙的文字。
當(dāng)時(shí)《雨花》在無錫開了一次筆會(huì),我作為文壇新人有幸參加,有幸遭遇一些當(dāng)紅的文學(xué)新星。王干和費(fèi)振鐘此前見過,不用介紹。大多數(shù)不認(rèn)識(shí),胡亂握手,汪政和羅望子是一起來的,我不知道汪政和曉華是一對(duì)夫婦,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那個(gè)與汪政一起過來的人,就是曉華。因?yàn)槠渌p打選手都是男的,根本沒想到還會(huì)有混合雙打。那時(shí)候,汪政和羅望子形影不離,很親密,都是蘇北的,都是同學(xué),都還有點(diǎn)兒稚氣未脫的學(xué)生模樣,王干和費(fèi)振鐘就是同學(xué)搭檔,我自以為是地認(rèn)定這兩人也是。
一錯(cuò)很多年,后來汪政夫婦到我們家來做客,才把這個(gè)結(jié)解開。羅望子的本名叫周誠,這個(gè)名字也讓人糾結(jié),跟他認(rèn)識(shí)又過了很多年,才知道這個(gè)本名。作家一旦用筆名成名,本名就是問題。甚至我寫這篇文章,也要再琢磨一下,才敢最后確定。毫無疑問,羅望子和周誠很容易引起混亂,拿稿費(fèi)和買機(jī)票必有麻煩。我們單位當(dāng)官的經(jīng)常換,我敢肯定,領(lǐng)導(dǎo)同志也會(huì)有跟我一樣的困惑。
第一印象往往會(huì)有錯(cuò)誤,首先是把名字搞混了。其次,是覺得這人老實(shí)。那次無錫會(huì)議,與會(huì)的青年批評(píng)家特別不老實(shí),一個(gè)個(gè)氣焰囂張,一個(gè)個(gè)咄咄逼人,都荷爾蒙過盛,都語不驚人死不休。上海的李劼、杭州的盛子潮、我們江蘇的王干和費(fèi)振鐘,還有汪政,不說是出口傷人,反正是已經(jīng)傷了人。那年頭剛流行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砍”,這幫家伙一個(gè)個(gè)都不是善茬兒,一個(gè)個(gè)不懷好意。可憐參加對(duì)話的諸位中年作家,本來還想聽番恭維,獲得幾句好話,結(jié)果風(fēng)馬牛不相及,被批評(píng)得鼻青臉腫,最后只能靠喝酒碰杯解決分歧。
印象中羅望子也是青年批評(píng)家一伙,基本上沒聽他說什么。當(dāng)然,我也沒說什么,在一個(gè)吵得一塌糊涂的會(huì)議上,要是你一點(diǎn)兒聲音都沒有,那么就等于沒參加這個(gè)會(huì)。所以我認(rèn)定那位被誤認(rèn)為是曉華先生的羅望子,是個(gè)很安靜的人,老實(shí)本分,文章寫得不錯(cuò),有一點(diǎn)兒內(nèi)向,有一點(diǎn)兒拘謹(jǐn),既老實(shí)又本分。
事實(shí)證明這些印象相當(dāng)不靠譜,根本對(duì)不上號(hào)。我們熟悉以后,想到了當(dāng)年就忍不住笑,什么安靜,什么內(nèi)向和拘謹(jǐn),包括老實(shí)本分,最多只有一點(diǎn)點(diǎn),基本上都用在了偽裝上。大家有機(jī)會(huì)一起打撲克,他總是欺負(fù)我水平低,看不入眼,一舉一動(dòng)都像是在調(diào)戲婦女,很不正經(jīng),很不嚴(yán)肅。因?yàn)橹焊邭鈸P(yáng)的激動(dòng),因?yàn)樘箘艙ヅ疲呐瞥3?huì)飛到桌子外面。跟他打牌,好像從來沒贏過,他贏了我也未必太高興,欺負(fù)是欺負(fù)了,對(duì)手太弱,勝之不武。
羅望子和荊歌同時(shí)進(jìn)入省作協(xié)創(chuàng)作組,平日里,一個(gè)生活在蘇北,一個(gè)生活在蘇南。晚輩總是要吃些虧,與蘇童和我相比,連作協(xié)房子他也沒分配到,社會(huì)主義的優(yōu)越性,到他們?yōu)橹拐f沒有就沒有了。這很像舊時(shí)大戶人家娶小妾,好丑不管,老少不論,先入一天為大,不服氣也沒辦法。事實(shí)上,我們真正見面的機(jī)會(huì)并不多,打牌的次數(shù)更少,雖然同一口鍋里吃飯喝湯,平心而論,說熟悉熟悉,說不熟悉真不太熟悉。他好像是能喝些酒,我不善飲,就算在一起喝酒聊天,也屈指可數(shù)。
其實(shí)我挺羨慕他不在南京,南京說起來是省城,是相對(duì)大的城市,省內(nèi)大多數(shù)作家都集中到此地。這種成群圈養(yǎng)未必就是創(chuàng)作的最好狀態(tài),未必就有利于作家寫作。寫作者還是孤獨(dú)一些好,最好沒有干擾。大隱隱于市,真是有能耐的高人,在鬧市也能寫出傳世的作品。我們都是些很普通的俗人,真要有可能隱居,真要靜下以來,徹底躲避都市生活的熱鬧,對(duì)寫作顯然更有幫助。
我一直在想,羅望子和在南京的作家們寫的東西明顯不一樣,是否與他獨(dú)特的生活環(huán)境有關(guān)。他依然堅(jiān)持生活在蘇北縣城,寫自己喜歡寫的文章,讀自己喜歡讀的書。時(shí)至今日,經(jīng)濟(jì)生活高度發(fā)展,有了銀子,有了聲望,在哪都一樣,在哪都可以牛氣。天高皇帝遠(yuǎn),作為當(dāng)?shù)氐奈幕耍谀侨玺~得水,進(jìn)退自如,活得很瀟灑,早已自成了一方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