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李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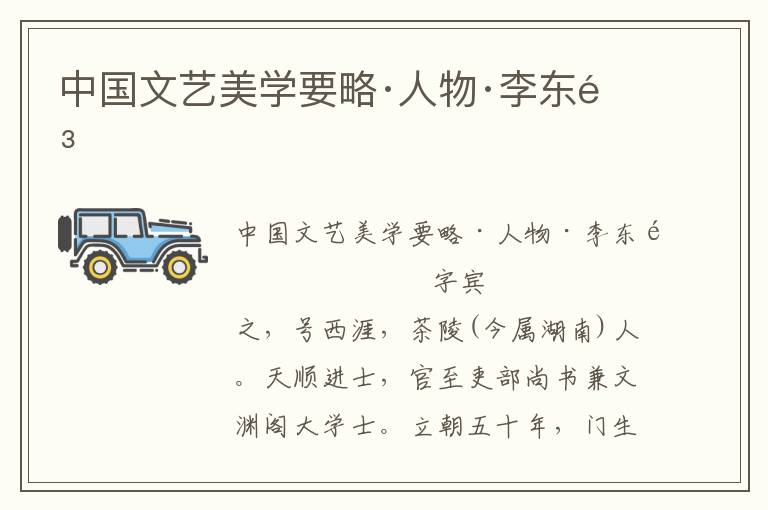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李東陽
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今屬湖南)人。天順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立朝五十年,門生眾多,以宰臣地位領袖文壇,是明七子前反對“臺閣體”的大宗派,“茶陵派”首領。著有《懷麓堂集》,內有《詩話》一卷。
由于處在“臺閣體”與七子的歷史轉變過程中,其文學主張亦帶有過渡的色彩,既有因襲“臺閣體”的一面,亦有倡導宗唐復古的一面。他不滿以點綴升平為能事,且又雍容典雅、平庸呆板的“臺閣體”,但其加以糾正的正面主張卻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極力提倡以唐為法,以杜為宗。在此同時,又簡單否定了唐以外各個時代詩歌的成就。他的宗唐宗杜,并非學其以詩反映現實生活,而僅是從形式著眼,對唐詩的尊崇也在音律節奏方面。他在《詩話》中說: “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學也。”從這出發學杜,自然只得皮毛,不得其神髓。李的形式主義宗唐法杜的觀點,直接影響了七子的復古主義理論。王世貞說: “長沙(李東陽)之于何(景明)、李(夢陽),其陳涉之啟漢高乎。”李東陽創作上講“法度”, “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七子則侈談“法度”。但李雖力主宗唐法杜,卻反對機械摹擬,這與七子的復古模擬論又有所不同。
另外,李東陽論詩,也有一些精辟的見解。其一,他強調詩歌創作中音樂美的重要性,認為原始詩歌的產生最初是與樂合而為一的。“樂始于詩,終于律。”詩是樂的歌詞,歌詞不能離開“樂”而存在。對“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作了進一步發揮和闡述。其二,他繼承了柳宗元關于詩不同于一般哲理文章的見解,并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認為“詩與文不同體”, “詩與文各有體,而每病……不能相通”。詩與論說文不同在“暢達情思,感發志氣。”這較好地說明了詩與文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