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族主義文藝”的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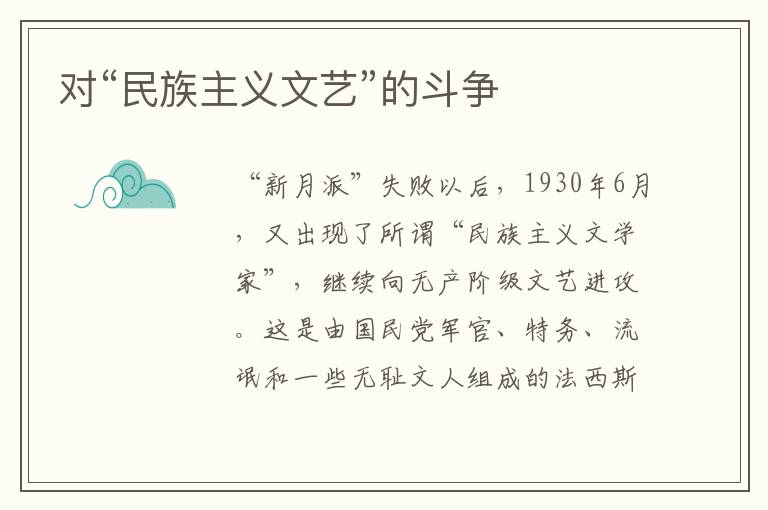
“新月派”失敗以后,1930年6月,又出現了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繼續向無產階級文藝進攻。這是由國民黨軍官、特務、流氓和一些無恥文人組成的法西斯主義的文學團體。它的主要成員有王平陵、朱應鵬、傅彥長、范爭波、黃震遐、潘公展等。他們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等刊物。他們在請人起稿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中叫嚷:“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他們妄圖用所謂“民族意識”來抹殺和取代階級意識,以取消階級斗爭。他們說:“在中國目前來鼓吹階級斗爭,實在不是中國所需要的”,而應努力于“文藝上民族意識底形成”。
針對“民族主義文學家”的反革命叫囂,瞿秋白、茅盾、魯迅等人先后寫文章與之斗爭。瞿秋白在《屠夫文學》中斥“民族主義文學”為“鼓吹殺人放火的文學”,暴露了他們的法西斯主義面目。茅盾寫的《“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逐一駁斥了“民族主義文藝”的“根據”,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和淺薄無知。魯迅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等文章,更深刻地揭露了“民族主義文學家”的階級本質和民族敗類的丑惡面目。魯迅首先指出,這些“民族主義文學家”,其實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保護和養育的“流氓”、“奴才”和“鷹犬”,他們的職責和任務是:“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分的‘莠民’。”他們“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目的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因此,他們提倡的“民族主義文學”,其實是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效勞的“寵犬文學”。
魯迅還通過對“民族主義文學家”的幾篇作品的分析,徹底暴露他們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和賣國主義的本質。黃震遐在他們參加軍閥戰爭后寫的小說《隴海線上》中寫到,他一到夜晚就有“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里與阿拉伯人爭斗流血的生活”的感受。魯迅抓住這一自我暴露的文字斥責道:“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并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么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么倒稱‘民族主義’,來蒙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象是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這就徹底暴露了這些民族敗類的可憎面目。在魯迅等人的有力批判和打擊下,“民族主義文學”這一“沉滓”很快就潰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