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文藝美學(xué)要略·論著·《答吳武陵論非國(guó)語(y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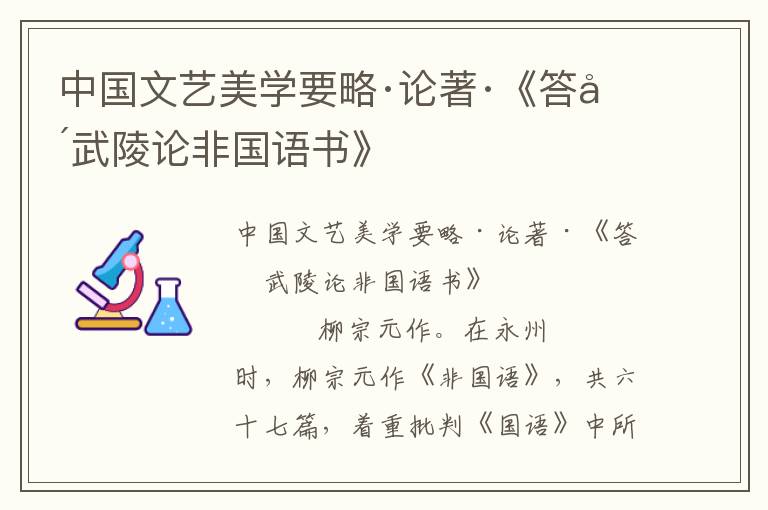
中國(guó)文藝美學(xué)要略·論著·《答吳武陵論非國(guó)語(yǔ)書》
柳宗元作。在永州時(shí),柳宗元作《非國(guó)語(yǔ)》,共六十七篇,著重批判《國(guó)語(yǔ)》中所反映的天命迷信和維護(hù)貴族特權(quán)等觀點(diǎn)。本篇是他就吳武陵對(duì)《非國(guó)語(yǔ)》一書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所作的回答。其主要內(nèi)容有以下幾點(diǎn)。
首先,他重視文學(xué)的經(jīng)世致用作用,但承認(rèn)文學(xué)的作用是有限的, “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wù)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這是他宦海浮沉,幾經(jīng)滄桑,特別是改革失敗被貶永州后的沉重的反思。
其次,柳宗元又認(rèn)為,盡管不能對(duì)文學(xué)的作用抱太大的奢望,但是畢竟仍須勉力為之,盡量使之有用。“故在長(zhǎng)安時(shí),不以是取名譽(yù),意欲施之事實(shí),以輔時(shí)及物之道”。這里的“施之事實(shí)”和“輔時(shí)及物之道”,說(shuō)得淺近一些,就是要求寫文章要經(jīng)世致用,切中時(shí)弊,有益于時(shí)代和社會(huì)。由此可見,雖然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yùn)動(dòng)都重視“文”與“道”的關(guān)系,但柳與韓的“道”還是有所區(qū)別的。柳之“道”雖也以《書》、 《詩(shī)》、《禮》、 《春秋》、 《易》等五經(jīng)為其“取道之原”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但他更注重文章所反映的現(xiàn)實(shí)內(nèi)容,即本篇中所謂的“輔時(shí)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后”。這一后,在他的《報(bào)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的“道之及,及于物而已耳”;和《與楊海之第二書》中的“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也?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jì)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wú)以為大者也”;都可以作為印證。
第三,由此出發(fā),柳宗元激烈地反對(duì)不切合實(shí)際而徒具形式的作品。他說(shuō):“夫?yàn)橐粫瑒?wù)富文采,不顧事實(shí),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后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井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他反對(duì)“文勝質(zhì)”并不等于不要文。 “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本篇中還流露出“不愿為人師”的情緒,與《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是一致的。
總之,這篇文章是柳宗元對(duì)文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之談,其中對(duì)文學(xué)作用的估價(jià)和要求文學(xué)有內(nèi)容、反對(duì)徒具文采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