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元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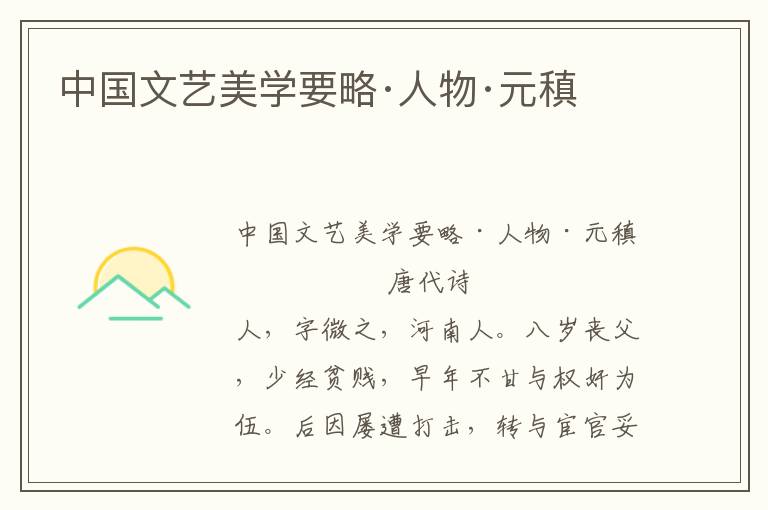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元稹
唐代詩人,字微之,河南人。八歲喪父,少經貧賤,早年不甘與權奸為伍。后因屢遭打擊,轉與宦官妥協,官至宰相,因妒讒裴度遭貶,死于武昌節度使任所。
元稹既有創作,又有理論,他的政治態度和文藝美學主張與白居易都很相近,是白居易的詩友,也是新樂府運動的中堅, 世人并稱“元白”。白居易提倡詩歌要為時、為事而作,元稹強調詩歌必須發揮“諷興”、“美刺”的作用,反對因襲模仿。他在《樂府古題序》中說: “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于文或有短長,于義咸謂贅剩,尚不如寓義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他自己也按照“諷興當時之事”的原則進行創作。他編選和唱和的樂府新作,“雖用古題全無古義”,這種創作實踐與他對當時黑暗社會的強烈不滿是一致的。
在唐代詩人中,元稹特別推崇杜甫,元、白的新樂府是和杜詩的影響分不開的。元稹所以對杜甫給予極高的評價,主要是他認為杜甫有創新精神,學習古人又決不依傍古人,即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他特別推重杜詩中的《悲陳陶》、 《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等,說它們“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旁”。在這些方面,元稹的理論代表了當時進步詩人的主張。但元稹在推重杜甫的同時,卻貶抑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說李白“不能歷其藩翰”,是“以奇文取稱”。這種看法當然是偏激的,說明他既沒有理解李白詩的積極意義,更沒有理解李詩的藝術特色,他只是從詩的形式著眼,評論李、杜的高下。后來元好問曾寫詩譏諷他說: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碔砆。”碔砆,石之似玉者。元稹所推崇杜甫的長篇排律,不過是詩中一體,在杜詩中也未必是上乘。可見他的審美標準是有問題的。元好問以此譏諷元稹的偏激不妥,還是中肯的。
元稹也曾大力推重政治諷諭詩,并且批評過南朝詩詞的“淫艷刻飾、佻巧小碎”的文風, 自我標榜說他的諷諭詩“詞直氣粗,固不敢陳露于人”等,而在實際上卻常常并不如此。特別是當他官居高位時,生活空虛,心滿意得,應酬唱和不過是附庸風雅,已經失去了他先前的銳氣,實質上是助長了詩歌的形式主義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