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一曲為誰吟——《圓圓曲》中對吳三桂的評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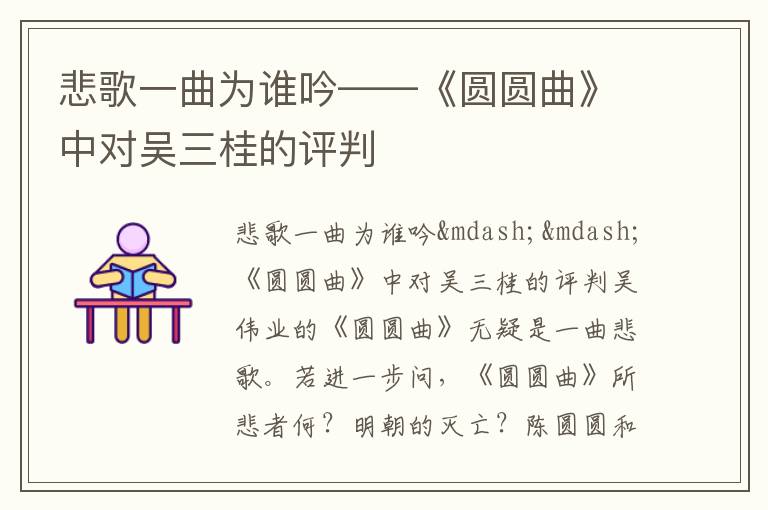
悲歌一曲為誰吟——《圓圓曲》中對吳三桂的評判
吳偉業的《圓圓曲》無疑是一曲悲歌。若進一步問,《圓圓曲》所悲者何?明朝的滅亡?陳圓圓和吳三桂亂世中的傳奇人生?人性的悲哀?人生的無奈?世事的無常?似乎都是。這里想仔細討論一下,何為“詩核”?
以明朝滅亡、明清之際的戰亂為背景,描述陳圓圓和吳三桂的悲歡離合,是《圓圓曲》的基本線索。其中有個人的身世之嘆,更有國家的興亡之感。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人們說起明朝的滅亡,還會扼腕頓足,感慨萬端。偶然?必然?進步?倒退?英豪?罪人?崇禎皇帝、多爾袞、李自成、吳三桂……往前追溯還有努爾哈赤、袁崇煥、洪承疇、皇太極……親身經歷這場歷史劇變的吳偉業,其感受想必沒有這么復雜,但一定無比強烈。他對明朝滅亡的痛惜、哀悼、還有悲憤,應該說,都投入到那一首首委婉、哀怨、優美的“梅村體”詩中,《圓圓曲》是其中的代表。
(一)心曲難言 機鋒暗藏
不過,我們從《圓圓曲》中并看不到吳偉業對明朝滅亡表達出強烈的情緒。這并不奇怪,原因是《圓圓曲》大約作于清朝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
吳偉業選擇了一個獨特而引人入勝的視角,那就是明末蘇州城色藝超群的名伎陳圓圓。在明末的江南,名伎如云。人們之所以對陳圓圓給予更多的關注,還是因為她與吳三桂的關系。吳三桂在明清鼎革中,實在是個舉足重輕的人物。大明王朝從衰落到滅亡,無論有多么長的“積弱”過程,有多少個必然和偶然的原因,最后壓倒駱駝的那根稻草是吳三桂。吳三桂打開了清軍多年無法打開的山海關大門,讓清兵長驅直入進入了李自成扔下的北京城。
《圓圓曲》沒有從清軍入關寫起,而以李自成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煤山開頭:“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整體風格委婉的《圓圓曲》,有這樣一個悲壯而有氣勢的開頭。這幾句詩意思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吳三桂聞訊給崇禎皇帝戴孝、全軍痛哭。他之所以降清,打開山海關的大門,引清兵入關,是因為陳圓圓被李自成手下的人搶奪。“沖冠一怒為紅顏”一句詩是全詩最為膾炙人口的名句,后人引用率很高。從表面上看,這句詩是說吳三桂降清的原因,實際上誰都知道,吳三桂降清的原因、過程和背景十分復雜,吳偉業當然也很清楚。他的《綏寇紀略》一書,即記載了李自成起義軍的事。他對明末的局勢有較深的了解和思考。所以,這句詩另有深意。
先看看吳三桂降清的大體過程:明朝滅亡前,明朝廷、李自成和清軍三方面力量已經抗衡了好多年。在明朝滅亡的前兩年,即崇禎十五年,明朝廷守衛錦州的那場戰爭,在持續了近兩年之后,明軍失敗。明朝的幾個重要的大將,像薊遼總督洪承疇(當時守松山)、祖大壽(守錦州)等,先后被俘,投降清軍。從那以后,身為遼東總兵的吳三桂退守寧遠(現在的興城,位于山海關之外往東北方向兩百里處)。錦州失守后,寧遠成為山海關外對清軍唯一的邊防重鎮,而吳三桂,是鎮守東北邊防唯一有戰斗力的大將。重擔在肩,吳三桂能救明朝嗎?事實是,吳三桂并不是一個性格剛烈的人,他的態度隨著三方面力量的消長而變化。郭沫若在1944年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里認為,吳三桂是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到北京近郊時,崇禎下令讓吳三桂放棄寧遠,率軍來保衛北京。吳三桂帶著他的軍隊,還有追隨他的百姓共五十萬人,日行五十里往北京趕。三月二十日到達豐潤(永平),當吳三桂得知李自成已進入北京(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進北京),便停止了進軍。約三月底,李自成派明朝降將唐通招降吳三桂,吳三桂考慮當時的形勢,表示答應。實際上,當時吳三桂已經進入李自成的勢力范圍,他沿途發放不擾民的告示。趙詒琛、王大隆輯《辛巳叢編》記:“從關上至永平,大張告示,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告示中稱李自成為“新主”,實際吳三桂已投降李自成。
后來,吳三桂聽說其父吳襄被李自成拷問追贓,改變了主意。在李自成占據北京的四十二天里,李自成住在皇宮,他的將領各住一座貴族的大宅院,把明朝的官員分別關押在這些宅子里拷問要錢。有記載說李自成向吳三桂的父親要二十萬兩銀子,作為軍餉。吳襄只湊足了五千兩。吳三桂突然帶兵返回山海關,號稱借清兵十萬打李自成,為君王和父親報仇。有學者認為是李自成在北京追贓的錯誤政策,讓吳三桂看出李自成難成大事,才改變了主意。當時許多被李自成關押考問過、活著出來的明朝官員寫了回憶甲申之變的文字,如趙士錦的《甲申紀事》、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等,記載李自成在北京時的情況。早先的這類書中并沒有關于陳圓圓的記載。后出的一些書里才增加了陳圓圓被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搶掠、吳三桂得知后大為惱火的記載。以后的正史《明史》和《清史列傳》都采用了這種說法。
吳三桂降清的過程大致如此,可說明《圓圓曲》里寫吳三桂因陳圓圓被搶而引清兵入關,是吳偉業的曲筆。在當時,說吳三桂為一個風塵女子叛國降清,對吳三桂是一種貶斥和譴責,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寫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對明朝遺老來說,是譏刺吳三桂降清;對清朝官方來說,因為吳三桂后來又叛清,在云南自立為王,在湖南衡陽自封為帝,這種說法也是在貶責吳三桂的人格。實際上,陳圓圓對整個大局不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那時,歌女舞伎是有錢人互相贈送的禮物,拿錢即可以買到,當時身居要職的吳三桂,不至于僅為一個歌女而大動干戈。也就是說,“沖冠一怒為紅顏”是全詩譏刺吳三桂最為重要的一句,所以,最為后人注意和肯定。
詩中對吳三桂的譏諷還有兩處,其一,第六十七至七十句:“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裝照汗青。”吳三桂率領清軍入關后,多爾袞命吳三桂往西北追擊李自成。吳三桂與李自成交戰,最終李自成敗于一片石。李自成一怒之下,殺吳三桂之父吳襄及全家三十余口。這四句詩說,女子原本不應對國家興亡起決定作用,但是“英雄多情”,吳三桂感情用事,因陳圓圓而草率行事,使得父親及全家被殺,而讓陳圓圓名留青史。這幾句詩對吳三桂的譏諷應該算是辛辣的。
其二,全詩的最后八句:“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烏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寫吳王夫差與西施的故事,暗喻吳三桂和陳圓圓。當年吳王寵愛西施,在館娃宮過著豪華的生活。可是沒過多久,吳國滅亡,吳宮荒廢,人去樓空。當年吳王為西施修建的響屧廊,因為斯人去矣,“響屧”不再,雜草叢生,唯余“苔空綠”。接下來的四句詩是:“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入清后,吳三桂被封為平西王。當時吳三桂的藩府在陜西漢中的南鄭,那里就是瀕臨漢水的古梁州。這四句詩的意思是,雖然現在吳三桂和陳圓圓過著“珠歌翠舞”的奢華生活,但是這些不會長久。“漢水東南日夜流”用李白《江上吟》詩意,《江上吟》有詩句曰:“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此處換了一種說法:漢水永遠只會向東南流,也即說吳三桂的功名富貴根本不可能長久。
如果是時過境遷、塵埃落定,這樣諷刺吳三桂,也許并不稀奇。而吳偉業寫《圓圓曲》時,吳三桂風頭正勁,是威震一方的平西王,正在陜西、四川一帶和抗清勢力打仗。吳偉業并沒有看到吳三桂的結局。他比吳三桂大三歲,比吳三桂早死七年。在《圓圓曲》里直截了當地說吳三桂為陳圓圓叛國降清、富貴榮華不可能長久,確是這首詩的鋒芒所在。所以當時有傳說,吳三桂看了《圓圓曲》,覺得大失面子,出高價讓吳偉業毀版,不讓《圓圓曲》流傳,被吳偉業拒絕。
無論如何,今天讀《圓圓曲》,會覺得吳偉業對吳三桂的譏刺很是溫和委婉,但回到吳偉業的環境里,可以體會到他的難言之隱。
(二)身世之嘆 家國之悲
《圓圓曲》中更加難以言說的是對逝去的明朝的追思和對死去的崇禎的哀悼。作為一個傳統文人,吳偉業對明朝滅亡不可能無動于衷。何況在明末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初出茅廬時就受到崇禎皇帝的恩遇。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吳偉業會試高中榜首,立刻卷入了一場政治斗爭。因為當時的首輔兼主考官周延儒和他父親交情頗深,所以他會試中會元后,馬上有人參劾周延儒舞弊。最后周延儒把矛盾上交到崇禎皇帝那里,崇禎對吳偉業的會試試卷給予了肯定,使他不僅得以順利參加隨后的殿試,并在殿試中得中榜眼(一甲第二名),從而踏上仕途。此后,吳偉業難以忘懷崇禎皇帝的知遇之恩。
《圓圓曲》中的家國之悲和興亡之嘆,隱含在對詩歌主人公的身世之嘆背后,也即蘊含在吳三桂和陳圓圓活動的背景里。“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這是《圓圓曲》開篇的四句,前面著重談論的是第四句。前三句寫得十分悲痛,詩意為:那天崇禎皇帝在絕望中棄世,吳三桂從山海關趕到北京,打敗李自成。吳三桂率領的遼東鐵騎全軍為崇禎戴孝痛哭。雖然描寫的是吳三桂這個人物出場的背景,可是渲染出了國破家亡的悲痛氣氛。
接下來的四句詩,角度一轉,以吳三桂自述、自我辯解的口氣,說他引清兵入關,并不是因為陳圓圓,而是為了消滅“逆賊”李自成,給君王和父親報仇:“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李自成占據北京時,曾讓吳三桂之父吳襄招降其子,吳三桂看到了父親的信,得知其父在北京被李自成拷打逼餉,拒絕了李自成的招降。詩里用吳三桂的口吻說,等打敗了李自成,哭罷了君王和父親,才和陳圓圓相見。這幾句詩的用意很微妙,似乎詩人覺得說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太過尖銳,來了一個回旋,讓吳三桂自己解釋了一番。這幾句詩也渲染出了亡國的悲痛氣氛。
當然,如詩題所示,詩中大部分筆墨,是寫陳圓圓的身世,寫她與吳三桂在戰亂中的分分合合的曲折經歷。“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這四句詩描述陳圓圓初次見到吳三桂的情形。陳圓圓和吳三桂相見,大約是在田弘遇家。田弘遇是崇禎的寵妃田妃的父親,在當時的北京城十分顯赫。陳圓圓和吳三桂相識大概是在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也即明朝滅亡的前一年。這一年,朝廷命大學士周延儒督軍,會合薊州、永平、通州等八鎮兵將,抗擊清軍于螺山(今懷柔縣北)。八鎮兵士不戰而逃,只有吳三桂從寧遠率兵入關,在灰嶺(昌平縣北)打敗清軍。五月十五日,崇禎皇帝接見吳三桂和山東總兵劉澤清、山海關總兵馬科,設宴于武英殿。吳三桂大概就是在這次進京期間,在田弘遇的一個家宴上,認識了陳圓圓。田弘遇當時有意結交吳三桂等顯要,因為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田貴妃死去,田弘遇需要交結權豪勢要保護自己。大概在這次宴會上,田弘遇答應把陳圓圓嫁給吳三桂。這幾句詩寫的就是田弘遇愿將陳圓圓許配吳三桂,只等吳三桂來娶了。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弦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撿取花枝屢回顧。”這四句詩具體描寫吳三桂在宴會上見到陳圓圓的情形:一個是將軍年少,意氣風發;一個是少女懷怨,色藝超群。二人頻頻相顧,兩情相悅。崇禎十六年,吳三桂只有三十一歲,所以是“白皙通侯最少年”。如果沒有戰亂,一個美女和英雄的故事,也許就此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但國難當頭,他們的命運注定波折迭起。“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后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娥眉匹馬還?”這十二句詩寫吳三桂和陳圓圓定情以后,本打算早些把她娶回家。但是軍情緊急,朝廷催促吳三桂回寧遠。于是,沒來得及娶走陳圓圓,吳三桂自己回到遼東前線,把陳圓圓留在了北京。沒成想就在吳三桂離開后,李自成占領了北京,他的部將在京城到處搜尋陳圓圓。陳圓圓本是訂了婚的人,這些人把陳圓圓當成一般的歌妓搶去了。如果不是吳三桂后來打敗李自成,陳圓圓不可能回到他的身邊。
“娥眉馬上傳呼進,云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這幾句寫吳三桂追擊李自成至山西,不知遠在京城的陳圓圓的生死存亡。他的部將在北京城找到陳圓圓后,立即飛騎傳信。吳三桂聞訊,結彩樓,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迎接。詩中描寫陳圓圓在戰場上見到吳三桂時的情形,嬌媚萬分:“云鬟不整”“啼妝滿面”,頭發散亂,滿臉淚水。“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云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寫吳三桂接著往陜西方向去追打李自成,陳圓圓隨行。
“錯怨狂風飏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這兩句似乎是詩人對陳圓圓的命運的評論:陳圓圓一定抱怨過自己像在狂風中飄揚的落花,飽受顛沛流離之苦,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可是,這抱怨是錯的。因為最終她看到了“無邊春色”,享受到了她一直向往的美好愛情和富貴榮華。的確,如果僅僅只是經歷亂離,若能兩心相知,患難與共,最終柳暗花明,苦盡甘來,對相愛的男女來說也不失為一種美好的境界。
可是,全詩最后又落腳在吳三桂身上。《圓圓曲》中有一段描寫陳圓圓發達后、消息傳到她的家鄉蘇州的情形:“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陳圓圓讓她早年的蘇州同伴艷羨不已的好運,就是她“飛上枝頭變鳳凰”“夫婿擅侯王”,嫁給了吳三桂。在陳圓圓早年同伴的眼里,她算是到達了世俗人生理想的頂端。她所擁有的“無邊春色”,她所得到的榮華富貴,她讓人羨慕不已的好運,都是吳三桂給予她的。那么,吳偉業真的認為陳圓圓交了好運、值得羨慕嗎?答案是否定的。上面曾談到,《圓圓曲》的最后,詩人對吳三桂的“成功”,對他所擁有的地位和財富,給予了無情的否定,實際也是對陳圓圓所遇到的“好運”的否定。
吳偉業同樣不是個性情剛烈的人。明亡后,他曾想自盡,被家人攔下。他沒有參加當時一些江南文人的抗清活動。他的一些親朋好友,在明清交替之際遭遇了殺身之禍,或者被流放。他能全身而退,兩代皇帝都待他不薄,可看出他小心謹慎的性格。入清后,他在無奈之下做了清朝的官。雖然只做了三年多,但讓他痛悔終生。所以,吳偉業在《圓圓曲》中表達出十分復雜的情感。其復雜性在于,詩中對于吳三桂在譏刺的同時,實際有某種程度的理解;在通過詩歌主人公的身世之嘆表達亡國之痛的同時,流露出對世事的無奈。《圓圓曲》的最后,詩人超越了歷史的具體性,超越了現實,道出了人生普遍的哲理。所以,雖然詩人沒有看到吳三桂的結局,但他言中了。
總體上說,吳偉業這位親身經歷了朝代更迭的作家,其《秣陵春》傳奇,因是描寫南唐的歷史故事,抒發故國之思很是委婉。可是即使是描寫明末故事的作品,如《圓圓曲》等,也沒能痛快淋漓地表達追懷故國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