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張讓傳》譯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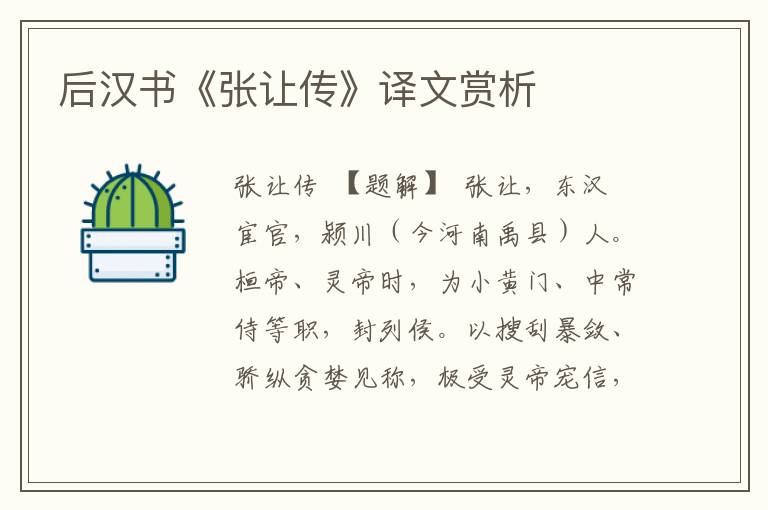
張讓傳
【題解】
張讓,東漢宦官,潁川(今河南禹縣)人。桓帝、靈帝時,為小黃門、中常侍等職,封列侯。以搜刮暴斂、驕縱貪婪見稱,極受靈帝寵信,常謂“張常侍是我父”。中平六年(189),何進謀誅宦官,事泄,張讓和其余幾個常侍設(shè)計伏殺何進。袁紹、袁術(shù)等人聞何進被殺,入宮盡殺宦官,張讓等人挾靈帝出逃,至黃河,走投無路,投水而死。
【原文】
張讓者,颎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者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xiāng)侯。延熹八年,黜為關(guān)內(nèi)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并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jié)、王甫等相為表里。節(jié)死后,忠領(lǐng)大長秋[1]。讓有監(jiān)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2],威形喧赫。扶風人孟佗,資產(chǎn)饒贍,與奴朋結(jié),傾謁饋問[3],無所遺愛[4]。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shù)百千兩,佗時指讓,后至,不得進,監(jiān)奴乃率諸倉頭[5]迎拜于路,遂共輿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于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賤,為人蠹害[6]。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jù)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注釋】
[1]大長秋:長秋宮是漢朝皇后居住之所在。大長秋是皇后所用的官屬的負責人,一般由宦官擔任。
[2]交通貨賂:交結(jié)賄賂。
[3]傾謁饋問:巴結(jié)逢迎,用財物賄賂。
[4]無所遺愛:對自己所愛的東西都不保留。
[5]倉頭:奴仆,下人。
[6]蠹(dù)害:殘害。
【譯文】
張讓是潁川(今河南禹縣)郡人,趙忠是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他們少年時都在宮廷中做事,桓帝時任小黃門。趙忠因為參加誅殺梁冀有功,封都鄉(xiāng)侯。延熹八年,黜為關(guān)內(nèi)侯,食本縣租千斛。在漢靈帝的時候張讓、趙忠一同升為中常侍,被封為列侯。與曹節(jié)、王甫等人內(nèi)外一氣。曹節(jié)死去之后,趙忠兼任大長秋。張讓用監(jiān)奴主管家務,勾結(jié)權(quán)貴,收受賄賂,威名很大。扶風人孟佗,家產(chǎn)富足,同張讓的監(jiān)奴結(jié)為朋友,竭自己所有送給監(jiān)奴,沒有剩下一點自己所愛的東西。監(jiān)奴感激他,問孟佗:“您有什么要求呢?我都能為您辦啊。”孟佗說:“我只希望你們?yōu)槲野菀姀堊屝袀€方便而已。”當時請求見張讓的賓客很多,常常在門口停著成百上千輛的車子。孟佗那時也去見張讓,因為后到,不能進去,監(jiān)奴就率領(lǐng)奴仆在路上迎拜孟佗,并且共同抬著他的車子進門。賓客們感到十分驚奇,認為孟佗和張讓很相好,都爭相拿來珍寶奇玩去賄賂他。孟佗分一些給張讓,張讓很高興,于是就讓孟佗做了涼州的刺史。
就在這個時候,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都任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子兄弟分布州郡當官,貪污殘暴,成為老百姓的禍害。黃巾軍造反,盜賊就如同開了鍋的粥一樣。郎中中山張鈞上書說:“我想張角之所以能夠興兵作亂,成千上萬的人希望能跟著他,其根源都在十常侍把他們的父兄、子弟、親戚、賓客放到各州郡,獨占財利,侵奪百姓,百姓的冤屈無處申訴,所以圖謀不軌,聚積成為盜賊。應該殺了十常侍,把他們的腦袋懸掛南郊,以此來向老百姓請罪。再派使者布告天下,這樣可以不須用兵,而大寇自會消散。”
【原文】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7]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并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獨發(fā)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
明年,南宮災[8]。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fā)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于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diào)[9],百姓呼嗟[10]。凡詔所征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11],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余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后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注釋】
[7]徒跣:赤著腳。
[8]南宮災:南宮發(fā)生火災。
[9]私調(diào):私自搜刮。
[10]呼嗟:呼天搶地。
[11]騶:武騎士。密約敕:秘密帶著敕令。
【譯文】
皇帝把張鈞的奏章給張讓等人看,他們都脫掉帽子、靴子叩頭前來請罪,乞求讓自己去洛陽監(jiān)獄,并且拿出家財以助軍費。皇帝詔令他們都戴上帽子,穿起靴子,和以前一樣工作。皇帝對張鈞發(fā)怒說:“你真是一個瘋子啊!十常侍中竟然沒有一個好的嗎?”張鈞又上書,還是同上次的奏章一樣。但總是被扣壓不上報。皇帝下詔廷尉、侍御史調(diào)查參加張角太平道的人,御史秉承張讓等人的意旨,誣告張鈞學黃巾道,把他逮捕,拷打他,死在獄中。而張讓等人卻與張角勾結(jié)往來。后來中常侍封谞、徐奉與黃巾勾結(jié)的事敗露被殺,皇帝因此發(fā)怒責問張讓等人說:“你們常說黨人圖謀不軌,下令禁錮,有的還被殺掉,現(xiàn)在黨人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你們反與張角私通,這該不該殺?”張讓等皆叩頭道:“這是前中常侍王甫、侯覽干的。”皇帝于是就不再追究了。
在第二年,南宮遭遇大火。張讓、趙忠等人勸皇帝下令收天下田地稅每畝十錢,用以修建宮室。征調(diào)太原、河東、狄道各郡的木材和有花紋的石頭,每當州郡把這些東西送到京師,黃門常侍總是下令譴責呵斥說這些木石不合格,并且強行折價,賤價收買,十分的只給一分的價錢,又把它賣給宦官,宦官又不馬上接受,木材因而堆積腐朽,宮室連年修不成。刺史、太守又私自增加征調(diào)的數(shù)量,百姓呼號嘆息,苦不堪言。凡是皇帝征求的東西,都派西園中的騎士秘密帶著皇帝的命令,號稱“中使”,恐嚇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的提拔任用,都責令出助軍需和修宮室錢,大郡到二三千萬,剩下的各有差別。應當上任的人,都必須先去西園評定價值,然后才去。有的錢交不夠,甚至自殺。那些保持清白的人請求不去上任,都被強行派去。
【原文】
時鉅鹿太守河內(nèi)司馬直新除[12],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愴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nóng)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臧,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shù)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者得志,無所憚畏,并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外,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shù)歉撸歉邉t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于倉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懸)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zhuǎn)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13],旋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余日罷。
【注釋】
[12]新除:剛剛調(diào)任為官。
[13]翻車:是一種刮板式連續(xù)提水機械,又名龍骨水車,是我國古代最著名的農(nóng)業(yè)灌溉機械之一。渴烏:為曲簡,以氣引水上也。
【譯文】
當時新任命的巨鹿郡太守河內(nèi)郡人司馬直,因有清名,減少一些,責令交三百萬。司馬直接到詔令,惆悵地說:“為人民父母,反而搜刮百姓,以滿足當今所需,我心不忍啊!”托病辭官,上面不準。走到孟津,上書盡力陳述當世的過失,古今禍敗的教訓,然后吞藥自殺。書奏上后,皇帝為此暫時停征了修宮錢。
又建萬金堂于西園,取司農(nóng)的金錢繒帛,滿積其中。又回到河間買田地住宅,建造宅第樓觀。靈帝本是侯爵出身,素來貧窮,常常嘆息桓帝不能置家業(yè),所以聚斂金錢財物作為私產(chǎn),又收存了小黃門常侍的錢各數(shù)千萬。靈帝常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畏懼,大家仿照宮室營造私人住宅。靈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怕他看見自己的住宅,就使中大人尚但勸皇帝說:“天子不應當?shù)歉撸歉撸习傩站鸵撋ⅰ!被实蹚拇瞬辉俚峭づ_樓閣。
第二年,就派鉤盾令宋典修繕南宮玉堂。又派掖廷令畢嵐鑄造四個銅人排列在蒼龍、玄武宮前。又鑄了四座鐘,可容二千斛糧食,懸掛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zhuǎn)水流入宮內(nèi)。又造翻車渴烏,安放橋西,用來噴灑南北郊道路,以節(jié)省百姓灑道路的費用。又鑄四出文錢,錢上都有四道和邊輪相連的花紋。懂得的人私下議論說,奢侈暴虐已經(jīng)到了極點。形象征兆出現(xiàn),這種錢鑄成,一定要四方流散。等到京師大亂,這種錢果然流散四海。又任用趙忠為車騎將軍,百多天免職。
【原文】
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shù)十人劫質(zhì)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yè)絕宗禋[14]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15]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16]自外戚失祚,東都[17]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于釁起宦夫[18],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謝全生,聲榮無輝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nèi)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
亦有忠厚平端,懷術(shù)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茍恣兇德,止于暴橫而已。然莫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19]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fā)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跡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注釋】
[14]宗禋(yīn):宗廟。
[15]嬖色:寵幸美色。
[16]西京:指西漢。
[17]東都:指東漢。
[18]釁起:罪孽發(fā)生于。宦夫:宦官。
[19]迷瞀(mào):迷惑。瞀:目眩,眼花。
【譯文】
中平六年(189),漢靈帝駕崩,中軍校尉袁紹勸大將軍何進下令殺宦官,用這種行為博取天下人高興。不料謀劃泄露,張讓、趙忠等人乘何進入宮之際,共同殺了何進。隨后袁紹率兵殺了趙忠,搜捕宦官,無論老小,統(tǒng)統(tǒng)殺掉。張讓等幾十人劫持天子作為人質(zhì)逃到黃河邊上,追趕得急迫,張讓等人哭著向天子告辭說:“如果我們滅絕,天下就會大亂!希望陛下您自愛啊!”說完,都投河自殺了。
史官評論說:自古喪國滅宗的,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慢慢地造成的。夏商周三代因好色取禍,秦始皇因奢侈暴虐招害,西漢由于外戚而亡,東漢以宦官失國。成敗之來,以前史籍議論得很多啊。至于禍起宦官,大略還有可以討論之處。為什么呢?宦官這種人,他們與普通人不同,名聲不好,不是出身于貴族大家。肌膚血氣不能傳于后代,表面上看不出他的壞處,做事容易取得信任,加以在朝廷里見多識廣,熟悉典章制度,所以年幼的君主,依靠他謹慎練達的長處,皇后喜歡他出入聽命方便。察訪他沒有猜疑忌憚的心思,接近他有可喜的顏色。
也有忠厚正直,懷術(shù)糾正邪惡的;有敏于應對,弄巧亂實的;還有借譽于忠良,先期引譽的。不都是放肆為兇,只是一味橫暴而已。然真假并行,貌似忠誠,情實奸惡,所以能迷惑昏庸幼弱之主,惑亂視聽,大抵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其中。詐利既多,黨羽日廣,忠直的臣子直言抗議,一定會先期泄漏出來,因憂戚發(fā)憤,想有所制裁,就正好給了他們奪權(quán)的機會。這就是忠直賢良的人沒有辦法,國家遭到滅亡的原因。《易經(jīng)》說:“履霜堅冰至。”就是說由來很久了,難道是一朝一夕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