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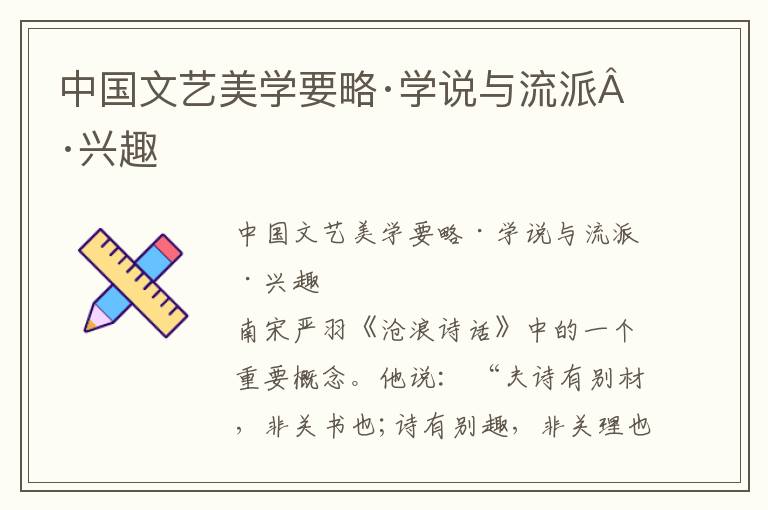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興趣
南宋嚴羽《滄浪詩話》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說: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 以議論為詩”。在這里,嚴羽把“興趣”與“理”、“文字”、“才學”相對而言,可見其必為相反概念。那么,什么是興趣呢?朱自清先生有一段解釋頗可參考:“興趣可以說是情感的趨向,羚羊云云見得這種趨向是代表一類事,不是代表一件事,所以不可死看。蘇軾所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就是此意,……興趣的興是比興的興的引伸義,都是托事于物,不過所托的一個是教化,一個是情趣罷了。比興的興是借喻,興趣的說明也靠著形似之辭,是極其相近的。興趣二字用為論詩之語,雖始于《滄浪詩話》,但以興趣論詩,晉朝就有了。鐘嶸的《詩品》……論顏延之詩引湯惠休說:“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鏤金,都是這一類。”由此觀之,“興趣”這一概念乃指在詩歌中借比興手法表達某種情趣。或者說“興趣”即指包含著情趣的詩歌形象。統觀滄浪論詩,的確是如此的。詩歌用來說理、記事,如果離開了情趣,都不免死板、呆滯,至于專在文字上下工夫,那就更令人難以卒讀了,唯有抒寫情趣、性靈,方顯得玲瓏剔透、意趣深遠;引人遐想,給人美感。當然這并非說詩歌不能記事說理,但這記事說理也應充滿了情趣,無情無趣之作決計成不了好作品。
根據“興趣”要求,情趣當然不是憑空生出的,也不是硬造出來的,它應是“興”的產物, 也就是詩人感于物而產生的情感體驗。嚴羽說: “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這里的意興與興趣意義相同。可見興趣與理并行不悖。盛唐佳作中可謂無一篇無理。關鍵在于如何來表現這個理。嚴羽所批評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涉理路”之詩,是指那種沒有情趣的蹩腳之作,并不解以此來認為嚴滄浪一概反對詩中表現事理。
由于詩歌離不開情趣,所以詩人對理的認識與表現也就帶著感情。這樣一來,就不是通常的認識了,而是形象思維。因而嚴羽提出“妙悟”的概念來。 “妙悟”是指詩人對描寫對象中的理所做的直觀性領悟。是一種心理體驗活動。因此“興趣”與“妙悟”是不可分的。嚴羽的興趣說強調詩歌中的情趣,把事、理與情趣統一起來,這就突出了詩歌的審美特征,亦即抓住了詩歌的本質。這比之那種簡單地強調詩歌的教化作用,重內容輕形式的觀點是深入得多的。因此興趣說在我國美學思想、詩歌理論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它對后世的詩歌創作也有明顯的影響。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神韻說、性靈說都受到了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