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脅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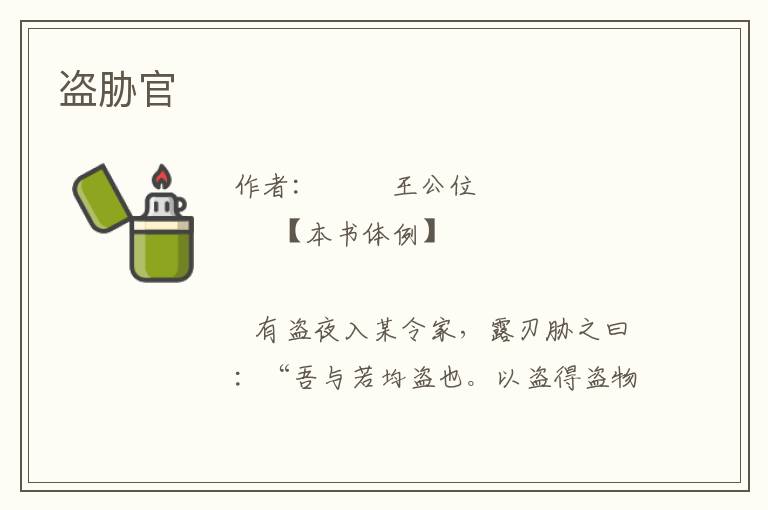
作者: 王公位 【本書體例】
有盜夜入某令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冒死為之,徒以貧故不得已而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若所為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若資,吾可以歸里買田,恂恂(xún詢)為善人,不猶勝若之終身為盜乎?”胠其篋千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其鄰有微聞之者,傳播于眾如此。此江南某縣嘉慶初年事。
(選自《北東園筆錄》初編)
有一位盜賊夜間潛入一位縣令家中,露出匕首威脅說:“我與你都是盜賊。我用竊取手段取得你所盜取的財物,不能稱之為盜賊。我僅盜取財物罷了,不必去殺人;你這個盜賊常常殺人而盜取財物,你與我相比,誰個較好些呢?犯了盜竊罪必定判處死刑,我明知而竟然冒死去干,只是為了貧窮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我曾經計算過,我所盜的若干家,所作若干案件的價值,與你所作所為比較起來,還抵不上你的一半,而白白地給我扣上盜賊的罪名,真是很沒道理的。現在,我獨獨奪取你家財物,就可以返歸鄉里購買田產,真誠實意改邪歸正做好人,不比你終身做官盜強得多嗎?”于是打開箱子拿走千金而離去。縣令大為驚懼,不敢對外泄露這件事。縣令的鄰居有稍微聽到這件事情的,傳播于眾人,大致如此。這是江南某縣嘉慶(1796——1820)初年的事。
這篇小說借一個盜竊者之口,斥責了名謂官吏實則盜賊的罪惡行徑,肯定了所謂盜竊者敢于與官吏作對的膽識。
行文可分四層意思。首先,盜者敢于公開承認自己是盜賊,但官吏更是盜賊。這里將“盜”與“官”相提并論,撕破了為官者的虛偽面紗,無疑這是對傳統觀念進行挑戰、批判與否定。接下去說:“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即是說我個人是私盜,而你縣官卻是官盜,以私盜奪得官盜所掠取的財物,不能稱為盜賊。這就進一步推翻了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將已經黑白混淆的觀念重新加以澄清、辯白,從而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官吏的罪惡本質和虛偽面目。出語針鋒相對,提法新穎,發人深思。其次,盜者說,我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取得財物而已;而你們官盜常用殺人手段竊取財物,這就進一步暴露了官盜的殘忍性。再次,盜者說,我的所作所為是迫不得已,我所盜的若干家,所作的若干案件,累計價值抵不上官盜的半數,可是官盜卻成了皇命朝官,我反落一個盜賊之名。這番話,鞭撻了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黑暗社會現實。最后,盜者說,我只要有了錢財就可以購置田產,平安生活,改邪歸正,不比你們終身做官盜強得多嗎?這里將盜者的暫時行為與終身為盜的官吏作了對比,進一步揭露官盜的一貫性。
本文顯然是受《莊子·胠篋》篇的影響而寫成的。《胠篋》篇中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意思是說,那些偷竊帶鉤的人便遭刑殺,而盜竊國家的反倒成為諸侯,諸侯的門里就有仁義了。莊子是針對戰國紛亂的社會現實所發出的不平之鳴,本文作者是針對晚清黑暗的社會現實所發出的不平之鳴,為此本文同樣具有批判和認識的意義。由于本文運用類比推理,詞語鋒芒畢露,語氣咄咄逼人,使本文具有雄辯的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