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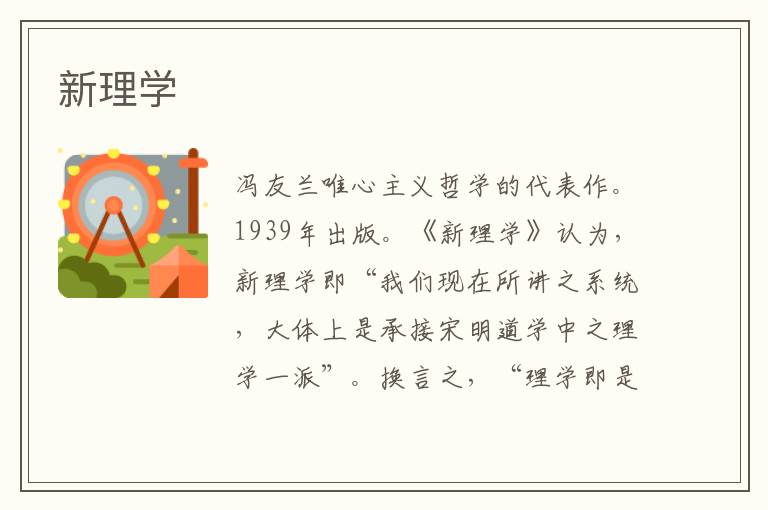
馮友蘭唯心主義哲學的代表作。1939年出版。《新理學》認為,新理學即“我們現(xiàn)在所講之系統(tǒng),大體上是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換言之,“理學即是講我們所說之理之學,則理學可以說是最哲學的哲學。但這或非以前所謂理學之意義,所以我們自號我們的系統(tǒng)為新理學。”(《新理學》,第1-2頁。商務(wù)印書館,1939年5月版。下引該書,只注頁碼。)馮友蘭認為,他的新理學是一個“全新的形上學”,是為講形上學的人開了一個“全新的路”。然而,實際并非如此,所謂新理學不過是宋明理學和實在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翻版而已。它通過詭辯的方法,虛構(gòu)了一個“理世界”,認為“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形成了他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新理學》把宇宙劃分為實際底事物、實際和真際等三個由低而高的層次。認為實際底事物即是具體存在物,實際就是經(jīng)驗中由事物組成的現(xiàn)實世界;真際就是由思維抽象出來的“理”組成的本體界。在他看來,由知實際底事物而知實際,由知實際而知真際。但是,“及知真際,我們即可離開實際而對于真際作形式底肯定。所謂形式底肯定者,即其所肯定,僅是對于真際,換言之,即其肯定是邏輯底,而不是經(jīng)驗底。”(第28頁)他主張“哲學只對于真際有所肯定,而不特別對于實際有所肯定。真際與實際不同,真際是指凡可稱為有者,亦可名為本然;實際是指有事實底存在者,亦可名為自然。真者,言其無妄,實者,言其不虛;本然者,本來即然;自然者,自己而然。實際又與實際底事物不同,實際底事物是指有事實底存在底事事物物。……實際是指所有底有事實底存在者。”(第10頁)這里馮友蘭完全割裂了事物、實際與真際三者的關(guān)系,認為哲學只是對真際作形式的或邏輯的肯定,而形式的或邏輯的肯定又可以超脫于客觀事物,可見這完全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其實任何一種邏輯的思維都離不開一定的物質(zhì)內(nèi)容,都是在具體的客觀歷史條件下的思維,所謂抽象的沒有具體內(nèi)容的邏輯肯定是根本不存在的。
《新理學》認為,“理”是事物的主宰者。“說理是主宰者,即是說,理為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某理為某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不依照某理者,不能成為某種事物,不依照任何理者,不能成為任何事物,而且不能成為事物,簡直是不成東西。”(第125頁)又說:“就事說,每種事,亦皆有其所以為此種事者;此即其理,為其類之事,所必依照者。依照此理之事,即其理之實際底例。亦即其事之類之實際底份子也。……就關(guān)系說,每種關(guān)系,亦必有其所以為此種關(guān)系者。例如此物在彼物之上,在上乃一種關(guān)系。在上之關(guān)系,必有其所以為在上者,其所以為在上,即在上之所以然之理也。”(第46-47頁)“總所有底理,新理學中,名之曰太極,亦曰理世界。理世界在邏輯上先于實際底世界。”(第115頁)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馮友蘭把世界劃分為二:一是此岸的現(xiàn)實世界,一是彼岸的“理世界”。現(xiàn)實物質(zhì)世界是“理世界”的體現(xiàn),“理世界”是現(xiàn)實物質(zhì)世界存在的依據(jù)。換言之,抽象的“理”是第一性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者或創(chuàng)造者,客觀的事物則是第二性的,是由“理”所派生出來的,顯然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的說教。
理本來是指事物的規(guī)律,事物的規(guī)律是一類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是一般的東西,而具體事物則是特殊的東西。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沒有特殊也就根本談不到一般,離開特殊的一般是根本不存在的。《新理學》把一般與個別割裂開來,認為理是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并且是具體事物的本原,在具體事物之先。這樣,他所說的理就不可能是事物普遍本質(zhì)和共同規(guī)律,而只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觀念等,可見這與程朱派的理學唯心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新理學》還認為,“理”是超時空的絕對,“何以理是超時空底。時或空是兩種實際底關(guān)系,而理不是實際底,所以不能入實際底關(guān)系之中。有‘在上’之理,但‘在上’之理,并不在上,不過物與物間之關(guān)系,如有依照‘在上’之理者,則其一物即在其他物之上。有‘在先’之理,但‘在先’之理,并不在先,不過事與事間之關(guān)系,如有依照‘在先’之理者,其一事即在其他事之先。”(第81-82頁)這就是說,理不僅與具體事物是割裂的,而且與時間、空間也是對立的,是超乎于宇宙之外的東西,顯然這就把“理”進一步抽象化、神秘化了。
其實,理與事是統(tǒng)一的,理就是事的理。同樣,時間與空間就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時間是事物運動的延續(xù)性,空間是事物運動的廣延性。因此,時間和空間都是事物運動的存在形式,時間和空間與運動著的事物是不可分離的。《新理學》把“理”說成是時間和空間以外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柏拉圖、黑格爾所說的“理念世界”的翻版而已。
《新理學》為了給“理”找一個“掛搭處”,它又提出所謂“氣”,稱之為“絕對底料”。它說:“絕對底料,在柏拉圖、亞力斯多德哲學中,謂之‘買特’,此‘買特’并非科學中及唯物論中所謂‘買特’。科學中及唯物論中所謂‘買特’即物質(zhì)。此所謂‘買特’則并非物質(zhì)。若欲自彼所謂‘買特’得此所謂‘買特’,則至少須從其中抽去其物質(zhì)性。我們說至少,因為或者還有別底性,須自彼所謂‘買特’中抽去。此所謂‘買特’本身無性。因其無一切性,故不可名狀,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第65-66頁)又說:“或有謂:一實際底物,即其所有諸性所合成。若抽去其一切性,則即成為無,更無有可以為絕對底料者。然若無絕對底料,則無以說明何以實際底物之能成為實際。若專靠所以然之理,不能有實際”,因為“理無氣則無掛搭處。”(第66頁)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說在宋明理學那里“氣”還是一個物質(zhì)性的東西的話,那末在《新理學》看來“氣”也是一個精神性的本體。它企圖在理與實際事物間建立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似乎“理”可以借助“氣”的“料”去轉(zhuǎn)變?yōu)閷嶋H。然而,它又把氣和物分開,認為“氣”只是一個“邏輯觀念”,其所指既不是理,也不是實際的事物。它本身無一切性,是不可捉摸,不可思議的“絕對底料”,是超物質(zhì)的“真元之氣”。可見,它所說的“氣”也是一個精神性的本體,實質(zhì)上“氣”和“理”并沒有什么區(qū)別,二者可以說是一個東西。《新理學》為了擺脫“理”“無掛搭處”的困難,企圖用“氣”來說明理何以能成實際,可是它對“氣”的解釋卻使之更深的陷入了唯心主義泥坑中。
《新理學》的哲學思想體系,與當時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對立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了有害的作用。但是,他力圖把現(xiàn)代西方哲學與中國儒學溶合起來,強調(diào)克服古代哲學的樸素性和直觀性,在邏輯思維方面,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