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和“詩界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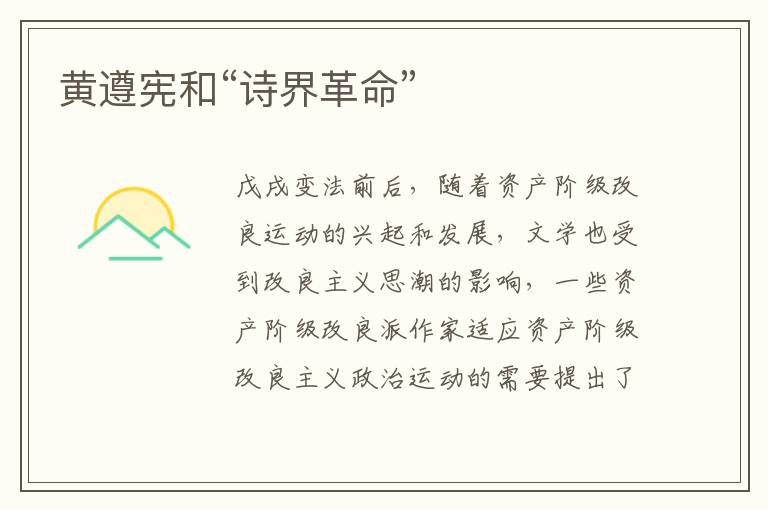
戊戌變法前后,隨著資產(chǎn)階級改良運(yùn)動的興起和發(fā)展,文學(xué)也受到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作家適應(yīng)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yùn)動的需要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在戊戌變法前的一、二年,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人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并試作新詩。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提出詩歌應(yīng)“能以舊風(fēng)格含新意境”,繼續(xù)鼓動“詩界革命”。但真正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shí)踐方面給“詩界革命”開辟道路的是黃遵憲。他被當(dāng)時(shí)改良派作家看做是“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在龔自珍之后,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詩人。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yīng)州《今梅縣)人。光緒二年(1876)舉人,歷任駐日、英參贊及舊金山、新加坡總領(lǐng)事。在國外十六七年,深受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等的影響,形成了“守漸進(jìn)主義,以立憲為歸宿”的改良主義政治理想。歸國后,參加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強(qiáng)學(xué)會”,創(chuàng)辦《時(shí)務(wù)報(bào)》,曾助湖南陳寶箴創(chuàng)行新政,積極參加戊戌變法。戊戌政變后,隱居鄉(xiāng)里,以詩人終。黃遵憲作為政治家和詩人具有遠(yuǎn)大的政治抱負(fù),他作詩是“憤時(shí)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他“窮途競何世,余事做詩人”。但在“詩界革命”中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早在青年時(shí)期,他便提出了反對傳統(tǒng)詩壇的擬古主義的主張,抨擊那些以摹擬古人為能事的詩人是“俗儒”,認(rèn)為他們是“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xí)甘剽盜,妄造叢罪愆”。并且別創(chuàng)詩界之論,提出了“我手寫我口”的主張。他認(rèn)為詩歌應(yīng)能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要求“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認(rèn)為今古不同,今之人也不必與古人同。主張繼承古人優(yōu)良傳統(tǒng),但認(rèn)為應(yīng)力求創(chuàng)新,變化多樣,“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從而達(dá)到“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為我之詩”。他的論詩主張表現(xiàn)了變古更新的精神。黃遵憲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表現(xiàn)了“新派詩”的嶄新風(fēng)貌。他的詩反映了新世界的奇異風(fēng)物和新的思想文化,開辟了詩歌史上從來未有的廣闊的領(lǐng)域,反映了近代社會的巨大變化。他的《今別離》四首,吟詠輪船火車、電報(bào)、照相片和東西半球晝夜相反四事,使詩歌創(chuàng)作有了新氣息。作為政治家兼詩人,他關(guān)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yùn),他的許多詩描寫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逐客篇》揭露美國侵略者掠奪華工開發(fā)美國反而虐待華工的罪惡;《馮將軍歌》歌頌馮子材抗擊法國侵略者的光輝戰(zhàn)績,表現(xiàn)出希望后繼有人,抵抗外國侵略,拯救國家民族危亡的愿望。《度遼將軍歌》揭露了湖南巡撫吳大澂在中日戰(zhàn)爭中的可恥失敗;《哀旅順》極寫旅順地勢的險(xiǎn)要,失之可嘆,表現(xiàn)了對國土淪喪的悲憤。《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等詩以極大的熱情鼓舞士兵抗敵的情緒。這些詩歌都從不同方面表達(dá)出詩人的愛國主義思想。作為改良主義的政治家,他的詩對封建社會不平等的制度和貪官污吏的罪惡也加以抨擊,《鄰婦嘆》描寫了舊社會苦難婦女的不幸。《己亥雜詩》對戊戌變法的失敗表現(xiàn)了悲憤的情緒,怒斥頑固派的殘酷愚拙,悼念維新黨人。黃遵憲的詩能以傳統(tǒng)的形式表現(xiàn)新的思想內(nèi)容,能把散文化的筆法與嚴(yán)整的韻律相諧和,做到了舊風(fēng)格含新意境,取得了詩界革命的新成就。他的詩以現(xiàn)實(shí)主義方法反映近代歷史的重大事件和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有“史詩”之稱。黃遵憲的詩表現(xiàn)了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不僅內(nèi)容方面有改良主義的思想主張,而且在形式方面也不能徹底擺脫舊形式的影響,力求保存舊風(fēng)格,有的詩歌古奧難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