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期江南經(jīng)濟的發(f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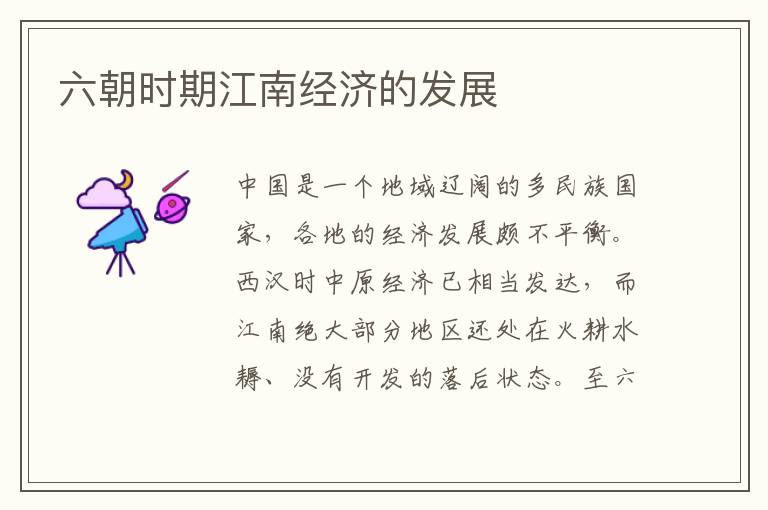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各地的經(jīng)濟發(fā)展頗不平衡。西漢時中原經(jīng)濟已相當發(fā)達,而江南絕大部分地區(qū)還處在火耕水耨、沒有開發(fā)的落后狀態(tài)。至六朝時期,各方面的社會條件才有了顯著變化。北方戰(zhàn)亂頻繁,從東漢末到劉宋初一百多年間,中原人口大量南遷,總數(shù)在二百萬以上,主要徙居荊、揚二州,其次為交、廣,再次為閩中,給歷來地曠人稀的江南地區(qū)補充了大量勞動力。隨著北方衣冠士族和下層民眾的南渡,也給江南帶來了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和科學文化。而且,東晉南朝政權(quán)建立,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第一次南移,郡縣設(shè)置更加廣泛,如交、廣地區(qū)由西漢的七郡五十五縣增為晉的十七郡一百二十一縣,漢代東冶縣至東晉析為十五縣,江南有效行政管理范圍顯著擴大,官府實施一系列勸督農(nóng)耕的政策,也有很大促進作用。此外,蠻、越與漢人的民族融合,戰(zhàn)亂無多、比較安定的社會政治局面,溫暖濕潤、灌溉方便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都是有利于南方經(jīng)濟迅速上升的重要歷史條件。江南地區(qū)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發(fā)展,主要表現(xiàn)為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孫吳時期,江南大族已經(jīng)擁有相當強的經(jīng)濟力量,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僮仆成群,閉門為市,但一般局限在三吳地區(qū)。東晉時期,田園、莊墅一類封建大地產(chǎn)更加普遍化,土地兼并出現(xiàn)了爭占山川湖澤的新趨勢,小農(nóng)破產(chǎn)加劇,紛紛成為大地主的佃客、部曲,成為私屬人口,農(nóng)業(yè)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日漸深化。宋孝武帝在大明年間(457-464)頒布“占山格”,規(guī)定官僚地主各依品級占山,山澤私有已經(jīng)合法化。整個南朝,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農(nóng)奴制的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從平原地帶拓展到廣大山區(qū)。謝靈運、孔靈符、蕭子良等等,都擁有含山帶水、自給自足的大莊園。在這種生產(chǎn)經(jīng)營形態(tài)下,人民的負擔加重了,而江南的開發(fā)也加強了。六朝時期江南農(nóng)業(yè)有長足的進步。大量荒地墾辟成為肥田沃壤,以三吳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京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為中心的丹陽地區(qū),以壽春(今安徽壽縣)為中心的淮海地區(qū),以江陵(今屬湖北省)為中心的荊州地區(qū),以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為中心的鄱陽湖流域,以至交廣地區(qū)、閩江流域,都得到開發(fā),南方再沒有大片的空白區(qū)了。農(nóng)作物的產(chǎn)量,提高幅度頗大。三國時稻畝產(chǎn)已達五石,南朝時出現(xiàn)了畝產(chǎn)二十斛的最高紀錄。而且,已經(jīng)顯示出多種經(jīng)營的特點,除了稻、麥、菽、豆諸糧食作物外,蠶桑、茶、藥材、果木、漁獵等,都是民眾的謀生之道。農(nóng)田水利設(shè)施也推廣開來,有溉田千頃以上的烏程(今屬浙江省)狄塘、吳興塘、曲阿(今江蘇丹陽縣)新豐塘,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蒼陵堰等;有對江湖自然水系加以綜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浙江長湖沿湖開六十九所水門,調(diào)節(jié)它的蓄池灌溉功能;還有主要用于防止災(zāi)害的長江的江陵大堤、錢塘江的捍海塘、滬瀆的防沙壘等。江南手工業(yè)提高很快,吸收了北方的先進技術(shù),發(fā)展了南方特有的工藝部門,主要是冶煉、紡織、瓷器、造船和造紙。把生鐵液灌入熟鐵以提高含炭量的“灌鋼”技術(shù),輕薄如煙氣的羅谷,一年四熟乃至八熟的桑蠶,胎質(zhì)實、釉層厚、紋飾美麗的青瓷,快捷如風電的鸼和載重二萬斛的巨船,利用桑皮、籐皮為原料制成的藤角紙,都是這個時期取得的突出成就。江南的交通事業(yè)也有所發(fā)展,尤其是水路航運,形成三條便利的交通線:干線是從江陵(今屬湖北省)至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市)的長江水道,連結(jié)了荊、揚兩個最富庶的經(jīng)濟區(qū);輔線一是從江陵、豫章至番禺(今廣東廣州市)的湘贛水道,溝通荊、揚、交、廣四州;一是從句章(今浙江余姚縣東南)經(jīng)建安(今福建建甌縣)至番禺的浙贛閩水道,溝通三吳和交廣。北起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中經(jīng)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京口、吳郡(今江蘇蘇州市)南至浙東的運河網(wǎng)已初步形成,是隋代大運河南段的雛型。江南的商業(yè),雖由于這個時期自然經(jīng)濟比重上升而不甚發(fā)達,但還是比北方繁榮。建康、壽春、江陵、番禺,都是這一時期新興的商業(yè)中心。布帛等實物一直起著貨幣的作用,但錢幣行世比過去普遍,東晉有比輪、四文、沈郎錢,宋有四銖、當兩、耒子錢,梁有五銖、四柱錢。海外貿(mào)易進展顯著,孫吳以來,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大秦(羅馬)諸國,皆遣使來華,南朝時,直接通商國家遠至天竺(印度)、波斯(伊朗)和師子國(斯里蘭卡)。江南的開發(fā),改變了中國一向南貧北富的形勢,長江流域的經(jīng)濟水平逐漸趕上甚至超過黃河流域,經(jīng)濟重心開始南移,為比秦漢更強盛的隋唐帝國提供了新的經(jīng)濟基地。而且,建立在南方開發(fā)基礎(chǔ)上的六朝文化,與建立在中原民族融合基礎(chǔ)上的北朝文化一道,成為馳譽世界的唐代文化的兩個重要來源。江南經(jīng)濟發(fā)展的材料極分散,除了六朝正史的有關(guān)志、傳之外,在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宋李昉《太平御覽》等類書和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等地志中,也保留了一些零星記載。今人專著有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fā)展》(上海人民出版社),論文主要有馮君實《六朝時期南方的開發(fā)》(《吉林師大學報》編輯部《中國古代史論文集》)及萬繩楠《六朝時代江南的開發(fā)問題》(《歷史教學》196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