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魯迅”與“學者魯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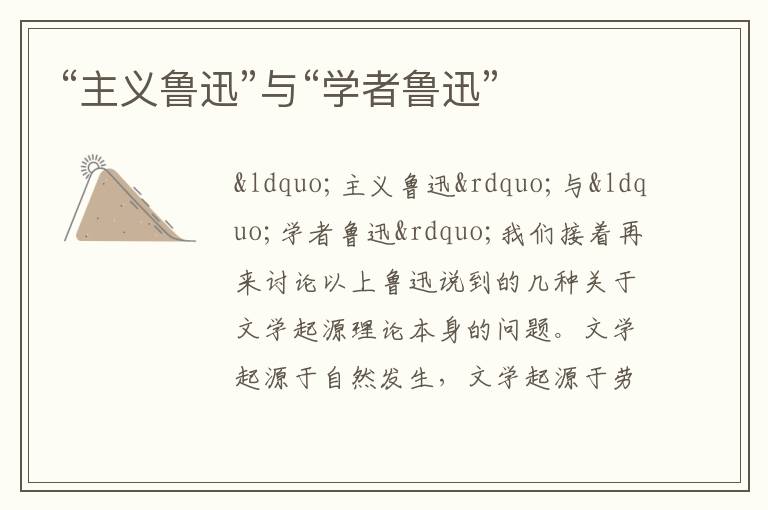
“主義魯迅”與“學者魯迅”
我們接著再來討論以上魯迅說到的幾種關于文學起源理論本身的問題。文學起源于自然發生,文學起源于勞動,愛情,神話,宗教,巫史等等。其實,這些說法各自無疑都有相當的道理,它們都經過許多研究者的反復論證,而且都有豐富的證據材料,足以使它們立足于學術之林。它們都解明了文學藝術起源問題上的或一側面,對于各種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形態、不同歷史年代的文學起源,它們都提供了給予解釋和解答的選擇可能,因此它們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學術資源。只是由于學界早就存在的各種學派的分歧和偏見,以及過分的學術上的自我中心主義,使得長期以來形成了各種學派和學術思想之間的隔閡和紛爭、批判和討伐,彼此都懷著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滅此朝食的決心。于是助長了學界那種門戶式甚至幫派式的思維,以唯我獨尊為追求目標。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在當時社會分化極其嚴重,各種勢力矛盾趨于激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學術問題上專宗一派的學者不少,他們專一的或者說是單一的知識結構,很容易養成排他思維,變成宗派意識,這是他們互相分歧、發生爭論甚至爭斗的基本原因。而能夠廣采諸說、兼綜各家的學者則不多。以前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魯迅也是一位很“專注”的學者,前期他信仰進化論,在抨擊反對進化論勢力方面尖銳潑辣,針針見血。后期他轉宗社會主義革命學說,對一些非社會主義思想派別也批判有加,不遺余力。這樣的印象應當說基本上不錯。但是如果完全從這樣的印象出發,來將魯迅“定型化”“角色化”,來解釋與魯迅相關的一切問題,那就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實了,可能將魯迅簡單化了。實際上,真實的魯迅,誠如我們在上面以文學的起源問題為例所作的討論那樣,他是個知識廣博、思想復雜的人物,他在一些學術問題上能夠兼采多種學說,為我所用,顯示出相當的學術包容性。在這種場合,他很理性,而并不偏執一隅。這也是魯迅性格的不可忽略的一方面。
其實文學起源問題,是個很復雜的文學理論問題。由于“起源”問題涉及的是人類初始時期的一個精神活動領域,是要去把握這個領域中的一個“臨界點”,而這個點早已成為過去時態,今天早已不存在任何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個點存在于什么時間,在這個點上的狀況究竟如何,所以這個問題也是很玄虛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本身,它就是個“模糊問題”,今天要對此作出精確的明斷幾乎是不可能的。后人關于這個問題的各種回答,其實也都是依據了某種文化發生論學說而作出的推斷,各種說法雖都有相當的道理,但任何一種都很難說就是“不可撼動的”結論。僅以上面所列舉的魯迅所提到的“天然”發生說,起源于神話說,起源于巫史說,起源于宗教說,起源于勞動說,起源于愛情說,起源于休息說等,便都有相當充足的道理,不可簡單否定它們,實際上也難以簡單否定它們。然而自另一方面看,每一種說法,幾乎也都存在某種“軟肋”,都不能自稱已經做到詳盡周密,涵蓋一切,天衣無縫。所以每一種文學起源說,雖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贊成,也都曾經遭受到一些人的反對和批評。
即以唯物史觀所認定的勞動起源而論,較早提出文學藝術起源于勞動的是19世紀晚期的一批藝術史學者,如德國的畢歇爾在《勞動與節奏》中指出,勞動、音樂和詩歌最初是三位一體的,而它們的基礎是勞動。梅森認為最原始的詩歌是勞動詩歌,其作用是為了加強勞動的效果。德索在《美學與藝術理論》中也談到了詩歌與勞動的密切關系,但他認為詩歌的作用不是“加強效果”,而是使得勞動更加輕松。普列漢諾夫在《沒有地址的信》中舉了不少“勞動先于藝術”的例子,認為:“藝術發展是和生產力發展有著因果聯系的,雖然并非總是直接的聯系。”他的論點成為唯物史觀的經典說法。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后,中國文藝理論界引進蘇聯的唯物史觀文藝理論,勞動起源說遂得以廣泛流傳。在此種背景下,魯迅接受了這種說法。但是,這種理論實際上也不是絕對嚴密的,而是存在若干紕漏。
首先,所謂“勞動”,對于原始人類而言,是個不確定的概念。原始人類早期生活來源的取得,按照一般人類學的解釋,應該包括采摘、狩獵和養殖、種植兩大部分。兩者都是勞動,但性質有所區別:前者是直接取自大自然,后者才是人類的“再生產”。前者是簡單勞動,后者則是相對復雜的勞動。是哪一種勞動當中產生了文學?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們可以不客氣地指出,這種簡單勞動,與動物從大自然中取得生活資料,差異不是很大。猿猴的采摘本領可能比人類還大,它們的爬樹能力比人強得多,而且猿猴之間也會有一些彼此呼應和情緒交流的聲音發出,難道能夠說文學起源于猿猴嗎?如果勞動起源說是指復雜勞動,當然就可以顯示出人類的特性來。但是早有學者指出,人類學會復雜勞動,是在進化到一定階段之后的事,所以這時候所產生的文學,就不一定是最早的“起源”的文學了。另外,我們還應該理解到,原始人類的生活內容也是豐富的,并非整天都在“勞動”,勞動之后必須有適當的休息。而且勞動要受天氣的影響,氣候惡劣時,特別是寒冷的冬季,是以休息為主的;在休息時難道就不會有文學藝術發生?而生產勞動之外,他們還有許多其他的活動,如兩性之間的互動關系(戀愛、婚姻等),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系(撫育幼小、贍養老者、兄弟姊妹友愛、天倫之樂等),各族群之間的互動關系(友好交往或互相敵對甚至戰爭),人類與神祇之間的互動關系(宗教祭祀活動等),在這些場合中,往往也能激發出人的激情,從中也完全可能產生早期的文學藝術。
另外,在關于文學起源的多種理論中,還有一些魯迅沒有說到的學說。如“游戲”說,認為文學起源于游戲。康德曾說過詩歌就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戲”,19世紀英國哲學家斯賓塞,指出藝術和游戲的本質都是人們發泄過剩精力的自由模仿活動,因此二者是相通的。這是文學起源于游戲的早期說法。稍后格魯斯撰《人類的游戲》一書,認為游戲是對實用活動的準備和練習。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普列漢諾夫曾批判“文學起源游戲說”,但在馮德提出“游戲是勞動的產兒”之后,又肯定了它的合理性。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的主流文藝理論,基本上對“游戲說”是否定的,說它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理論”。平心而論,我覺得游戲說也有相當道理。因為在人類活動的早期,游戲與現在的意義(消遣的、純粹玩樂的意義)不完全相同,它往往寓有學習、練習各種生活生產技能的含義。我們看一些幼小動物,也特別喜歡游戲,彼此打鬧,通過這種游戲,它們學會各種必需的生活技能,包括一些捕食技能。所以游戲并非“超實踐”“超生活”的無意義活動。人類包括兒童和成人(老年人亦需要游戲,君不見近年來公園中唱歌舞蹈者,多六七十歲老者?)都需要游戲,游戲是生命活動的組成部分,所以游戲中產生文學,也是一種符合情理的說法。游戲說之外,還有一種“模仿”說,認為文學藝術是人類對于自然和自己生活的模仿。此說在西方也有很古老的歷史,早在古希臘時期,德謨克利特就說:“在許多重要事情上,我們是模仿禽獸,作禽獸的小學生的。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亞里士多德在其《詩學》中亦說:“摹仿出于我們的天性”,人最初的知識包括文學藝術都是從模仿得來。這些說法,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不可遽以為其謬妄。當然,模仿說與游戲說有些接近,因為許多游戲都出于對生活實踐的模擬,從自然和生活中得到啟發。
如果我們認可各種關于文學起源的學說,雖然大都不免存在這樣那樣的欠缺,但都有其一定的依據和道理,不可斷然予以否定和抹殺,那么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就首先應當端正我們的立場和態度:不應當持過于褊狹的眼光和心理來看待此問題,應該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和理性的眼光,來兼采各說之長,以求得一種恰當的答案。至于要對特定的民族文學現象解釋其“起源”問題,則還應當結合該民族的特殊歷史發展狀況,他們的特殊文化心理背景,考察期文學的實際發展進程,才能得出比較合乎實際的看法。而“開放”的觀念,“理性”的態度,是對于文學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魯迅在這方面給我們作出了良好的榜樣。
以上我們對魯迅曾經發表過的關于文學起源問題上的一些觀點,作了討論。我想我們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魯迅不同時期所持有的一些觀點,幾乎每一種都有學術上的合理性。由此可知,魯迅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清醒的理性立場。他沒有因為自己信奉了某種世界觀體系,就將一些合理的學術觀念完全舍棄。他實際上對此作了調和,對那些“合理的學術觀念”,即使與他當下的“世界觀體系”不相符合,甚至存在沖突(如“宗教起源說”顯然與唯物史觀相沖突),他也有所保留,有所堅持。他不愿為了某種“世界觀體系”和“主義”而犧牲掉一些符合科學和理性的思想觀念和學術見解。至少在古代文學領域內是如此。不妨說,魯迅之所以為魯迅,就在于他在許多時候,都堅持以學者的理性為自己的基本思維方式。
魯迅前期信仰進化論,后期信仰唯物史觀。從這個角度說,可以認為他當時是一位“主義魯迅”。但魯迅畢生都是學者,他同時也是一位“學者魯迅。”“主義魯迅”始終與“學者魯迅”共存,在某些場合,“主義魯迅”甚至還要讓位于“學者魯迅”,這正是魯迅與某些單純的“主義”人物的不同之處。這是一種重大區別,影響到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見解都會發生差異。由此我們也似乎可以悟出,魯迅在20世紀三十年代,他已經是一位“主義魯迅”;但他卻在一系列問題上與同一信仰的另一些“主義”人物發生了分歧,甚至還有激烈的沖突。這里的原因是什么?我以為,他們各自文化成長背景的差異,知識結構的差異,還有思維方式的差異,導致在一系列具體問題上的不同認知,這是產生分歧和沖突的基本根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