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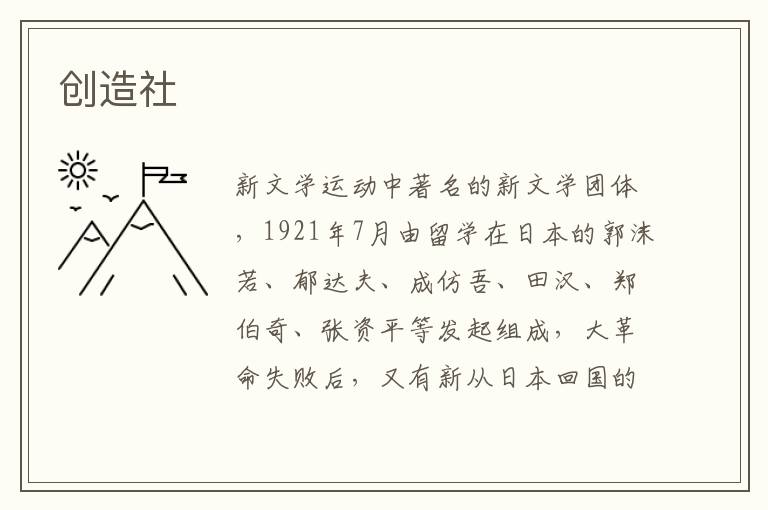
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新文學團體,1921年7月由留學在日本的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鄭伯奇、張資平等發起組成,大革命失敗后,又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朱鏡我、彭康、馮乃超、李初梨、李一氓等參加。先后組辦刊物有《創造》(季刊、月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文化批判》、《思想》等,并出版《創造叢書》,收創作、翻譯作品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譯著百余種。創造社的出現,被稱為“異軍突起”,它是我國新文學的積極浪漫主義流派。反帝反封建是其基本傾向,他們對現實極端不滿,認為把握住時代,對社會的虛偽和罪惡,進行猛烈的攻擊,奮力打破現狀,是文學的使命和文學家的天職;強調自我,崇尚主觀,認為作家要本著內心的要求從事文藝活動,必須忠實地表現自己的內心的要求;在創作上,不論詩歌、散文、小說或劇作,都反抗現實,理想未來,富于主觀抒情色彩,往往是直抒胸臆。或表現為大膽的詛咒、抗爭,狂飆突進的革命精神;或表現為坦率的自我暴露,濃重的苦悶哀痛;甚或流露感傷、頹唐的情緒;即或在歷史故事神話傳說題材中,也說“自己的話”,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從理論到創作,都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點。在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方面,也多為浪漫主義者,歌德、海涅、拜倫、雪萊等為他們所喜愛。在文學理論上受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至上”思想影響,既強調文學的時代的戰斗的使命,同時又反對文學的“功利主義”,宣傳“無目的論”,講求文藝的“全”與“美”。這固然是出于反對封建主義文學觀和新文學的粗制濫造傾向,但理論上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1925年以后,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擴大,創造社的一些成員不斷沖破資產階級思想束縛,清算唯心主義思想影響,批判“無目的論”,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號召革命的文學家“到兵間去,到工廠間去,到革命的漩渦中去”,創作“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郭沫若:《革命與文學》)。主要成員也直接參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斗爭。大革命失敗后,又齊集于上海,積極提倡革命文學運動,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應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發揮戰斗作用。他們的倡導把文學革命引向深入,但也存在著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創作上的標語口號傾向。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在文學理論、文藝批評、翻譯等方面發生過的爭論,是屬于新文學內部兩種文藝思潮的爭論,兩個社團在反對封建文學、鴛鴦蝴蝶派方面,則是一致的,協同作戰的,它們共同地為新文學及其不同流派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